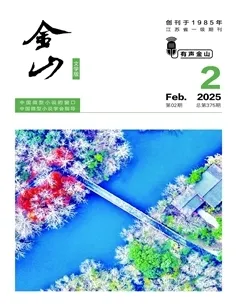小街情語是心語
作家王躍的散文集《小街連云》出版發行。看到封面上那青石板鋪就的巷里小路,描繪了小街的古樸滄桑,一下子拉近了我和這本書的距離,盼一睹為快。擇一周末,躲進陋室,一壺清茶相伴……
(一)
打開書,一股清風撲面而來。字里行間流淌的是小街的美,小街的自信,小街的風姿,小街淳樸的民風,小街人和善的熱情。千言萬語,欲語還休,柔韻留音,萬種風情,所有這些在王躍筆尖的演繹下,都似“百煉鋼化為繞指柔”,輕輕地觸摸著讀者的心房。
散文集共分為“小街連云”“眺望鄉愁”“人閑花落”三個部分,分別寫小街的風土人情和美食、作者的鄉愁和對生活的感悟。
文章以景、以事入手展開抒情,文筆細膩,雋永清秀。王躍筆下的連云小街故事,如小街澗溝里的一條條溪流,靜靜流淌,潺潺而過,一路歌唱,流入山腳下的黃海,流進讀者的心田,詩意般向讀者娓娓道著那隱藏在小街和她心里塵封已久的往事。
人世間唯有兩樣東西不可觸摸:一是記憶,二是思念。記憶無花,在王躍心里卻永遠盛開;思戀無果,在她心里卻永遠清晰。一個作家的記憶和思念,成就了王躍一篇篇優美散文。
(二)
王躍的故鄉在江蘇沭陽縣,故鄉留下了她的童年,記憶最深的是淮沭新河,那是魚蝦的天堂,“鯽魚渾身散著金光”,“鱖魚身上的花紋像大師的杰作”, “鯉魚的身子像在朱砂里打了個滾”……
這些魚兒不僅是她童年的印象,更是在她的舌尖上留下了家鄉的味道。
因父親工作變動,王躍舉家搬遷到連云港。她的新家就安在連云小街,她在小街的臨海路小學、連云中學,分別讀完了小學和初中。此后的日子里,除了在外求學,她在小街一直生活到婚嫁。
對于連云港的地產美食,她在《寧把他鄉作故鄉》中寫道:“一方面是我的家在大河邊,我的味蕾已經適應河鮮的滋味;另一方面也因為我的父親。父親對沙光魚是不屑的,他說,肉太癱了,哪有我們大河里的魚好吃。”
一年秋天,王躍在好友的邀請下,一行幾人到連云區板橋街道東邊的臺南鹽場一對蝦塘釣沙光魚。“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熱情的鹽場人自然要留客人吃飯,據說,住在圩下的鹽場人對沙光魚情有獨鐘,鹽場人家招待客人,離了沙光魚就不成席了。“十月沙光賽羊湯”,光是魚,好客的主人就做了三種,當然少不了沙光魚,有紅燒的,有做湯的。好客的主人熱情地夾一條紅燒沙光魚給她,王躍一下子失態地叫道:“我不吃沙光魚的。”主人有點尷尬了。她不知道的是,那是鹽場人待客的高禮遇呢!
那天,是王躍在連云港生活多年以來,第一次品嘗沙光魚,當然并沒有傳說中的癱,相反的是,魚兒的肉質細膩,味道鮮美。剎那間,王躍一下子明白了,父親為什么說沙光魚的肉癱了。
入鄉隨俗,不知不覺中,云臺山的特產如云霧茶、葛藤粉等,成了王躍的最愛,黃海盛產的梭子蟹、大對蝦、生蠔,潮間帶灘涂上豐產的黃鉗蟹、沙光魚、小花蜆成了她餐桌上的新寵。
(三)
人生旅途的邂逅,不經意轉身的回眸,讓王躍的生活中多了一份人間美食的記憶。正如那杯升騰著裊裊清香的云霧香茗,在舌尖翩躚的味蕾所舞出來的風韻,就是她揮之不去的鄉愁。
小街的云臺山自古多藥草,宋代文壇大家蘇東坡游歷云臺山后,留有“舊聞草藥皆仙藥,欲棄妻孥守市阛”的詩句。
4月,小街上映山紅漫山遍野;5月,金銀花萬花叢中一點黃。夏天里,小街山上白色野薔薇開得正旺,小街人家的梔子花又香又白,團團如蓋。“因為它們喝的是云臺山上的泉水。”
據說,愛花的女子心地善良,內心深處都是毛茸茸的,我想,王躍也是這樣的人。
“空的墨水瓶是身子,一塊薄薄的圓鐵片上有一個洞,一根雪白的燈芯從中穿過,燈芯的下半身懸浮在煤油中,每當黑夜從村頭開始向村里彌漫,燈就亮了,如豆……母親在燈的不遠處,有固定的位置,是一把矮矮的木凳子,她手里永遠不得閑……”
這是王躍在《燈如豆》中,對煤油燈和母親的描寫。
我也寫過一篇類似的散文《煤油燈下的母親》,也是墨水瓶自制煤油燈。一盞煤油燈,兄妹圍一桌,母親一邊做著針線活,一邊陪我們寫作業。夜深了,多少次我一覺醒來,母親還在煤油燈下忙活。一燈如豆的年代里,煤油燈發出闌珊的亮光,把母親的影子拉得比黑夜還長……
王躍年長我兩三歲,我們屬于同時代的人,童年的相似經歷令我對這篇文章感同身受,特別有共鳴。童年里,那昏暗燈光下的一幕幕,每晚都在農村莊戶人家一扇扇窗里上演。
閃爍在記憶中的那盞燈是素樸的,這種樸素的記憶更是思念,屬于王躍大姐,也屬于我,因為我們的母親就是燈!
(四)
既然書名是《連云小街》,我猜想作者一定會寫小街上的果城里。
里,為人們聚居的地方。
果城里,一座始建于民國時期的建筑群,由荷蘭人在連云港建港時建造。建筑風格既有濃郁的江南氣息,又有明顯的西洋風格,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建筑中的精品,也是現代人的網紅打卡地。
果然,文集里有一篇《我在果城里,等你》。
走進果城里,進門的臺階是石頭的,房子的墻頭是石頭的,高高的門框是石頭的,腳下的路是石頭的……
如此石頭之城,應該是一座冰冷的建筑,但,在作家王躍看來它卻是一座“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溫暖之城、融合之城。傳統的民族風格與外來的西洋風格珠聯璧合的果城里,符合這位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女性的審美觀和對美學的追求。
輕輕推開這扇沉重的大門,感覺穿越到了過去的年代,那破敗窗口的風吟,仿佛在向王躍講述著過去的舊時光。
踏著歲月斑駁的石板路,王躍一路尋覓,也一路思索:果城里最早的居民哪兒去了?昔日那朱紅的廊檐、紅色的瓦,也全褪去了顏色。今日的果城里,有太多太多的落寞。
果城里就像一個燈枯油盡的年邁老人,靜靜地立在云臺山下,滄桑寫滿了臉龐。置身其中,絲絲惋惜與陣陣惆悵,一起涌入王躍的心頭。
(五)
兩年前,我開始創作一部長篇報告文學,其中部分章節寫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錦屏磷礦建港鐵軍劈山填海炸平廟嶺山,建設煤碼頭的故事。去年隆冬里一個寒冷的午后,我約王躍大姐給我做向導,到當年的廟嶺山遺址實地考證,感受港口建設者如火如荼建設連云港的壯舉。
昔日的廟嶺山已經蕩然無存,我們站立的位置視野開闊,可以俯視原廟嶺山的全貌。王躍指著前方不遠處的一片區域對我說:“紅星弟,這里就是廟嶺山所在地,現在成了港口集團新東方貨柜碼頭。廟嶺山,也叫孫家山,山的東面還有一條建于民國年間的鐵路隧道,叫‘云臺山洞’。之后,云臺山洞也被稱為孫家山隧道,是火車從隴海鐵路自西向東駛向終點站的最后一條隧道。”
王躍對廟嶺山可謂如數家珍,盡管天氣寒冷,她還是邊說邊伸出一只手比畫:“廟嶺山距離我家很近,出了家門只需向東步行5分鐘就到。我可是廟嶺山的常客呢,上小學和初中時,班上有一個和我很要好的女同學,她的家就住在廟嶺山的南坡。那時還是單休日,逢星期天她就邀請我到她家里玩。”
文集中一篇《廟嶺山,一座不沉的山》,細細讀來,才知道廟嶺山上還有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間的寺廟,叫祗圓寺。祗圓寺北面的山體延伸入海,形成一個距離海面兩米多高的天然平臺,相傳,西漢名士蕭望之經常垂釣于此,由此得名釣魚臺。釣魚臺的臺面有幾丈方,上面泛著淡淡的青色,陡峭的臺壁上,留下了隋海州刺史王謨詩刻,南宋海州郡守趙東、金世宗時東海縣令宋蟠、明代知州王同等人的題刻,記述他們“剝苔讀詩、慷慨吊古、臨風秉筆”的山海之情。多處石刻中,又以王謨的“釣魚磯”三個大字最為著名,他還留下了詩作:“因巡來到此,矚海看波流。自茲一度往,何日更回眸。”
講述到此,王躍咂咂嘴,惋惜地說:“紅星,那些石刻我都一一觀賞過呢,可惜的是,都被炸毀了!”
隆隆的炮聲打破了廟嶺山的平靜。
1982年初,連云港港廟嶺新港區煤炭碼頭一期劈山填海工程全面開工,隨著6月10日廟嶺山首次大爆破取得成功。廟嶺山開始日漸變瘦、變小,最終被夷為平地。
王躍在文中寫道:“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廟嶺山旁的過客,我的新家安在廟嶺山東側的荷花街,每周我都要經過廟嶺山回娘家……”可見,她對廟嶺山是多么難舍難忘。
王躍指著下面車來車往,流水游龍的新東方貨柜碼頭對我說:“多年后,我采訪了連云港港口集團建港工程師高兆福,他因為發明‘爆破擠淤法’而獲得國家科技發明獎和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爆破擠淤法,通俗講就是利用港口的淤泥造港,這樣可以使得航道變寬、變深,方便大噸位巨輪進出港,關鍵是不用大動干戈去開山填海。如果此方法早點發明,廟嶺山就免去了被炸毀的厄運。”
說著說著,王躍的聲音大了起來,她顯得很激動,雖然身處寒冬里,她的臉還是因情緒的變化而漲得通紅。
王躍愛廟嶺山,正如她在文章中寫道:“愛一個地方,總是在面目全非后,才涌起層層疊疊的思念。”
為廟嶺山從地圖上消失,沉入海底而感到惋惜的人,可能不是王躍一個人,至少還有連云小街的人吧?但是,在作家王躍的心里,廟嶺山永遠是一座不沉的山!
讀到最后一頁的最后一行字,我喝完了茶壺里最后一口茶,輕輕合上書,我的心房被文章柔柔地觸摸著。“有了《小街連云》,塵封的日子不再是一片云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