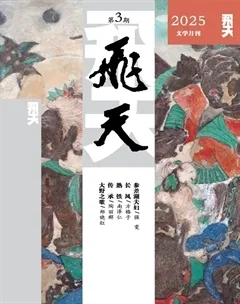傳承
陶麗群,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在《人民文學》《十月》《當代》《中國作家》《青年文學》等刊發表,并多次入選各種選本和年度排行榜。曾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百花文學獎,長江文藝雙年獎,廣西文藝銅鼓獎,《民族文學》《北京文學》《安徽文學》《廣西文學》年度優秀作品獎等獎項。現供職于百色學院。
臘月風吹細雨。不大,毛毛雨,線頭般從鉛灰色的空中飄忽下來,落在人臉皮上,那一點毛刺刺的冰涼讓人微微一悚。這兩天一直飄這樣的雨,路面變得又濕又滑。
天色還早,村里靜悄悄的,狗都還沒出門,太冷了。鄭老四在灶頭喝了一碗熱開水,捉一把鋤頭便出門。往時這個時辰,熱騰騰的大米粥早就下灶頭了,晨起喝一碗黏稠熱乎的大米粥是他多年的習慣。一碗熱粥下去,肚腹暖呼起來,熱氣一上來,人一天的精神便也跟著生發起來了。昨晚老婆跟他慪氣,故意起晚,待他起身,煮粥的水才燒開。他的家在南屏村后排,從伙房后門出來就是南屏空曠的稻田了。他越過伙房后的菜地。菜地很小,不到一分,老婆種滿卷筒青、生菜、豌豆苗、一小片小米椒,還有蔥花、香菜、蒜苗。菜長得好,蔥綠蓬勃,冬天的霜倒也沒毀了它們。
無遮無攔的曠野清冷幽寂,遠處彌漫一團團霧氣。鄭老四緊了緊身上的黑色夾克衫,豎起來的夾克衫領子擋不住紛亂的毛毛雨,脖子一陣陣發涼,但他卻也不愿意返回屋多穿件衣服。在鄭老四生命中的每個冬天,他一向如此,冬天保持一點適當的冷,他認為這樣才能讓人時刻保持清醒。夾克衫是兒子的,在他身上明顯寬松,兒子比他高大壯實。當然,鄭老四在兒子這個歲數時也有這樣的身板。五十歲上后,他幾乎沒買過衣服,兒子扔下的衣褲鞋襪,他接著穿,不講究。這是鄭老四內心并不多的自豪感中的一種,他有兒子,這個兒子大體上還挺稱心。兒子生性木訥,但品性溫順,他們父子之間有一種旁人極難察覺的深厚情誼。這個村靠近縣城,年輕人學了城里人的派頭,不土不洋,看不慣父輩那套為人處世之法,父子之間往往處得如同水火,雙方盛怒之下動手也是常有的事,這讓鄭老四越發覺得兒子難能可貴。兒子上頭還有一對雙胞胎女兒,都嫁了,如今家里就四口人,他們夫婦倆、兒子、年近八十的老丈母娘。過年兒子二十五了,農歷八月初八訂了一門親,打算新年元宵節完婚。未來的兒媳婦眉毛高挑,依他這輩子體察人摸索出來的經驗,這個女崽必定是個心性要強之人,兒子未必能降服得住她。但這樣也好,這個家需要一個強一點的人。鄭老四這三個崽女,讀不成書,萬幸都健康長大,脾性也溫順。
出了自家菜地后,他走進寬廣的稻田,晚稻早就收割了,如今稻田里只剩下曬干的半截稻稈。等年后出幾個暖陽日,在田里放一把火燒掉稻稈,稻草灰就成了肥,春耕又開始了……一向這樣,鄭老四在南屏待了三十三年,這個村莊有很多他已了熟于心的規矩。曠野清冷寂寥,望不見一個人影。年就在跟前了,人和地每年這個時節都要休養生息。春夏秋是萬物破土成長和繁華之季,人和物都處于生命的律動當中,消耗大量精氣神,萬物蕭肅的冬天得蟄伏靜養。
但,也有一些生命在寒冬盡了氣數,永遠走不進新年的春天了。每年這個時候,村莊一般都會走掉個把人。眼看萬物復蘇的春天就在眼前,就是差那口氣。鄭老四觀察了一輩子,發現人在春夏秋這三季走掉的極少,零零散散亡去的幾個人,黃寶林家的大兒死于車禍,黃全栓從房梁上跌下來摔死,黃秋糧死于毒蛇咬,黃雙齡的小兒死于斗毆,還有溺水的、喝藥的、吊頸的,都是死于非命。鄭老四二十四歲上門來到南屏,當了大半輩子八爺(抬棺人),誰死、怎么死的心里都有一本清楚的賬目。這些橫死的,在鄭老四心中都不屬于“氣數盡的人”“氣數盡的人”是生命自然消亡,像曠野中的萬物在冬天枯萎凋落,遵循天地之道,“橫死”則屬于被天地強行拿走了性命,像萬物在春夏繁華之季枯萎。人只有在寒冬走掉,才配為人。橫死的,屬于違逆天地之道,這是命里有罪孽,不一定是這一世,也許是上一世犯下的,所以不該走也得走。鄭老四見過眾多生命的消亡,悟出這道理。
一陣短促的鞭炮聲從村里傳來,到達潮濕的曠野時,鞭炮聲的脆亮便鈍了很多。如此短促的炮仗聲當然不是喜炮。昨天下午四時,黃家福七十九歲的老父親走了。其實這個時辰并非他走掉的準確時辰,老人午飯后上床歇午覺,大半個下午過去了也沒起來,孫子進屋叫人時,才發現老人已沒了氣息。如此高齡又走得如此利索,這老人真是福澤深厚。鄭老四暗暗松了口氣。村里有兩三個正在吊氣的老人,病了有好長一段時間了,真真假假“死”了好幾回,又一口氣緩回來了,把家里的子孫折騰得夠嗆。按照南屏人的說法,這樣的人要么福澤深厚,老天不忍收了他,讓他多享幾日人間之福。要么罪孽深重,老天故意讓他幾回生幾回死地折磨著。這樣的老人走掉,八爺們(抬棺的八個人)通常都會覺得晦氣,因為在抬棺過程中,通常會出現鬼壓身,也就是抬棺的八爺中,會有一個人覺得肩上的抬棺木壓人厲害,讓這位八爺感到異常沉重吃力。南屏人的說法是,走掉的人有罪孽,害怕到了那邊的世界被責罰,所以將看不見的靈魂依附到抬棺的某一位強壯的八爺身上了,不肯去那邊。不管你信不信,鬼壓身這事確實有,八位八爺胖瘦高矮都差不多,愣是有一位吃力得小腿肚打戰,脖子的青筋都凸暴出來了。也只能咬牙忍著送到墓地。這一番吃苦,輕者幾天精神頭都差,重者可能就要頭疼腦熱發好幾天痧了。鄭老四就碰到過一回鬼壓身,那是黃雙齡的小兒斗毆被捅死那回,那小子也就二十來歲,精瘦,加上一副棺木,別說八個人抬,四個人抬都能跑得起來,鄭老四那回硬是給壓得出了一身大汗水,兩腿灌鉛似的,像是他一個人在背那副棺木。過后幾天他一直頭重腳輕的,兩條腿走路像走在棉花上,使不上勁。
村后這條沿田路通往南屏的洼地,也就是村里的墳場。它夾在一片寬廣的稻田間,出了水利渠后拐上甘蔗地,穿過也是寬廣一片的甘蔗地,才到達洼地。鄭老四仔細留心查看正在走的這段路,大體上還是平坦的,沒什么上下坡,除了有些濕滑,穿上防滑水田鞋,留心下腳步應該沒什么問題。他越過自家挨在沿田路邊的稻田,田里一片綠油油的,長著綠肥。晚稻收割后,老婆在田里撒了綠肥種。綠肥長得有點像豌豆苗,開春犁田后漚在泥土里,腐爛后就成為極好的肥料,能省不少化肥錢。這些年南屏已經不養耕牛了,犁田耙地全機械化,耕牛便逐漸退出南屏人的生活。不養耕牛,便沒糞肥肥田,田地對化肥的需求量就更大了,這是一筆相當大的農資開銷。村人便開始種綠肥漚田,成本低,一斤種子二十來塊,能撒好幾畝田。只是這東西如何能和耕牛的糞肥相比,只是聊勝于無罷了。村人種了幾年,便沒了心情再種。鄭老四的老婆倒是一直堅持種,他說了幾次,老婆還是照種不誤,他便不再說了。對于老婆,這個和他生活了三十幾年的女人,他目睹她的青絲變灰發,腰線從有到無,料理家事也不甚利索了,他也沒嫌棄過她。年輕時老婆的眉眼倒也算是有幾分稱他的心,孩子生后她就不怎么收拾自己了。多半時候家里的事情都是鄭老四說了算,性子還是很溫順的,但在一些她認定是為家里、為孩子好的事情上,她執拗到鄭老四也無可奈何。比如種綠肥,比如關于昨晚的爭執。
雨似乎變得大了點,落在稻稈上有綿密的微聲,不過風倒是沒有了。鄭老四在自家田頭略微站了站,發現有幾處田埂被老鼠挖了洞,走過去,從田里挖一鋤頭泥塊把洞口堵住了。不過他也知道堵不住,過不了兩天,又會被重新挖開。這尖嘴猴腮的貨是不會這么輕易罷休的,除非你把它的窩挖得底朝天,再往死里追著它滿田跑,它才會長記性,放棄這個給它帶來厄運的老窩。鄭老四只是下意識地見田埂壞了順手補一補,種田人都這樣。他很快離開了家里的田,沿著沿田路繼續往前走。這一路,他把好幾處凹凸不平的地面給挖平填滿,讓路面變得更平坦。稻田和甘蔗地相接連那地方,有一個緩坡。鄭老四當然熟悉這個緩坡,而且也知道上這個緩坡抬尾棺的兩位八爺會比前頭的幾位八爺多吃點力,當年他也是這樣的。三十幾年過去,他終于熬到抬棺頭的位置。八位八爺分排在棺身兩旁,八爺的前后秩序是有講究的,八爺當然也是固定的。一旦你成了八爺,就得把棺抬到五十五歲,其間除非你“走掉”或者身體健康情況不允許,才能換人。換人也并非隨便換誰都可以,得把新人的生辰八字和幾位舊八爺的對一對,八位爺的命必須相符,才能組成抬棺隊伍,譬如要結婚的男女,八字相合才能談婚事組家庭。由于有了這些要求,加上抬棺又有鬼壓身損自身陽氣的風險,就算這是個積德行善的活兒,一般人都不樂意當八爺,要找一個替換已經到了年紀的八爺,實屬不易。
鄭老四在緩坡上來回走了兩趟,仔細勘察地面,然后開始挖平緩坡。也不需要完全挖平,再把坡稍微緩一緩就夠了,坡也不長,抬尾棺吃力也就那么十幾步路。地面被常年踩瓷實了,挖起來不容易,全是硬黏土,他挖了好一會,才鋤了緩坡一層薄薄的地皮,像魚鱗一樣。新鮮的泥土很濕潤,散發淡淡的泥土腥味,鄭老四擎著鋤頭凝視這面坡。三十幾年來,他不知道通過這道緩坡送多少人去往洼地,每送走一個人,他對于人生與生命就多了一層理解。一個人活著的時候,不管多么繁華尊貴,走的時候終究是一個人孤獨地走,那些他生前自以為享有的繁華與優越,最終都帶不走,都不是真正屬于他。這個村黃姓是第一大姓,余下一些零零散散的外姓都是早年從別處搬遷來的,并非真正的南屏人,比如鄭老四這樣的上門來的。大姓家族仗著人多勢眾,難免多有看輕外姓人的言行。三十多年前,鄭老四剛上門南屏時,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夾著尾巴做人,路上碰個貓狗都恨不得繞道走。當了好些年八爺后,每多一次見生命消亡,他的生命狀態就變得越松弛。對世間萬物(也包含人)應有敬重之心,但達到畏懼得沒了主心骨、活得丟了自己的就沒必要了,大家橫豎都是一條命,誰都逃脫不了最后埋進洼地,沒必要把自己的命凌駕于別人的命之上,更沒必要將自己的命墊在別人的命底下。鄭老四開始一點一點活得舒展起來,大大方方和南屏人交往,有人擲給他不屑的目光,他了然于心,但并不困于心。
再鋤一層薄土,坡面就沒那么滑了,坡度也緩了不少,他便不再動。
上了這個坡就是甘蔗地,十多天前南屏的甘蔗就砍收結束了。黃家福的老父也算是個體恤人,擱到十多天前走,家家忙活砍收甘蔗,誰都沒心思操辦這場白事。甘蔗要在炸糖廠規定的時間內砍收完,炸糖廠派出運輸車隊來運輸甘蔗,錯過時間,往糖廠運輸甘蔗就得自行解決運輸問題了。鄭老四家有八分甘蔗地,長得好,正好整了一車,年前甘蔗款應該能撥下來。當然,兒子元宵節的婚事并不靠這筆錢,婚事的款項早就備下了,彩禮給了六萬八,這是相當體面的一筆彩禮,辦事當天女方會回禮,對半,或者四六返回。鄭老四想到兩個出嫁的女兒,兩個女兒的婆家都不怎么富,好在人家家風正,禮數周全,把家里的底子坦誠亮給了女方,存款不多,外債倒是一分沒有。家里底子薄是因為有老人常年臥床吃藥。鄭老四也就沒計較了,彩禮錢幾乎全部回了禮,女兒的三金也是他們夫婦貼給的陪嫁,還給每個女兒開了本折子,存上不大不小的一筆錢款,以備急需。他是疼愛兩個女兒的,當然,在三個崽女中,他的心還是更傾向兒子。兒子是他血脈和生命的象征與延續,有一個兒子在農村人的觀念里是不可或缺的。將來他走掉是要兒子給他點長明燈摔火盆,捧著牌位走在前頭引路將他帶到洼地。
鄭老四原本想順著甘蔗地往洼地去,看看老丈人的墳頭的。三月初三掃過墓后,他便沒來過。老婆在洼地自家地里種了木薯,隔三岔五跑洼地,鄭老四有點兒佩服這個女人的膽量。洼地土質貧瘠,種什么都欠收成,南屏人早就放棄在那里種莊稼,任其長滿野草。老婆覺得可惜,春天時一把火燒了還未來得及發芽的枯草,然后挖地下種子。洼地平時很荒涼,村里還養牛時,人們還會將牛趕到那里放,如今再也沒什么人來去了。一旦洼地有人聲,就是村人又往這里送走掉的人來了。這雜草橫生杳無人跡的墳地,一個女人能待得住,得有點膽子。鄭老四站在甘蔗地朝洼地望,只見那里隱約的草尖。洼地地勢比甘蔗地低,是望不見的。
似乎又起了風,裹挾著雨撲打在鄭老四的臉上,他抹了一把臉,濕漉漉的。轉身朝村里望,包圍著南屏的空曠稻田還是人跡全無。在朦朧的細雨中,南屏的上空升起裊裊的晨煙。他到底沒往洼地去,大清早又風又雨的,一把歲數了,荒涼之地還是少去為好。他尋思著,沿著來路往回走了,心里默念老岳父。岳父兩個女兒,鄭老四的老婆是老大,小姨子嫁在隔壁村。那是個很有膽量的能干女人,早年說服她男人包了六十畝山地種甘蔗,日子早就富了。老岳母有點小氣,喜歡斤斤計較,但老岳父那可真待他不薄。鄭老四剛上門來到南屏那年,他就問他要了生辰八字,去找當時抬左側棺頭(左右以左為大,前后以前為大,抬棺位于左側前頭的八爺是八爺中的領頭人)的八爺黃家寶,讓黃家寶拿他的八字和另幾位八爺的對,竟真對上了,相合相生,等黃家寶到了年紀退下來,老岳父便將他薦進八爺隊伍里。鄭老四當然明白老丈人的良苦用心。誰家都有老人,老人走掉時都不是自家人背去洼地埋掉的,得仰仗八爺們一路勞力相送。八爺在農村,是受人尊敬的,惹了八爺,到你家有事時,他臨時告個頭疼腿疼,出不了棺,那可就是大事了,你沒法臨時湊出一個合適的八爺,而出葬時辰又耽誤不起。老丈人這是為鄭老四鋪就融入南屏的路呢。這八爺一當就是三十多年。三十多年,他在南屏大體上還算是順順當當的,當然小煩惱小矛盾小摩擦避免不了,但都不算什么。老丈人是在八年前臘月十一走的,也是無病無災,吃完晚飯說累了,進房一躺就沒再起來。鄭老四把老丈人的葬禮辦得很體面,得體地將他送走了。
沿著來路慢慢往回走,遠遠地,他看見幾個人影從村巷里出來,一身素白,鄭老四便明白是燒遺物來了。走掉的人的鋪蓋衣物鞋襪等個人用品,得在出葬當天清晨燒掉,捎往“那個世界”,等人到了“那個世界”才不至于無裹身之物。兩邊的人越走越近,是黃家福的大妹領著幾位族嫂。幾個女人挑的挑抬的抬。家福的大妹叫葵花,腫著兩只大眼袋,看見鄭老四,頭一低,微微彎腰給他鞠一個躬,鄭老四趕緊伸出雙手扶住她。這是喪禮。
“叔,老父全仰仗您送一程了!”葵花說,又垂淚了。
“你家阿爸是有福德之人,高壽,走得無痛無苦,是喜喪。”鄭老四勸慰一句,幾個女人便走了。等他快要進入村巷時,回頭一望,看見她們在稻田間一處十字路口燒火,灰色的煙霧斜斜升起。
老丈母娘也起來了,裹著厚實的大棉襖在廳堂里引火盆。小寒以來,老人天天都得燒火盆,在火盆邊上一坐就是一整天。過了年老人就八十一了,按照南屏的習俗,這個歲數是個坎,得給做一場道場沖沖喜。但元宵節是兒子的婚事,一個家庭不能一年雙喜。所謂的福無雙至,物極必反。所以老人的八十一沖喜就免了。鄭老四擔心老岳母有意見,讓老婆和她解釋,老岳母在這件事上倒是難得開明,不沖就不沖了,孫子的喜事要緊。
“我來燒!”鄭老四走過去端起火盆。燒的是木炭,這是小寒前他從集上買回來的,兩蛇皮袋,燒完天氣也開始暖和起來了。有差不多十年時間,這個老岳母橫豎看他不順眼,家里但凡他經手的事情,她能挑出一大堆毛病,岳父也拿她沒辦法。岳父只會趁喝兩口酒時嚇唬她,揚言要將她送回娘家。不知為何,岳母對這話鐵板釘釘地信了,往往能讓她把脾氣收斂上一陣子。老岳父用這句話愣是嚇住她一輩子。他端著火盆進廚房,粥已經煮好,老婆正在剝卷心菜。她抬眼慍怒地瞪他一眼,鄭老四只好笑笑。他將幾塊木炭放在煤氣灶上,點火引燃。
“早飯后你過去瞧瞧,有事情做就搭把手。”鄭老四說。
“要你教我!”老婆氣鼓鼓地說。
“提醒你嘛,怕你忘記了。”鄭老四討好地說。
“我什么時候忘記過這種事情。”老婆說。他尷尬地笑笑。木炭在煤氣灶上噼啪作響。村里有白事,鄉鄰們是自動前往幫襯的,不用請。今日有你,明日有我,誰都有落難需要幫襯的時候。等娶了兒媳婦,村里紅白喜事的禮尚往來就歸兒媳婦了,婆婆要退居幕后。
老婆很大聲地吸了鼻子,鄭老四正從煤氣灶上往火盆里夾已經燒紅的木炭,一慌,失手將木炭摔落在地上,木炭被摔碎了,火星四濺。他飛快地瞧了老婆一眼,見她兩只紅腫的眼睛里一片水亮,不敢出聲,手忙腳亂地收拾地上的碎木炭。老婆瞧著似乎又不忍心,從飯桌邊站起來,走過來踢了他一腳,從碗柜下拿出掃帚將四散的火炭歸攏起來,盛到火盆里。鄭老四知道老婆心軟了。這么多年,他摸透了她的脾氣,只要鄭老四放低姿態,露出誠惶誠恐的樣子,也不管是真怕還是假怕,老婆立馬就軟了。女人其實很好弄,她要的就是個態度,給個態度什么就都依你了。村里有幾個男人,動不動就跟老婆動拳腳,弄得家里雞飛狗跳不得安生,他覺得這幾個孬種沒活明白。一個家里,把女人弄順了,她就死心塌地地給你把家整好了。男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你有再大的本事,進家門也弄不到熱飯熱菜吃。
鄭老四將火盆端出來給岳母,又盛了一碗熱粥給她。岳母一輩子凡事愛挑剔,但有一點好,在吃上從來不吭聲,鍋里有什么吃什么,一天三頓白粥也從不在左鄰右舍前多嘴。依她的性子,也不知道怎么的竟能做到這一點。
“都備好了?”岳母端著粥碗問他。
“媽,都備好了!”鄭老四答。他知道岳母問的是兒子的婚事。
“嗯,少不下三十桌,幾頭的親戚要照應到,落下誰都有口舌!”岳母說。
“都列有名單了。”鄭老四說,他略一猶豫,起身進房間拿出一本綠皮子的本子,逐一念上頭的名字給岳母聽。本子上有三頭親戚,鄭老四這一頭,岳父這一頭,岳母這一頭。岳母聽著,指出幾個沒列出來的遠親。她說那些親戚的崽女結婚時也請我們了,我們也不能忘了他們。遠歸遠,總歸也算是一份親。鄭老四便拿筆添列上,又給岳母對了一遍名單,一時也想不起還有誰落下。岳母放下粥碗,扶住兩個膝蓋慢慢起來,緩緩挪進房間。他們家是一棟兩層樓房,六年前起的,鄭老四夫婦和老岳母住一樓,兒子住樓上。鄭老四覺得這輩子就這樣了,給岳父母養老送終,嫁掉兩個女兒,給兒子起個房子,將兒媳婦娶回來,這一生就算完結了,以后這個家興衰就看兒孫們的德行了。
岳母從房里出來,手里多了一個灰色的毛線帽子,吊著的兩朵絨球晃蕩著。她又扶著兩個膝蓋坐下,通過廳堂的后門往廚房小心地看了一眼。鄭老四心里暗笑起來,說到底,在大事上,老岳母還是相信自己的。她那警惕的一眼不就是防自己的女兒嘛。老人依然緊緊捉著毛線帽子,探究似的深深看了鄭老四一眼,然后將毛線帽遞給他。這情形是第三次,鄭老四知道岳母給的是什么。兩個女兒出嫁時,她也是這樣將積攢的幾個老本拿給鄭老四的。她早就不掌管家事了,手里的幾個錢都是逢年過節晚輩們給她的祝福,長年累月積攢,也存下一小筆零散錢。鄭老四接過岳母的毛線帽。不接不行。這個女人要強了一輩子,孫子的終身大事是不會不出一分力氣的。他張開帽子,帽兜里有用橡皮筋扎起來的一小捆一小捆紙幣,大小面值都有,還有十來個鋼镚,一塊錢一枚的鋼镚。這是積攢破爛賣的錢。
“夠不?”岳母問,仿佛孫子的婚事就等她這筆錢。
鄭老四使勁點頭,“媽,夠了夠了,就差你這筆大錢了!”
岳母聞言,豁開空空的門牙一笑。她已經快二十年沒走出過南屏了,根本不知道外邊的世界如今是什么模樣,平時家里人趕集,她需要點什么,老是囑咐“去供銷社買點……”她不知道供銷社早就成老皇歷了。
鄭老四把那些錢小心翼翼揣進兜里,將毛線帽子還給岳母。這帽子,使命大概也到此了。鄭老四暗想,有淡淡的哀傷。
“我們家的崽,十多年前我找人求過一卦,”岳母悄聲說,鄭老四心里一怔,這他倒沒想到,“四十一歲要有一個坎,你讓他去積點陰功是對的!”岳母將手里的毛線帽往腦袋上戴,她似乎忘記腦袋上已經有一個了,兩個帽子疊著戴在一起,使她看起來有一種滑稽的喜感。鄭老四聞言,知道岳母已經破曉了他的心事。
“是的,媽。”他附和著說,但他所想的和岳母所說的卻是兩回事。
“寶枝婦道心腸,舍不得孩子,女人就那樣,腦袋拎不清輕重,別管她,這事由我來說!”末了,岳母又說了一句讓鄭老四吃驚的話。寶枝是他老婆的小名,生孩子后他就沒這么叫過她,岳母冷不丁說出口,讓鄭老四心里一陣恍惚,這一恍惚幾十年就過去了。岳母的話讓鄭老四懸著的心放下了,他從來不知道凡事斤斤計較的老岳母還有這樣的眼光,真是令他刮目相看。
老岳母開始喝起粥來,鄭老四起身離開火盆邊。家里目前還沒增添什么新家具,他打算過了臘月二十三再集中采購,差不了幾天了,那時候年味濃了,新東西進家門就更喜慶了。他上到二樓,看見兒子的幾雙鞋子東倒西歪散在地板上。這一層他平時不大上來,老婆會上來打掃衛生,一般就兒子住著,二樓上也沒什么家什。他琢磨著要做兩個客廳,這一層得增添壁柜、茶幾、沙發、電視機,少說也得萬把塊錢。平時老兩口晚上看個電視就在一樓,小兩口可以在二樓看。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活法,他理解。鄭老四的目光落在兒子的零散的鞋上,兩雙灰色運動鞋,一雙皮鞋,一雙夏季拖鞋,一雙防滑水田鞋。他蹲下來,拎起一只水田鞋仔細看。兒子穿四十三碼,早年他也穿這個碼數,如今只穿四十碼了。到底是老了,人越活越小,不服不行。他仔細查看這雙防滑鞋子,還八成新,應該是今年才買的。鄭老四拎著鞋子仔細查看,鞋底的防滑釘很結實。他伸出食指,挖掉幾粒夾在防滑頂縫里的小石子,然后將散亂的鞋子一雙雙擺好。屋里的墻壁是抹石灰漿的,不夠亮堂,他思索著過幾日要刷上雙飛粉,粉一上便煥然一新了,再往上頭貼幾個大紅雙喜字,配上新家具,就差不多了。他走到兒子的屋門口,屋門敞開著,這讓鄭老四心里一陣寬慰。這孩子一向這樣,人在不在家他的屋門也敞著,隨便進出,沒什么防備父母的事情和心思。他還少不更事時,家里農忙,他愣是蒙頭呼呼大睡到日上三竿,鄭老四一上來,氣得一腳踢在門板上,兒子便從床上蹦起來,人也不惱,咧著嘴巴笑……不知怎么的,關于養兒子的點點滴滴一時間涌上心頭。算起來,這個兒子養得沒讓他們夫婦操什么心,人憨實,沒什么心眼,病也很少,一般就頭疼腦熱,老岳母給刮個痧,再捂出一身汗便又活蹦亂跳了。叛逆期也沒見他有什么不對勁,頂多就跟他媽頂個嘴,被罵急眼了便威脅說要去廣東打工。鄭老四對這些小打小鬧一向不管,老婆便罵他心里沒孩子。他哪是不管孩子,女人總是認為男人不管孩子,男人對孩子的愛和女人不一樣,不糾結在雞毛蒜皮上的。
鄭老四走進房間,里頭有一股發膠水的氣味。屋里的衣柜和床過些日子也要換新了,再過些日子,鄭老四再要像現在這樣隨意進出兒子的房間是不可能的了。他在心里輕輕嘆了口氣。兒子還在睡覺,灰色的被子下只露出一撮黑黝黝的頭發,床上的被子整出一個大大的人形。鄭老四瞧那大人形,心里又寬慰又有些失落。兒子確實長大了,往后和他最親密、成為他生活必不可少的幫手的將是兒媳婦,慢慢地,家事的主意也得他拿了,鄭老四會漸漸從家庭的中心位置退居次要。
兒子在被子里動了一下,他顯然是聽見有人走進來了,將遮在臉前的被子一把推開,露出一張年輕的、略方的臉,健康和被窩的溫暖使臉上的氣色呈現出溫暖的淡淡紅潤。他散漫地睜開眼,看了鄭老四一眼,又閉上了。
鄭老四在床前的靠椅上坐下來,兒子依舊不管不顧地睡。他瞧著那張露在被窩外的年輕臉龐,是一張沒經過什么世事的臉。想到自己這一生走過的坎坎坷坷,兒子也要重新走過一遍,心里隱隱疼起來。但這又是沒辦法的事情,每個人的路都得自己走,旁人是沒法代替的。
“有事?”一會兒,兒子睜開惺忪的眼睛問了一句。
“沒事,你睡你的。”鄭老四輕聲說。
“我睡覺,你坐這里干嗎?”兒子在被窩里嘟噥,翻了個身,將后背對著鄭老四,露出一小片裸露的強健肩膀。鄭老四趕緊欠起身,將被子拉上來幫兒子蓋住肩膀。默默坐了一會,鄭老四便起身出了兒子的房間。這時候又一陣短促的響炮傳來,他算了一下時辰,應該是做道場的道公們到了。果然,一會兒便傳來隱約的鐃鈸聲音,里頭混著道公唱念的聲音。除了午飯時間,這唱念要一直持續到落葬。短促的炮響聲頻繁響起,那是外村的親戚們陸續奔喪來了,來一撥親戚就鳴一掛短炮,意在告知逝者,親人們來到了。
老婆吃過早飯便去白事家幫忙去了。鄭老四沒吃早飯,和岳母坐在廳堂里烤火。兩人都沒說話。短促的鞭炮聲不斷傳來,這讓鄭老四想起岳父的葬禮。岳父是在八年前走的,那時候家里的樓房還沒起,雙胞胎女兒也還沒出嫁,老老小小一大家人。岳父還沒走時,即便他已經衰老得再也扶不動犁頭,鄭老四心里依然覺得自己有個靠,橫豎風來雨來了,還有老岳父擋在他前頭。他是出不了什么力氣了,但他積累下了珍貴的生活經驗,給個一兩句話,依然可以穩穩妥妥地化解他們生活中所遇到的大小難題。如今老人氣息全無躺在棺木里,鄭老四一下子便覺得人生所有風雨都朝他撲打過來了,他在驚惶與不安中成了這個家的主人,將要面臨著幫助三個崽女成家立業、為老岳母養老送終的家庭重任。那時他既是八爺又是孝子,跪了一天孝后,到出葬時刻,脫下孝服又當抬棺的八爺。送岳父走那一路鄭老四心情極為沉重,悲傷與驚惶交織在一起。
如今自己五十五歲了,到了人生的一個坎,年后將兒子的婚事一辦,他對于家庭的重任便完成了一半,只剩下給岳母養老送終了。岳父去世后,鄭老四磕磕巴巴領著一家人過下來,不順總是有的,但總歸是大順,他得感謝老岳父對他半輩子的扶持,教給他的為人處世之道,更感謝南屏這片水土接納了他。這一點老婆寶枝是不會理解的,她是本村人,永遠不會理解當初他來南屏時內心的惶恐。他怕這片水土不接納他,他怕被村人排斥。
兒子起來了,有力的腳步聲從樓梯上傳來,一陣跑炮,牛高馬大地從樓梯那里拐過來,一下擠到鄭老四和岳母中間。
“我媽呢?”他張口就來,這話是不經腦的,就像渴了要喝水一樣。老岳母抬手拍了一下他的頭。
“你還吃奶?整天找媽,你說你能擔得成事嗎?”她責備起來。兒子伸出手,摘掉岳母腦袋上的毛線帽子扣到自己的腦袋上。
“你媽到那邊去了。”鄭老四盯住兒子說。兒子找媽讓他心里泛起隱隱的疼。二十五了,但一代人不同一代人,當初鄭老四二十五的時候,已經遠離家人來到南屏,在新環境里誠惶誠恐謀生了。眼前這兒子,雖然到了娶親的年紀,心里卻還是一個大孩子,沒經什么世事。就該讓他早一點見識真正的生活。他催兒子趕緊去洗漱吃早飯,到那邊去瞧一瞧,搭把手。
“往后你家有事,鄉鄰才來幫襯!”他說。
兒子一聲不吭走掉了。鄭老四聽見從衛生間里傳來水聲和口哨聲。嘩嘩的水聲讓他渾身一激靈,打了個冷戰。兒子一向喜歡早上起來洗冷水澡,他說那叫醒腦,冷水這么一沖,精神頭就上來了。
屋外依然微風帶細雨,細細密密的,村里漸漸有了人聲。往日這時辰,人早就到田地里了,靠田地吃飯就得這樣,往地里使多大工夫地就有多大產。90年代時,人們扔下田地一窩蜂往廣東跑,指望能在那里闖出一條發家致富的路。家沒發也沒富上,卻讓人沾上了眼高手低的毛病,明明在城市里飄得像條孤獨的流浪狗,卻死活不肯再回來侍弄家里的田地。南屏至今還有幾戶90年代的紅磚瓦房,矮小巴巴地夾在左鄰右舍的樓房間。這些都是兒女出去闖蕩的人家,家里的老人走掉后,再也沒人回來建設祖屋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外頭混得怎么樣。鄭老四的三個崽女被他管得嚴,一律不準外出打工,初中畢業后跟著他和老婆種地。他對他們言傳身教,關于種地,關于生活,他的幾個崽女要比別個的崽女懂得更多的經驗,這一點讓他感到很欣慰。農村人,歸根結底根子都在土地里,他一向認這個道理。
兒子到白事家去了。午時正十二點,一陣長炮響起,他知道已經落棺了,走掉的人已經斂入棺木,到下午三時落釘封棺,四時起棺出葬。這些儀式鄭老四早已了熟于心。他出了家門,順著村巷往白事家走,遠遠地看見忙碌的村人,站住,又往回走。老婆一直也沒回來,他不知道那邊具體的情形。其實他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過去,給走掉的人上一炷香火,那是鄉鄰的情義,很正常。鄭老四卻邁不開步子,靠近幾次又轉回來。午后他感到有些困,想進屋躺一會。眼是閉上了,腦子里卻像有根鞭子在抽著轉。第一次當八爺的情形不斷浮現在他的腦海里,那時他抬棺尾,是最年輕的八爺,一雙女兒尚未滿周歲。三十幾年,起棺出葬時電閃雷鳴他遭遇過,傾盆大雨他淋過,鬼壓人他也沒省下,他熬到了左側棺首,成為首席八爺。如今,他在南屏早就沒有了當初異鄉為異客的驚惶,這片土地完完全全接納了他,賜予他的家人健康順遂。他想回報,已是有心無力。
炮仗再次響起,他知道是落釘封棺的時辰到了。棺材一封,從此算是親人陰陽相隔,成為兩個世界的人。鄭老四從屋里出來。他再也待不住,往門口走去,又想起什么,返身回來上了二樓,往兒子那堆鞋瞧了一眼,又下樓。出大門時,岳母在房間里叫住他,她從房間里出來,默默瞧了他一眼,將手里捏的一截鮮艷毛線繩遞給他。鄭老四一怔,這一點他倒是忘記了。他接過那截毛線繩子離開了家。
牛毛細雨停住了,冷冷的風在村巷里飄來蕩去,時辰已經進入下午,氣溫又變低了。往后這段時間會越來越冷,不然就不是臘月了。村巷里沒什么人,太冷,人們都縮在家里忙活。一年到頭都忙田地里的事情,也只有年底下這幾日料理家里的,該補的補該修的修,該新買的要新買,結結實實敞敞亮亮過個年。
老遠,鄭老四就看見黃家福家的門前擠滿了人,鐃鈸和念唱聲音更響亮了,時辰已經差不多到了。黃家福屋門口懸掛的白門簾已經撤下,門內的廳堂地上擺著一具暗紅色棺木,棺身上點一盞豆亮的長明燈。幾位八爺正在扎抬棺的木架子,他看了他們一眼,也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八爺們看見鄭老四走進來,停下手里的活。他瞧了木架子一眼。三年前,他就不再親手扎架子了,放手給右側首棺的黃新明領其他八爺上手,他在旁邊偶爾指點一下。他信得過相伴幾十年的伙計們。黃新明靜靜瞧著他。鄭老四感受到他的目光,這位老伙計也是當爺爺的人了,雙鬢早就泛起白霜。他對老伙計投去信任的一瞥,黃新明心領神會,又領幾位八爺忙活起來。
鐃鈸和念唱聲緊密起來,短炮接二連三鳴起來,這是起靈炮。跪靈的親人們已經從屋里的棺木旁轉移到屋外,在門口跪靈。八爺們將棺木抬上架子,四道粗麻繩將棺木和架子捆扎起來,每道粗繩橫穿一根大腿般粗的大圓木,大圓木兩端又捆綁人小腿般粗的小圓木,大圓木和小圓木呈“十”字狀,小圓木兩端各站一位八爺。
道公們開始念唱開路詞:
道長問:“舉人生前仁不仁?”
眾道答:“仁!”
道長問:“舉人生前義不義?”
眾道答:“義!”
道長問:“舉人生前禮不禮?”
眾道答:“禮!”
道長問:“舉人生前智不智?”
眾道答:“智!”
道長問:“舉人信不信?”
眾道答:“信!”
眾道合唱:“舉人功德滿,魂歸天,駕鶴成輦入仙班,各路關卡皆讓道,狐黃鬼怪閃兩邊!”
四時到,鐃鈸一陣大響,門口跪靈的親人們齊聲大哭,八爺們已在棺木旁扎穩馬步,抬棺的小圓木落在肩上了。起靈炮一響,八爺們齊發力,吼起來:“一、二、起!起靈了!”
鄭老四感到肩上忽然一沉,小肚腿一顫,沉重感壓迫身心而來,渾身驟然發緊。他望向兒子,兒子站在棺尾右側,那根小圓粗木緊壓在他的肩膀上,褐色夾克衫肩部被壓皺了。靈棺出門,兒子走過鄭老四跟前,腳步滯重。鄭老四伸手拍了一下兒子的手臂,父子四目相對,兒子的目光略帶驚惶,鄭老四的目光流出慈愛與感激。
靈棺在鐃鈸和鞭炮聲中漸漸遠去。
鄭老四忽然記起,岳母交給他的紅絨線還沒給兒子綁到手腕上,他踉蹌著追了兩小步,又停下了。抬棺送人本就是積德行善,要辟什么邪?
責任編輯 趙劍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