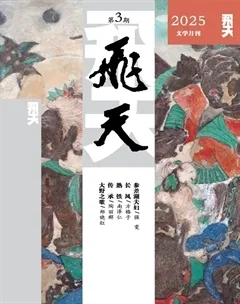喜鵲(外二首)
2025-03-12 00:00:00林子
飛天 2025年3期
桃花好多年未開
三兩瓣紅暈夾在記憶的褶皺里
它用湖藍色的尾翼撥開暮色
貧瘠的童年里射出一束探照燈光
我出生的院落,半段殘垣支撐信念
春風依舊
像一個毫無破綻的謊言
它又一次飛遠
沉落在黃昏的寬袍里
將夜和中年的我,落在人間
糜 灘
沒有一個名字比這更充盈,更廣袤
風吹八百里,谷浪起,谷浪落
我的親人們
趕著羊群消失在夕陽斑駁處
行邁靡靡,趕了幾百里路
歸鄉(xiāng)的父親
望東山,望西灘
糜紅谷黃,少年時候
沒有一個名字比這更寂寞,更荒涼
野草離離,中心如噎
三五只野雞
落下來,又飛走了
父親彎著腰站了許久
風把他含在嘴里
就像含著一棵躬身的糜子
風吹稻浪
金黃的波濤
起伏——起伏——
有一株折下腰,再沒有站直
那一年,父親也這樣
收割、打腰、擰捆
把一壟壟浪推倒,碾成碎金
剝成珠礫,就像在拆卸
自己金黃的盛年
稻田,一塊一塊被騰空
只剩幾個水坑,一截風聲
沉沉墜下,一直到心底
夕陽,一個圓鼓鼓的陶塤
風吹,響了許久
秋天在無數(shù)個父親的咳嗽聲里
緩慢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