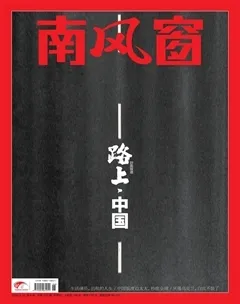尋路中國:流動的生活圖鑒

4月4日清明節祭掃將至,默元想起他已故的爺爺,一個持牌照的腳踏車師傅。上世紀80年代,在連接湖北和江蘇的328國道邊上,爺爺日常蹲守在公交車上落亭外,就像今天的出租車司機,只不過當年主要是用二輪自行車載客到附近目的地,偶爾還會用人力三輪車馱兩個氧氣鋼瓶或其他貨品,從蘇中“里下河”低洼區南沿的老家,送到省城南京或“小上海”無錫。往返約400公里的路,緊趕慢趕要花兩三天。
一晃三四十年過去,江蘇境內公路四通八達(過長江通道就有近20條),從默元老家開車去無錫只要2小時,去大上海也只要3小時。“在路上”的中國人,不難從路橋網絡、交通工具的現代化中,察覺“時空在壓縮”,“車輪駛過的世界”在變大;滿溢的幸福之上,如今還流淌著一些關于節假日出行的“甜蜜的煩惱”。
從“通上路”到“全國一盤棋”
公路作為“中國社會的毛細血管”,歷史可追溯到清末和北洋政府時期,當時公路建設處于萌芽狀態,多為軍用或地方集資修建。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公路基建仍不發達,公路標準低,高等級路和大江大河上的橋梁數量稀少,平均行車時速僅約30公里。
默元后來聽長輩說,八九十年代,家鄉不少人天蒙蒙亮出發,坐長途汽車去無錫、蘇州、上海等地打工。那時候,老家沒有機場、鐵路,公路幾乎是唯一的出行選擇,但也是一段走走停停的艱難旅程。當時蘇南紡織業發達,有人帶話讓默元的母親也出去打工,但她怕路途波折,加上不愿放棄社辦廠(后來叫鄉鎮企業)的工作,沒去。
1988年,在“要想富,先修路”的輿論氛圍中,中國第一條高速公路—滬嘉高速公路(連接上海市區與其衛星城嘉定)建成通車,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前來剪彩。此后,全國掀起公路建設熱潮,且目標從“通上路”轉向“建好路”。沈大高速、京津塘高速、京港澳高速隨后幾年陸續建成。至2001年底,中國高速通車里程達到1.9萬公里,躍居世界第二。
不過,這一階段農村公路仍較落后,多為石子路、水泥路,少見瀝青路;河運在水鄉地區仍扮演重要角色。默元老家的院前自留地,緊挨著一條有2000多年歷史的老通揚運河。默元依稀記得,80年代末鎮上建自來水廠時,一船船物資從這條河運過來,打井工人們就在默元家“付費吃大鍋飯”,由默元奶奶做飯。村里本家鄰居的長輩中,還有半輩子做船夫的老人,顯示上世紀河運在“里下河”一帶仍有不小市場。
2003年起,農村公路進入為期10年的全國重點建設期,促進了農產品進城和城市商品下鄉。光是第一年,全國就建成農村硬化路19.2萬公里,一年的建設量超過此前50多年的總和。默元大學畢業后與高中同學聚會,就聽說縣里開通了不少新的農村公路和公交線路。
隨著中國加入WTO后外貿大爆發和集裝箱運輸的普及,公路網的規劃從局部走向全國一盤棋。尤其是2013年更新的“國家公路網規劃”,提出國家高速公路網由“7射、11縱、18橫”等路線組成。其中“7射”指7條首都放射線。經過頂層設計的公路網,打通了物流的堵點,且愈加重視客流的走向。
新時期公路網的布局更加科學,從放射形、三角形到并列形和樹杈形不一而足。截至2023年底,中國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占公路總里程的3.4%。預計在未來10年,國家高速公路會將地級行政中心、城區人口10萬以上的市縣,以及重要的陸路邊境口岸,全面連接起來。
默元老家所在的縣2018年改設市,如今借助“一縱一橫”的G15沈海高速和S28啟揚高速,實現2小時車程內通達8個機場,加上鹽通高鐵過境,鞏固了該市“長三角北翼重要的交通樞紐”地位—正所謂區位優勢不變,變的只是交通的形式和速度。
在廣袤的中國大地,公路的變遷是一部流動的史詩,記錄著時代脈動和無數個體的命運。從“鄉土中國”邁向“流動中國”,方向盤的每一次轉動,都成為個體與時代雙向奔赴的象征。而在新能源車發力前,中國“鐵公基”就已經馳名天下了。
速度的狂歡
早在2012年,中國高速公路總里程就已達9.6萬公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美國高速公路建設高潮始于1956年《聯邦援助高速公路法》,艾森豪威爾受德國高速公路啟發,推動建設覆蓋全美的州際公路網;至1970年代其基本成型,絕大部分路段免費,由聯邦燃油稅和州財政支撐。
如今,中國公路總里程已超5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超過18萬公里。這背后是一場持續數十年的速度狂歡。典型如京新高速,似一條巨龍橫貫戈壁,將北京與烏魯木齊的距離壓縮至12小時車程;港珠澳跨海大橋則以55公里的跨度,將珠江口兩岸的時空重新定義。
盈盈是湖北恩施州巴東縣人,她向外省人介紹家鄉時,會說“就在宜昌邊上”。宜昌作為三峽大壩所在地,知名度顯然高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提“宜昌”有方便對方理解的一層用意。從地理上看,位于重慶湖北交界處的巴東縣,尤其江北部分,距離宜昌城區也比到恩施州府近,說“在宜昌邊上”也合乎情理。
尷尬的是,在宜巴高速2014年開通前,盈盈每次從宜昌回巴東,要坐車四五個小時(若坐長江快艇,因水陸銜接會耗時更久),即便能近覽江北的峽谷溪流美景,人也往往困乏不堪。但宜巴高速開通后,兩地車程一下子拉近到2小時左右,且該路段橋隧比高達74.5%(興山至巴東段更超過90%)—整段高速路就像架在一個個長短不一的“筷子”上,高度差讓人震撼,馳騁感讓人愉悅。

宜巴高速是我國“東西大通道”滬蓉高速最后一段開工的項目,其通車不僅方便了湖北省內交通,串聯起一條生態旅游“黃金通道”(涵蓋長江三峽、神農架、武當山等),也極大便利了成都、重慶等地經宜昌、武漢通往上海的陸路。
對于跨省游客來說,預計2025年底建成通車的宜興高鐵意義更大,能將重慶至宜昌的車程縮短至3小時以內。但就省內中短途而言,高鐵站站點少(不像高速路出入口多),對于自駕一族的意義不是那么明顯,高速路更能帶給他們“速度的狂歡”。
相比在三峽北岸的崇山峻嶺間架起高速路,“洞穿天山山脈”的高速路,更像是一種基建奇跡。2024年12月,世界最長的高速公路隧道—全長22.13公里的烏尉高速的天山勝利隧道貫通,穿越天山從3個小時縮短至20分鐘,將烏魯木齊至“州府”庫爾勒市(南鄰尉犁縣)的車程從7小時壓縮至3小時。
一旦烏魯木齊至尉犁縣的高速路全線通車,將作為自治區首府去往南疆最便捷的通道,串聯起“北疆城市帶”和“南疆城市群”;往東,可由“京新高速”銜接京津冀,通過“連云港—霍爾果斯高速”銜接長三角;往南,則可由“西安—和田高速”銜接“西部陸海新通道”,通達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和粵港澳大灣區—可謂雖處邊陲之地,亦心系全國。
當然,在地形險峻、氣候惡劣的地區修建公路,會面臨巨大的技術挑戰。喀喇昆侖公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修建時,共犧牲了中國和巴基斯坦約700名建設者,“天路”因而被稱為“死亡之路”。時至今日,這條“世界上最高最美的公路”,僅部分路段做了高速化升級,大部分路段限速在時速80公里以下,好在沿途可飽覽帕米爾高原、喀喇昆侖山脈等壯麗景觀。
遇見最美中國
公路不僅承載著經濟的脈動,也承載著人們對于“一路風景一路歌”的向往。
1954年建成通車的川藏公路(318國道),從成都平原一路向西,穿越橫斷山脈、青藏高原,最終抵達拉薩,因為“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神奇變化,成為了時下自駕游的熱門路線,被譽為“中國最美景觀大道”。
1983年建成的新疆獨庫公路(連接克拉瑪依市和南疆的庫車市),縱貫天山脊梁,沿途可至“億年奇觀”獨山子大峽谷、“世界四大草原之一”的那拉提草原、大龍池景區、紅山石林。由于冬季大雪封路及需要養護,獨庫公路每年只通車5個月。
2023年全線建成的海南環島旅游公路,串聯起了椰林、沙灘、海浪、熱帶雨林等景觀,服務區也變成了一個個小型的旅游景點,讓高速公路旅行變得更為松弛、有趣。
廣州人宛清經常跑深圳,對廣深沿江高速印象深刻。在他看來,快接近南山區收費站的那一段路最美:左側是深圳前海鱗次櫛比的玻璃幕墻,右側是伶仃洋上白鷺掠過紅樹林;疾馳時海風灌窗,咸濕氣息裹著自由感撲面而來;夜幕降臨時,車燈與遠處南沙港的集裝箱燈火交疊,仿佛駛入流動的星河。
去年6月開通的深中通道,則宛如一條巨蟒橫臥珠江口,橋墩高聳入云,仿佛是守護這片海域的巨人。從深圳的高樓大廈到中山的古巷深宅、田園時光,半小時車程就可以自由切換。當然,較高的過橋費用也意味著你不會過于任性地使用它。
作為獨生子,宛清常在假期帶著全家自駕游。過去一年,他把能蹭的節假日高速免費都蹭了,而且去的大部分都是免費的景區,以此降低整體消費成本。為了減少回程堵車,他控制自駕半徑、精選景點,往往上午就開始返程,以避開返穗車流高峰。他熱愛這種在路上的感覺,因為這個時候一家人能夠團聚在一起,拋開日常生活中的雞零狗碎,塑造共同的美好回憶。
節假日“高速福利”之外,2023年全線通車的番禺南大干線,因其免費、快速和全程不設紅綠燈,也是宛清周邊游的首選路徑。這條路是廣州未來1號公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左手連著佛山禪城的煙火城廓,右手握向南沙的碧野長天;暮色中路燈次第亮起,車流化作光斑流淌的河,像是大地寫給未來的草書,每一道彎折都藏著新生的刻度。
“路,就是書。”余秋雨用《文化苦旅》串聯起不同的文化與歷史,而美國歌手鮑勃·迪倫在歌曲《答案在風中飄》中唱道:“一個男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被稱為真正的男人?”人類在旅途中的感悟與追求,最能生發出對于生命意義的追尋。公路在這里,成為了一種精神的寄托,代表著自由、探索與成長。
全球視域中的公路圖鑒
德國是高速公路的鼻祖,其高速路以不限速聞名(少部分路段限速在120~130公里/小時),也因此對車輛性能和駕駛技術提出了更高要求。
當你駕車以180公里的時速飛馳在黑森林邊緣,兩側的冷杉如綠色幕墻掠過,發動機的轟鳴與風聲交織成一首工業時代的狂想曲。但“浪漫”背后暗藏危險:每年因超速引發的死亡事故占德國交通總事故的12%。一位德國工程師自嘲:“我們發明了汽車,卻治不好人類對速度的癮。”
反觀日本,高速公路限速嚴格,一般最高時速不超過100公里。東名高速公路上,豐田和日產組成的車流勻速前行,如同被精密校準的傳送帶。服務區內,自動販售機提供熱湯和飯團,洗手間配有加熱馬桶圈,連路肩的積雪都被激光傳感器實時監測。這種極致的秩序感,讓公路成為社會文明的縮影。
相比德日的高速公路,美國的高速路更有文化一些。其66號公路(芝加哥—洛杉磯)曾見證一個時代的輝煌—汽車旅館、霓虹加油站、牛仔酒吧,構成公路文化的圖騰。但1985年八車道州際高速的興起,讓它淪為“被遺忘的母親之路”。再后來,當懷舊潮席卷全球,66號公路的廢墟重生為文化地標,人們駕駛復古房車,在破敗的汽車旅館前拍照,仿佛在用消費主義療愈失落。
對比美國發達的私人飛機出行,公路的意義愈發曖昧。在得克薩斯州,富豪們駕駛塞斯納飛機掠過州際公路,地面上堵成紅線的車流如同螞蟻軍團。當公路無法承載人們對效率的極致追求,天空成為新的疆域。但這種“分層交通”是否在加劇社會割裂?或許正如瑞士的盤山公路所啟示的:在阿爾卑斯山區,工程師用33個發卡彎和12條隧道征服險峰,但限速30公里的規定迫使人們抬頭—冰川、松林與鷹隼的身影,才是旅途的本真。
這種“回照”也出現在中國西部。帕米爾高原上,塔吉克族牧民的牦牛群沿千年古道遷徙,與平行的314國道(烏魯木齊—紅其拉甫公路)互不打擾,偶有自駕游客搖下車窗拍照,卻見牧民報以微笑。而在五千里之外,當云南獨龍江公路因暴雪封閉,村民們用馬來運送年貨,古老的驛道突然復活。路政部門負責人感嘆:“我們總想著用公路取代一切,但有些路,注定要留給馬蹄和腳印。”
說到古老,英格蘭西南部的科茨沃爾德小鎮,保留著中世紀村莊的風貌,吸引了許多影視劇前來取景。那里的鄉間公路是單車道,路兩側是蜂蜜色的石墻和羊群,每隔幾百米便有一處“錯車港灣”。沒有護欄,沒有指示牌,駕駛者僅靠眼神和手勢默契配合。一位開著拖拉機的農場主說:“路窄了,人心反而近了。”
人在江湖漂,“與時空的和解”,可以是日本服務區里一碗熱湯的慰藉,也可以是英國鄉間小路上的默契禮讓;可以是新疆沙漠公路旁突然出現的野駱駝群,也可以是深圳大鵬半島堵車時小攤販遞過來的新鮮楊梅。
說到服務區,疫情前宛清曾連續六年暑期出國游,加上2010年去歐洲六國旅游,算是走過不少國家,在他印象里,高速服務區是德國的名片—各種商店應有盡有,就像是市區的延伸,加上德國客車、貨車都現代感十足,給他的路上感覺要比在日本的體驗更好。
默元則自豪于江蘇的高速服務區—蘇州的陽澄湖、無錫的梅村、常州的芳茂山、揚州的廣陵,一個個服務區都像是高速上的“小江南”或“愛馬仕”,甚至還伴有主題公園或曲藝演出,作為地方文化展示的窗口,設計理念完全不輸國外。
終極歸宿:人與家園
回望來時路,中國公路的發展成就毋庸置疑—它讓貨物流動、讓旅行愜意、讓邊疆不再遙遠;展望未來,中國龐大的公路網仍在不斷加密,今后將更加注重綠色(如有效避讓生態保護區)、智能(如與運輸服務網、信息網、能源網深度融合)和可持續發展(如提升基礎設施的韌性,降低事故風險)。
許多地方已在先行探索。在浙江,杭紹甬高速“試點”應用北斗高精定位和AI事件檢測,進行實時路況預警、自動駕駛支持及動態限速,通行效率提升三成;在山東煙臺,智能巡檢車用激光雷達掃描路面裂縫,算法生成養護報告,效率是人工的10倍;在湖北荊州的服務區里,自動充電機器人“追逐”電動汽車,仿佛未來已至。
但技術的精確性,在人類復雜的出行行為面前,顯得脆弱。
春節期間,一場關于高速公路上堵著“大聰明”“電車黨”與“一年兩箱油”的群嘲,席卷網絡。有網友表示,初四出發仍被堵在路上,真是第一批返程的“大聰明”。廣東湛江的自駕大軍中,一位特斯拉車主在服務區排隊4小時后崩潰道:“我計算了續航,卻算不透人心。”最熱鬧的還是“一年兩箱油”,這類車主平時不開車,過年回家才啟動車輛,被戲稱為“馬路殺手”和“高速擁堵的始作俑者”,甚至被調侃“閑時占車位,忙時堵高速”。
有專家建議,將節假日小客車高速公路免費政策,改為每年5000公里的免費額度,以緩解節假日高速擁堵問題。然而,這種政策可能導致高速公路管理部門收入銳減,進一步加劇財政壓力。
中國的高速路建設,主要通過“貸款修路、收費還債”的模式,債務規模可觀。2022年底,全國收費公路債務余額達7.92萬億元,且通行費收入無法完全覆蓋運營成本和債務償還。許多高速公路建設年代較早,養護、管理以及債務償還等方面的壓力較大。
相比普通的高速公路,建在流動沙漠中的公路,養護成本更高。在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公路(輪臺至民豐)路面寬10米,用“蘆葦柵欄”“蘆葦方格”等培育的綠化帶卻有78米寬。上百對“治沙人”夫妻各駐一處井站,每天徒步維護公路兩邊的滴灌管線和植被,加上沙暴中推沙車的臨時馳援,才能確保這一征服“死亡之地”的世紀工程不被流沙淹沒。
顯然,當古老駝鈴與ETC提示音在時空中交響,當北斗衛星在電子地圖上投下淡藍色軌跡,中國公路早已突破單純的地理連接,而成為刻錄文明嬗變的活態史詩。或許,未來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更長的里程、更智能化的巡檢系統,還要有一種“慢下來”的智慧:讓公路成為故事的容器、社會流動的晴雨表,而非僅僅作為車輛的快速通道。事實上,從最初的“通上路”到如今追求極致的公路體驗,公路早已不僅僅是交通的載體,更成為了一種文化符號和生活方式的象征。
“路是大地的詩,詩是遠方的路。”公路在中國,不僅是大地上的詩行,是通往未來的進取之路,更是歲月的琴弦,奏鳴著人生與歸宿的交響曲。當清明節祭掃的車流再次點亮中國地圖的脈絡,或許每一盞車燈都在訴說:路的盡頭不是遠方,而是人對家園永恒的尋找與回歸。
(文中默元、盈盈、宛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