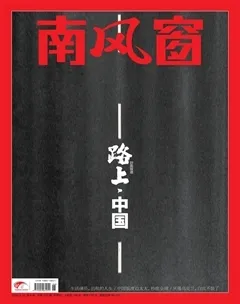默茨勝選,德國“重振雄風”?

每當一個國家“萎靡不振”時,更換政府似乎被視為一種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就像一支足球隊屢戰屢敗看不到希望時,讓主教練“下課”被視為一種“重振雄風”的法寶。
2月23日提前舉行的德國聯邦議院大選,就是基于一種類似的心態。政客、媒體和選民們似乎認為,德國只有通過提前更換聯邦政府才能擺脫國家“內外交困”的局面。
選舉的結果,也確實讓朔爾茨喪失了以總理之尊繼續領導德國的權力。他所在的社會民主黨(俗稱“紅黨”)在大選中慘敗,得票率只有16.41%,與上次大選相比損失了近10個百分點,從第一大黨的地位淪落為議會老三,甚至屈居于右翼政黨“選擇黨”(AFD)之后。
聯盟黨(俗稱“黑黨”)在黨首默茨的領導下,以28.6%的得票率名列榜首,獲得了組閣權,但并不是此次高達83%參選率的德國世紀大選的最大贏家。最大贏家是“選擇黨”和“左翼黨”。只有12年建黨歷史的“選擇黨”的得票率翻了一番,以20.8%的得票率一躍而成議會第二大黨,笑傲群雄,讓百年老黨社會民主黨汗顏。
重新洗牌
之所以說“左翼黨”也是最大贏家之一,是因為選前誰也不看好它。這個因為黨內分裂、名人出走而瀕臨出局的政黨,突然在沖刺階段發力,以反保守、反納粹的清新形象,把無數擔心德國“向右轉”的年輕人聚集在黨的旗下,突破了民調3%~4%的詛咒,拿下了8.77%的有效選票。
如果說有誰比社民黨輸得更慘的話,當推自由民主黨(FDP,“黃黨”)。這個以黃色為標志的中右政黨在選戰的最后階段,頻頻失誤,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領導層的幼稚和黨內的分裂,只拿到4.33%的有效選票,止步于得票率5%的議會門檻之外。
與“黃黨”的命運相同,這個5%的門檻也把新生的“莎瓦聯盟”(BSW)擋在了議會的大門之外,只是后者輸得更慘。這個成立不到兩年的“左右思想混合體”拿到了4.97%的有效選票,與5%的門檻差之毫厘,換算到選票的話就差一萬多張而已。無奈選舉游戲江湖險惡,稍一失手便前功盡棄。
“黃黨”和“莎瓦聯盟”的出局,意味著德國政黨碎片化的趨勢受阻。選前的議會由七個政黨把持,選后的議席向五個黨團集中:聯盟黨老大(208席),選擇黨老二(152席),社民黨老三(120席),綠黨老四(85席),左翼黨老五(64席)。
其中,老大、老三、老四(“黑黨”、“紅黨”和綠黨)屬于所謂的中間勢力陣營,掌控56%的有效選票;老二(藍色“選擇黨”)和老五(深紅“左翼黨”)身后站著約29%的選民,還有約15%的選票投給了無法進入議會的人,打了水漂。
肩負組閣重任的“黑黨”黨首默茨,必須在這般格局中組成一個穩定、團結、能開創新局的聯邦政府。五個政黨共630名議員,看似非常容易形成多種組合以達到316席的門檻,實則難上加難。
默茨有限的選擇
默茨的選擇實際上極其有限。老二和老五被他視為“極右”“極左”,毫無共同執政的理念基礎,不在考慮之列,盡管藍色“選擇黨”不斷向他伸出橄欖枝。
“選擇黨”希望默茨邁出勇敢的一步,推倒他設置的“右翼防火墻”,放下身段共同執政,聯手推出新的難民政策,徹底改變德國的難民管理失控造成惡性兇殺事件頻出的亂局。
默茨心里很清楚,聯手“選擇黨”組閣,無異于養虎遺患,把它從“極右”的牢籠中解放出來,給自己培育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左翼黨”絲毫沒有與“黑黨”聯手執政的興趣。對它來講,“黑黨”是富人和狹隘的德意志利益的代言人,屬于被“斗爭”的對象;同理,“黑黨”對親俄反美疑歐的“左翼黨”連正眼都不愿瞧一下,更不用說同它聯合執政了。
默茨本身并不屬于反對與綠黨合作的人。他在選前雖然猛烈抨擊過綠黨,但在骨子里并沒有關上有朝一日與綠黨聯合執政的大門。這一點與他的巴伐利亞姊妹黨“基社盟”黨首索爾德恰恰相反。索爾德與綠黨水火不容,誓言有他在,“黑黨”絕無與綠黨聯手的可能性。
綠黨不爭氣,也是這次選舉一大輸家,雖然沒有“交通燈”執政伙伴“紅黨”和“黃黨”輸得那么慘,但綠黨在過去三年多的執政過程中露了原形:剛愎自用,價值導向,盛氣凌人。
丟掉三個多百分點是選民對綠黨過去政府工作的“肯定”。從上次大選的14.7%到這次的11.6%,綠黨應當感受到了大批選民離它而去,投入了“左翼黨”的懷抱。綠黨唯一可能感到欣慰的是,其占選民10%~12%的基本盤還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四年痛定思痛過后,綠黨可能又是一條好漢。
但對于默茨來講,當下的綠黨沒有任何的戰略價值。任何懂得加法的人都屈指可算出來,“黑黨”的208席加“綠黨”的85席只有293席,遠遠不夠組閣所需的至少316席。
救星“紅黨”
算來算去,默茨組閣唯一可依靠的對象就只剩下“紅色”的社會民主黨了。也就是說,和老三組成所謂的“黑紅大聯合政府”,是默茨登上總理寶座的唯一臺階。
雖然俗話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但對默茨來講,通向總理府的道路只有一條,就是與他的手下敗將社會民主黨人合作,分享權力,排定座次,約定目標,劃清楚河漢界,建立新政府。
選后出現這般局面,估計是默茨及其團隊萬萬沒想到的。選前的民調一直看好他的“黑黨”,幾乎所有民調機構的預測支持率都徘徊在30%~32%。
受民調的鼓舞,默茨和他的主要助手們都放出豪言要打一個漂亮的選戰,目標確定在“30%+”。換句話來講,30%以上乃至35%的得票率,是默茨期待的。
然而,28.6%的結果意味著,“黑黨”并沒有實現選戰目標。這不是區區幾個百分點的問題,而是一個戰略問題,事關默茨能否大刀闊斧地帶領德國走出低谷,“重振雄風”。
從組閣的能動性和權力的掌控來講,28%和30%+是有本質區別的。“黑黨”選前最為擔心的是,如果拿不下30%+,即使成為議會老大,也可能不得不與另外兩黨聯合組成三黨政府。朔爾茨“交通燈”三黨執政的難度和痛苦,無疑給“黑黨”敲響了警鐘。
“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的中國哲理,在德國“交通燈”政府垮臺的實踐中得到了有趣的驗證。默茨不會不明白,在德國的政治生態下,一黨獨大是黃粱美夢,兩黨執政是最佳選擇,三黨聯合執政是自掘墳墓。
三黨湊在一起,整天吵架,一事無成,這是當代德國政治的慘痛教訓。朔爾茨三年多前上臺時躊躇滿志,三年后政府分崩離析,多黨聯合執政實驗失敗,默茨不想重蹈覆轍。
估計在開票的2月23日晚上,默茨和他的“黑黨”團隊在看到28%這個數字時,一方面為自己贏了大選而興奮,一方面也嚇了身冷汗,擔心被迫與另外兩黨聯合組閣的噩夢變成現實。
“黃黨”和“莎瓦聯盟”的意外出局,對“黑黨”是一種解脫。這兩黨雖得票率加總近9.4%,卻都被5%的門檻擋在了議會門外。另外,還有約4.6%左右的選票流向了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黨,它們同樣被擋在了議會之外。
門檻效應
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加起來近15%,獲得了這些選票的人進不了議會,但其得票所對應的席位卻留在了議會內,并被進入議會的黨團按相應比例瓜分。
正是這個原因, 使得 “黑黨”和“紅黨”加起來只有45%的得票率,卻可分得328個席位,占總席位630個的52%,超過了組閣所需的316席,“黑黨”拿下總理府不再需要第三個政黨的助力。
按理說,默茨應該可以松口氣了。但這只是表象。默茨的地位事實上空前虛弱。雖然他贏了選舉,但必須求助于“紅黨”把他抬進總理府。
“紅黨”當然知道自己的分量,雖然慘敗給“黑黨”,但只不過是讓出總理府而已。默茨要想拿走帥印,還得看他們的臉色。“紅黨”要是說“不”,默茨只能望洋興嘆。
然而,“紅黨”畢竟是百年老黨,可以說是千錘百煉,培育了大批具有國家情懷的政治家,像著名的德國總理勃蘭特、施密特和施羅德,就是他們中的典型代表。他們懂得什么是黨的利益,什么是國家的利益,不會因為狹隘的政黨利益而犧牲國家利益。換句話講,當國家因為自己拒絕聯合執政而面臨癱瘓時,很難想象“紅黨”會去看默茨的笑話,拒絕與他合作。
不過,“紅黨”會讓默茨付出高昂的政治代價。在政府部門權力的分配上,默茨的“黑黨”可能不得不作出重大讓步。不可以想象“紅黨”會按照“黑黨”的號令行事,接受按選票的強弱比例來分配權力。
權力分配
最有可能的是,“紅黨”會要求核心部門權力分配的對等。執掌經濟部是“黑黨”的核心訴求,如果默茨勢在必得,他可能不得不把他最為心愛的財政部,讓給“紅黨”來管轄。
朔爾茨政府的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是目前德國最受歡迎、人氣最旺的政治家。如果他繼續擔任防長,外長人選必然來自“黑黨”,最有可能出任下屆德國外長的人選當推拉舍特。他是“黑黨”上屆黨首,是當年敗在朔爾茨手下的“黑黨”總理候選人。
在政策層面,“黑黨”也必須對“紅黨”作出重大讓步,以換取該黨基層對聯合執政的支持。“紅黨”已經放話:黨的領導層將把是否與“黑黨”大聯合的最終決定權交給全體黨員,通過黨員表決來作出決定。
這樣一來,即使“紅黨”騰出總理府,未來德國政府的一半政策也將是現任政府政策的延續。它的直接后果就是,“黑黨”在大選中所承諾的許多“重振雄風”的政策會大打折扣。
未來的幾個星期,將是決定德國何去何從的關鍵時期。“黑黨”和“紅黨”之間組成聯合政府的談判將異常艱難,求變的“黑黨”和求穩的“紅黨”將會激烈地討價還價。沒有誰能保證這場選后的聯合執政談判一定會成功。
“黑黨”呼吁盡快組閣,聲稱急劇變化的世界不會等待德國;但期待剛剛敗下陣來的“紅黨”能迅速作出決定加入默茨領導下的新政府,無異于相信社會民主黨人會神仙般地克服心理障礙,能在一夜之間毫無痛苦地從政府主導者變成小伙伴。
因此,現在說德國新政府上臺后必將“重振雄風”可能還為時過早。這取決于“紅黨”會否誠心誠意地接受“黑黨”保守的難民政策和激進的企業減稅松綁政策,也取決于“黑黨”會否心甘情愿地向“紅黨”積極務實的對華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靠攏,還取決于兩黨能否迅速達成共識,大幅擴充軍備,逐步擺脫對美軍事依賴,聯手英法推動歐洲的“戰略自主”向實質性方向發展。
大選結束了,朔爾茨即將下臺,默茨就要上任,但德國的未來仍是一個未知數,“重振雄風”尚需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