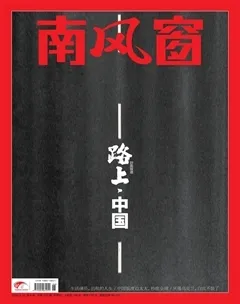中醫與鄉愁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一種醫療手段,更是一種文化、一種哲學、一種對自然和生命的深刻體驗和文化象征。而鄉愁作為一種復雜的情感體驗,不僅是對故鄉的懷念,更是對故鄉文化、生活方式、自然環境、人際關系的懷念,是一種情感紐帶。
在文化、情感、哲學等諸多方面,中醫和鄉愁之間有著復雜而微妙的聯系。二者相互交織,互為表里,相互促進,形成一種特有的文化和生活現象。
遺憾的是,學界對這一現象的關注和研究卻極少,筆者不揣淺陋,試以論述。
中醫文化與鄉愁情感
中醫的文化之根來自中國古代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醫以研究自然整體狀態的人的生命現象為宗旨,來論證生命和疾病的發生、發展和轉歸。中醫文化是一種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文化,強調整體衡動的觀念,主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陰陽平衡。臨床上,中醫師借助其理論指導,運用針灸、草藥、氣功和推拿等手段來治療疾病,同時,中醫不僅治療身體疾病,更注重心靈的平和和調養。
鄉愁是一種對故鄉,對過去的生活懷念和情感寄托。它可以是對家鄉的自然風光、風土人情的懷念,也可以是對童年時光、往昔經歷的追憶。鄉愁作為一種普遍的情感體驗,也是一種文化認同和歸屬感的體現。在現代社會中,鄉愁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的反感和對傳統文化的追尋。
然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和現代生活方式的普及,中醫的傳承和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在快節奏、高壓力的現代生活中,人們又很不適應,希望回歸傳統,回歸生命的本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醫不僅是作為治療疾病的手段,更是一種生活哲學、一種文化的傳承、一種鄉愁的寄托。中醫正以其獨特的方式,為人們提供一片心靈凈土,讓他們在這里找到安寧和平和。
鄉愁是一種對過往美好生活的懷念,在中醫中,人們找到了與故鄉的聯系,找到了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式,它不僅致力于治愈身體的疾病,也致力于撫平靈魂的創傷,讓人們在高速變化的世界中找到一絲安寧和安定。
鄉愁情感在中醫(藥)中的體現
鄉愁情感在中醫中,是通過中醫文化的傳承和實踐來體現的。
首先是中醫的傳統養生文化,強調“治未病”,即通過日常生活的養生保健來防病治病,如煲湯、藥茶、氣功、食療、推拿和拔罐等來保障健康。這些養生方式既便捷又經濟,往往又是在家庭、鄉里形成習慣,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世代傳承。
其次,中藥材往往帶有濃厚的地域特性。所謂道地藥材,是經過中醫臨床長期優選,產于某特定地方的品優效好的藥材,如廣藿香(廣東)、淮山藥(河南焦作)、川貝母(四川西部)、云三七(云南文山)、烏天麻(云南昭通)、化橘紅(廣東化州)、春砂仁(廣東陽春)、柴胡(陜西、甘南)、石斛(安徽霍山)等等。道地藥材的療效確切,其味道/氣味和療效往往能勾起人們對家鄉的情感。對那些遠離家鄉的人們,這些熟悉的藥材不僅可以養身療病,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思鄉情緒。
再次,中醫有許多地域流派,這些地域流派的形成和發展,深受地理自然環境、當地文化傳統以及社會歷史背景的影響。比如,嶺南醫學流派是中醫藥文化與嶺南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重視脾胃調節,經方時方并用,喜用花葉,注重地域疾病譜情況,巧用道地藥材防病治病,并將湯、茶、藥膳與民眾生活保健相結合;新安醫學學派發源于皖南新安江流域(古徽州地區),因為徽文化的尊儒重教,該醫派以儒醫群體和世醫家族為特征,醫家林立、學派紛呈,有“固本培元”派、“時方輕靈”派、“醫學啟蒙”派等,并將易理引入醫學思辨,開創了“八綱辨證”理論。此外還有齊魯醫派(山東)、長安醫派(陜西)、吳門醫派(蘇州)等等。
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養育一方醫學,一方的老百姓則信賴一方的醫生。許多中醫地域流派的醫家都是名震一方的大家,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形成巨大影響,又對推動中醫學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許多中藥材的名稱也帶有濃濃的鄉愁味,讓人聯想起故鄉的景色、人情和記憶。例如:當歸、熟地、銀杏、相思子、益母草、知母、何首烏、白頭翁、遠志、懷山和杜仲等。當患者看到藥方中這些中藥的名字時,會產生熟悉而親切的感覺,心中會泛起暖意,得到安慰。
更有趣的是古代許多文人,把中藥名寫進詩詞以表達思鄉之情,既妙趣橫生,又意韻悠然。
比如藥名四季歌的《春》:“春風和煦滿常山,芍藥天麻及牡丹。遠志去尋使君子,當歸何必問澤蘭。”
還有大詩人辛棄疾的《滿庭芳·靜夜思》,一連用了25味中藥材名,抒發其思念家人、思念家鄉的情感。最后一句“當歸也!茱萸熟,地老菊花黃”飽含著濃濃的鄉愁。
南宋名臣洪皓出使金國被扣留荒園十五載,堅貞不屈,他用中藥名寫了一首著名的思鄉愛國詩:“獨活他鄉已九秋,剛腸續斷更淹留。寧知老母相思子,沒藥醫治盡白頭”。
文藝作品中的中醫與鄉愁
文藝反映生活,反映時代的面貌和特征。在許多文學藝術作品中,中醫與鄉愁常常交織在一起,形成獨特的情感表達和文化符號。
比如電視劇《大宅門》,講述了一個著名中醫世家幾代人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家國情懷的故事。電視劇播出后在國內外引起廣泛反響,喚起人們對中醫藥文化的熱愛和對家鄉的情感。
華裔作家譚思美的小說《喜福會》,通過中藥材和中醫治療方法,展示了華裔家庭對傳統文化的懷念和傳承;京劇《白蛇傳》中,白娘子為救許仙,偷取靈芝,這一情節不僅展示了中藥的傳統療效,也表達了白娘子對許仙的深厚情感和對故鄉的思念;電影《我不是藥神》通過描寫一個普通人為救治病人而走上販賣藥品的道路,揭示了中藥材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和復雜性。影片中許多情節通過中醫藥材,表達人們對故鄉、對親人的深厚情感和責任。在名畫《清明上河圖》中,明代畫家仇英,描繪了宋代汴梁多處中藥鋪和醫者的形象,這些細節不僅展示當時的社會、生活,也反映了人們對傳統中醫文化的認同和懷念。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經典之作,書中有大量中醫藥和鄉愁的描寫。女主人翁林黛玉遠離家鄉,寄居賈府,多愁善感、體弱多病、藥不離身,是典型的憂郁型性格,她經常對著藥材、藥湯發呆發愁,她愁自己的身世,思念自己的家鄉。所以她的“病”一半是病、一半是鄉愁。甚至作家張愛玲說《紅樓夢》里的大觀園所營造的就是人類的故鄉伊甸園。
現代藝術作品中,中醫元素也經常被用來表達鄉愁和文化認同。例如,藝術家蔡國強的裝置藝術作品《藥山》,通過大量中藥材的堆積形成一座象征性的“藥山”,以展示中醫藥文化的豐富性,并表達對故鄉和傳統文化的深深懷念。
全球化視野下的中醫與鄉愁
中醫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應用。
我國人口第一波大的出國潮是19世紀中葉的下南洋,當時大批閩浙潮汕沿海地區的人們去東南亞討生活。由于東南亞地區氣候炎熱,瘧疾、霍亂流行,缺醫少藥,加之水土不服,對中醫藥等救治方法的需求增加。隨著南遷華人的增多,中醫藥成為當地華人社區主要的健康保障手段。專門到東南亞謀生的中醫師也逐漸增多,中醫藥文化在當地的影響與日俱增。在新馬泰等地中醫藥聯合會或中醫師協會、善濟醫院、普救善堂等中醫院相繼成立。同時,華人經營的中藥材店鋪在各地開業,中國與東南亞的中藥材貿易也大幅提升。
長期以來,中醫藥為保障東南亞華人華僑的醫療健康做出巨大貢獻,同時也作為文化紐帶把他們與祖國文化的血脈接通,緩解他們念土思根的鄉愁情緒。同樣,在北美、歐洲和澳洲等地,華人聚居區如唐人街上都有中醫診所和中藥店鋪,他們長期為當地的華人華僑、留學生服務,選擇到中醫診所和藥鋪尋醫購藥,既是基于對中醫中藥針灸等傳統療法的信任,也是他們對祖國傳統文化的尋根。
全球化背景下,中醫文化的傳播也會導致文化沖突。電影《刮痧》講述了一個中國家庭在美國用刮痧的方式給孩子治病的故事,因孩子和同學打架被警察發現了孩子身上的痧淤,便認為他們虐待兒童,要剝奪他們對孩子的撫養權,引發了一場沖突和法律糾紛。最后在親友、鄰里和學校的幫助和家庭成員的努力下,糾紛得到化解。刮痧不僅是一種獨特有效的中醫治療手段,也是電影的關鍵情節,更是寄托文化認同和鄉愁情感的象征。
中醫與鄉愁的相互作用
中醫與鄉愁的交織互動,是我國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二者的相互作用體現在文化認同、情感寄托和心理療愈等多個層面。
首先,中醫是鄉愁情感的根源和載體。快速、繁華(忙)、喧囂的城市生活,切斷了人與自然的聯系,也切斷了人們與傳統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聯系,使得人們變得煩躁、疏離、精神空虛沒有歸屬感,即得了所謂的城市病或現代病。而中醫無論是在文化認同、情感寄托還是診療方法上,都是治療現代病和城市病的有效途徑。通過中醫人們能夠找到與故鄉、與自然、與傳統文化的聯系和情感寄托,從而勾起鄉愁,緩解鄉愁。
其次,鄉愁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醫的傳承、發展和傳播。“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隨著綠色環保主義的興起和休閑理念風行,鄉愁情感已成為現代人的一種普遍情感,人們面對嘈雜而喧囂的都市生活產生厭倦,向往回歸自然、回歸鄉村、回歸傳統。這時,中醫對這些都市人來說可以作為一種連接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橋梁,給他們提供身體上的治療,提供心理上的熟悉感和慰藉。
最后,中醫與鄉愁的交織促進中醫文化的海外傳播。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中國人走出國門,留學、經商、打工和移民日趨增多。目前,留居海外的華人華僑遍布世界各地,他們遠離祖國和家鄉,面臨著文化和身份的認同問題和情感的孤獨。他們用中醫藥維護健康的同時,也把中醫藥文化帶到居住國,并使不少外國人接受和相信中醫。
中醫與鄉愁情感的交織與互動,有助于我們在追求科技與效率的同時,記住那些讓我們心靈得以安寧的東西,那些與過去、與自然、與生命本身相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