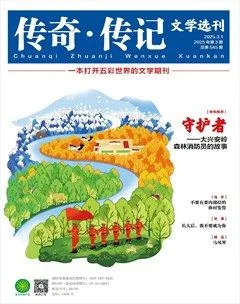皮影二
韓虎讓人討厭,戲間休息,他鉆進后臺摸鐃摸鈸,動簽子,嬉皮笑臉地,攆都攆不走。哪里有半點兒成年人的莊重穩當嘛。
每次演皮影戲他都來。鑼鼓未響,他就在戲場就座。戲開演后,他嫌在白紗前看得不過癮,還擠到幕后,看藝人將簽兒上翻下撩、左杵右抖。激動起來,他也跟著手舞足蹈。戲演結束,他搶著拔電線、收音箱、整戲筐,礙手礙腳。善存師傅撥開他說:“趕緊滾蛋。五十剛出頭的年紀,正是家里的好勞力,別在這兒游手好閑嘛!”
善存師傅是皮影戲非遺傳承人,縣城唱影戲的一把手,戲班的臺柱子。
皮影戲興于唐代,元代傳至西亞和歐洲,盛于清代,可謂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可近些年,皮影戲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但善存師傅不信這個邪,他要求戲班:“沒有觀眾也開戲。”傳了多少代了,好東西得留下嘛。
“要是真沒人看呢?”有人打趣。
“那就給老天爺演!”善存師傅心想,咋能沒人呢,不是還有韓虎嗎?就算沒有討厭的韓虎,也能雕皮子嘛。
將劇中人物在牛皮上鏤刻出面目形狀,填染顏色,串聯部件制作成皮子,本身就是藝術品。家當齊著,技術全著嘛。
時代變化太快啦,眨眼間劇團一個接一個沒了。不說演皮影戲,就是看皮影戲的也沒有幾個了。都去刨錢了。白天刨,晚上回來,想第二天怎么刨。
善存師傅觀察著呢,說是不景氣,但皮影戲還是有人看的,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進了城,對新潮的娛樂不感興趣,除了抱孫子帶孩子,沒有其他事情打發時間,皮影戲慢慢聚集出些觀眾來。老人們聽腔兒看影兒,圖的是消磨時間,懷念過去的味兒嘛。
這讓善存師傅高興。他領著戲班在文化廣場演戲,一周一次,棒打不挪。演到精彩處,稀稀拉拉的觀眾熱烈鼓掌,戲班演得更來勁兒。
晚上呢,善存師傅領著戲團團員雕皮子。嵌在框子里掛上墻,那是個趣兒嘛。
這次更不一樣,觀眾里添了幾張陌生面孔,還有個年輕人,多難得啊。善存師傅對戲班說,一定要把他們牢牢吸引住!
可是這當口兒,善存師傅在回家路上摔了一跤,胳膊折了。
演影戲全靠兩只胳膊挑簽子嘛,折了胳膊怎么挑簽子?
戲班藝人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讓皮影二上。”
皮影二就是討人厭的韓虎,次次都來,時間久了,戲班的人都叫他皮影二。皮影一是誰?當然是善存師傅嘛。
讓皮影二上,善存師傅堅決不同意。為啥?韓虎正值壯年,上有老下有小,是撐家的柱子。現在演影戲可是一分錢掙不著,還要貼賠大量時間學技術,記唱詞。戲班人少,還得兼敲鑼鼓鐃鈸。自己的三個哥哥就是顧著養家,先后放棄了嘛。把韓虎這個撐家的柱子拉來弄這不刨錢還要出錢付電費、置買“家當”的營生,是害人家嘛!
可是又不能不演,善存師傅一咬牙:“他挑簽子,我唱。傷好了攆他走嘛。”
這周演《兄妹開荒》。鼓梆子先響了三下。這是提醒聽戲的停下喧囂,演戲的準備好手腳嘛。善存師傅看看韓虎。韓虎一頭的汗,也斜眼瞟他呢。
“你又不是沒鼓搗過。”平素戲班小憩,韓虎偷偷拿了簽子比畫來比畫去,善存師傅沒少瞪他。
“我怕……怕壞了師傅的名聲。”
“我不是你師傅。”善存師傅踢踢韓虎的腳后跟兒,“腳扎穩,胳膊放松嘛。”
鼓點起來,善存師傅開了口:“雄雞雄雞高呀么高聲叫,叫得太陽紅又紅,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炕上做呀懶蟲。”
韓虎左手的簽子挑動“哥哥”的身段。
善存師傅繼續唱道:“扛起鋤頭上呀么上山崗,上呀……”看到韓虎手中晃動“哥哥”的草帽,肩上的鋤頭卻歪了,他急忙要去糾正,卻不由得“呀”一聲低叫。胳膊打著石膏,一伸手就鉆心地疼嘛。
“上呀么上山崗,崗上好呀么好風光。我站得高來望得遠,那么咿呀嗨。”韓虎吼著嗓子接上,把善存師傅那“呀”的一聲掩蓋了。
“咱們的邊區到如今,成了一個好呀地方,那哈咿呀嗨嗨哎嗨。”
哇,這個討厭的家伙會唱嘛,善存師傅瞪大了眼睛:唱念做打一體。只道是他會舞弄個簽子,沒想到還真藏著副好嗓子嘛。
蒼勁有力的二胡旋律中回響起韓虎粗獷利颯的唱腔,那明明是練過的嘛。
善存師傅悄悄挪步到了觀眾堆里。
紗幕上,哥哥妹妹賣力地開荒,深情地歌唱。
觀眾一齊鼓起掌來了,看戲的年輕人也熱烈地拍起掌。
善存師傅傷好后舉辦了收徒儀式,賜了韓虎藝名。儀式上,韓虎呈出一個筐子,說:“妻子、兒女都很支持我,給我買了牛皮、刻刀、顏料。”善存師傅打開,里面是韓虎一筆一畫抄的幾厚本唱詞,還有一摞摞雕了半截兒或者已經雕好了的皮子嘛。
一年后,省城非遺文化調演,表演名單里有影戲班。善存師傅在回執主演一欄,莊重地寫下三個字:皮影二。
這次他沒有帶“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