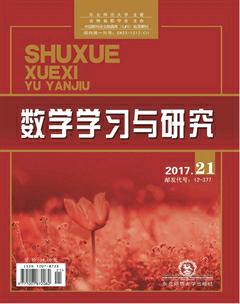淺談高中數(shù)學(xué)中學(xué)生創(chuàng)新思維培養(yǎng)模式
馬婷

素質(zhì)教育的出現(xiàn)和不斷深化改革,面向全體學(xué)生,要求教師重視學(xué)生創(chuàng)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學(xué)生創(chuàng)新精神的培養(yǎng),在高中數(shù)學(xué)教學(xué)當(dāng)中,顯得尤為重要.由于數(shù)學(xué)學(xué)科本身的基本特性和相關(guān)性質(zhì),對于學(xué)生創(chuàng)新精神的要求,也隨著時代的進(jìn)步而逐步提升.
一、鼓勵學(xué)生交流,尋找創(chuàng)新靈感
學(xué)生創(chuàng)新精神的培育,不僅需要得到教師的高度重視,而且還需要學(xué)生具備一定的創(chuàng)新靈感.創(chuàng)新靈感的獲得,才能夠讓學(xué)生在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如魚得水、得心應(yīng)手.學(xué)生創(chuàng)新靈感的激發(fā)和培養(yǎng),勢必需要教師采取相應(yīng)的教學(xué)方法和手段.對于學(xué)生而言,許多創(chuàng)新靈感的獲得,與交流和溝通具有莫大的聯(lián)系.在學(xué)生的互相交流過程中,學(xué)生能夠從彼此的交流之中,獲取一些關(guān)于創(chuàng)新元素的相關(guān)靈感,同伴或同學(xué)一句簡單的話語和不明顯的提示,都可以給學(xué)生創(chuàng)造獲取創(chuàng)新靈感的條件和基礎(chǔ).由此可見,在培養(yǎng)學(xué)生創(chuàng)新精神的數(shù)學(xué)課堂教學(xué)中,教師不能忽視對學(xué)生交流和溝通能力的提升.教師可以采取分組討論教學(xué)的模式,給學(xué)生一個基本的出發(fā)點和中心點,讓學(xué)生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深入的討論和思考,并在積極創(chuàng)新中完成學(xué)生對數(shù)學(xué)知識的學(xué)習(xí).
比如,以“統(tǒng)計與概率”中的抽簽法為例,分析教師如何通過鼓勵學(xué)生交流的方式,來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從而提高學(xué)生整體的數(shù)學(xué)能力和豐富學(xué)生的基本數(shù)學(xué)思想.對于抽簽法,單單憑借教師的講解,未免顯得太枯燥無味.為了提高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積極性,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數(shù)學(xué)興趣,教師可以采取分組教學(xué)的方法.圍繞抽簽,教師可以給出一個問題:“抽簽法的優(yōu)點和缺點各是什么?請在小組當(dāng)中積極討論,并親身驗證抽簽法.”在這樣的問題背景下,學(xué)生勢必會絞盡腦汁,想方設(shè)法尋找關(guān)于抽簽法的基本理論概括和抽簽法的過程探究,學(xué)生在對抽簽法的不斷探究中,最后會慢慢挖掘出自身的創(chuàng)新因子.特別是在小組的同伴之間進(jìn)行交流和溝通時,大家各抒己見,你一言我一語,這為學(xué)生創(chuàng)新靈感的獲得,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通過小組教學(xué)的模式,給學(xué)生一個問題,讓學(xué)生以問題為核心,在小組中進(jìn)行交流和討論,必要時做出一定的實踐創(chuàng)新,來加強(qiáng)和鞏固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這在高中數(shù)學(xué)教學(xué)當(dāng)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義.
二、倡導(dǎo)學(xué)生實踐,培養(yǎng)創(chuàng)新精神
實踐出真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然而,實踐還有一些其他的作用,在實踐中,往往能夠促成學(xué)生創(chuàng)新精神的培養(yǎng).實踐,意味著動手,暗示著學(xué)生具有獨立的思考空間和時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師的指導(dǎo)性原則和學(xué)生學(xué)習(xí)主體性的基本要求.在高中數(shù)學(xué)課堂中,為了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教師可以采取倡導(dǎo)學(xué)生實踐的方式,以學(xué)生動手能力為基本出發(fā)點,著重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
比如,以“定義域”相關(guān)的數(shù)學(xué)題目作為典范,來探究學(xué)生實踐能力對于創(chuàng)新思維培養(yǎng)的重要性.眾所周知,數(shù)學(xué)題目的一題變多題,是高中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中的家常便飯.學(xué)生在掌握了一個基本題目時,教師可以給學(xué)生布置任務(wù),讓學(xué)生在原有題目的基礎(chǔ)上,對數(shù)學(xué)題目進(jìn)行擴(kuò)充,將一道題目變成多道題目,并鼓勵學(xué)生完成對改編題目的解題探究.如,數(shù)學(xué)題:f(x)=mx2+8x+4的定義域為R,求m的取值范圍.教師可以根據(jù)這道題,有針對性地鼓勵學(xué)生進(jìn)行題目的變形,著重提高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對于這道題,有很多的題目變形,如,變形一:f(x)=log3mx2+8x+4的定義域為R,求m的取值范圍.變形二:f(x)=log3mx2+8x+4的值域為R,求m的取值范圍.從一道簡單的數(shù)學(xué)題中,學(xué)生可以變形出多道相似的數(shù)學(xué)題.這不僅提高了學(xué)生的數(shù)學(xué)能力和綜合的數(shù)學(xué)解題素養(yǎng),而且還在更深層面培養(yǎng)了學(xué)生的數(shù)學(xué)創(chuàng)新精神.
倡導(dǎo)學(xué)生積極實踐,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這是在高中數(shù)學(xué)教學(xué)課堂中,為了培養(yǎng)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教師可以采取的方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也是培養(yǎng)學(xué)生創(chuàng)新精神的基本前提和條件.
三、采用微視頻教學(xué),提高學(xué)生創(chuàng)新能力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科學(xué)技術(shù)的日新月異,微視頻教學(xué),已經(jīng)被廣泛應(yīng)用于數(shù)學(xué)教學(xué)當(dāng)中.微視頻的優(yōu)點和優(yōu)勢尤其突出,微視頻具有短小精悍的基本特點,而且便于教師的控制.數(shù)學(xué)學(xué)科是一門需要學(xué)生具備高度創(chuàng)新精神和豐富想象力的學(xué)科,微視頻在數(shù)學(xué)教學(xué)中的引入,很好地培養(yǎng)了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能夠提高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
比如,在“橢圓”的教學(xué)中,為了豐富學(xué)生的數(shù)學(xué)思想,提高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可以引入微視頻教學(xué).尤其是在橢圓離心率的學(xué)習(xí)時,大家都知道,離心率越小的時候,橢圓的形狀越圓,而離心率越大的時候,橢圓的形狀越扁.對于這個簡單的橢圓知識點的教學(xué),教師就可以采取微視頻的教學(xué)模式,把各種情況下的離心率變化情況和橢圓的形狀在微視頻中進(jìn)行一定的演示,從而提高學(xué)生想象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想象橢圓的形狀變化,對于學(xué)生創(chuàng)新精神的培養(yǎng),具有關(guān)鍵性的作用.
采用微視頻教學(xué),提高學(xué)生創(chuàng)新能力.這是在高中數(shù)學(xué)教學(xué)中,培養(yǎng)學(xué)生創(chuàng)新精神和提高學(xué)生創(chuàng)新能力的基本教學(xué)方法.在微視頻教學(xué)中,可以提高學(xué)生的數(shù)學(xué)想象能力和豐富學(xué)生的創(chuàng)新思維.
鼓勵學(xué)生交流,尋找創(chuàng)新靈感;倡導(dǎo)學(xué)生實踐,培養(yǎng)創(chuàng)新精神;采用微視頻教學(xué),提高學(xué)生創(chuàng)新能力.這是對于學(xué)生創(chuàng)新思維培養(yǎng)的三點教學(xué)嘗試,學(xué)生創(chuàng)新思維的培養(yǎng),在高中數(shù)學(xué)教學(xué)中占據(jù)非常重要的位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