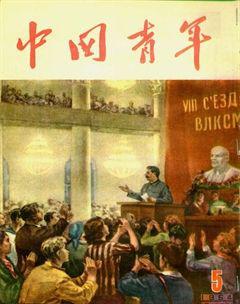吳琴的思想轉變
白金
這是經過四個月土地改革工作的鍛煉后,吳琴同志在我們小組思想總結會上的發言。從這篇自述里,可以看出一個知識份子從討厭農民轉變到熱愛農民的感情變化的過程。
學校宣布要同學們下鄉做土地改革,別人高興的嘴都并不攏,我自己心里卻感到很大的別扭。首先我和地方干部就合不來。我覺得他們土里土氣的沒見過大世面,又不講衛生。過去我在政治班學習,就和兩個從農村來的“土包子”處不好。其次,我聽說下鄉要做農民的“毛驢子”,心眼里也極不痛快。一連三四個月,天天要和那些又臟又笨的農民在一起,說話、吃飯、開會,總離不開他們。哎呀,這豈不是掉在垃圾箱里了嗎?想不去,又怕別人說我“落后”,一賭氣——“去就去!”
在第一次群眾大會上,我把準備好的“告農民書”和土地法大綱向農民講了一個慷慨淋漓。該死,講完了,誰也不鼓掌,有的竟呼嚕呼嚕的睡著了。區干部老馮很簡單的談了一下農民怎樣受地主壓迫,一個個都振起精神來聽。我真氣的不行。到貧農家里去,明明他家里窮得揭不問鍋,還說“沒苦”,天生一副賤骨頭!我一走到街
上,他們原都在有說有笑的蹲著曬太陽,看見我走到跟前,就唰的一下子都站起來啥也不談了。真是活見鬼!
晚上,我們工作組同志開會,別人都有材料,只是我一個人悶著沒話說。同志們給我提了意見:說我沒放下知識份子的臭架子,生活作風還有些高高在上的味道,因之不能和聚眾打成一片。我開始承認工農干部的作風是踏實,特別是在工作經驗和接近群眾方面,確實比我強。我決心向他們學習,可是心里多少有點不服氣,想道:“我非得追過他們不行。”
我搬到貧農李大娘家去住,和她睡在一個炕上。每天早起,我給她擔水,打掃院子。慢慢的她把我當成自個閨女一樣看了。一天半夜,大娘突然大叫起來,把我從夢里嚇醒,心里卜通卜通的直跳,“妮子,我看見我大小子了,他渾身是血……”她的聲音是那么凄慘可怕,從她的如泣如訴的敘述里,我知道李大娘的大兒子和侄子,都被本村大地主趙唐帶來的偽軍在夜間抓走,殺了扔在村西頭的井里。有個孤兒李藍群一次向我哭訴著說:十年前臘月初三,地主趙唐用刀砍了村里七個人。里邊就有他爹。今年五月初二,趙唐又領一連蔣匪軍,抓走了十一個貧農。用火燙,用繩子吊,用帶刺的木板毒打。他的娘和他媳婦都被打死。從一些農民的訴苦里,我體驗到地主的罪惡,同時,對于受剝削受壓迫的農民,也開始有了感情。
我能夠隨便在墻根下,地頭邊坐下來,和那些正在曬太陽抓虱子的貧農們擠在一起談天,我不再覺得他們“笨”和“臟”。正相反,我認識了他們的心靈比什么都潔白。我的小屋里,漸漸擠滿了人,老大娘、年青婦女、小孩子,還有老大爺和年青的農民,他們常把心眼里的話告訴我。李大娘盼望著能分上幾畝水地,分上一個紅漆柜子,以后還打算娶一房兒媳婦。十七歲的女孩子李金花對我說,她爹把她許給了地主趙大鳳的兒子,她不愿意,一定要解除婚約。
有一天,我到五里外一個村子去開會,已經晚上十一點了,一個人走黑道,有點阻寒,走出村子不遠,后面就有一陣腳步聲追上來,嚇得我一身冷汗,“誰?”“吳同志,等一等!”原來是村子里的糾察隊,一看天黑了,就自動的趕來接我,太陽一落就來了,直等到我散會。還有一次,老馮同志到縣里開會去了,我一個人在村里受了風寒,發燒很歷害,迷迷糊糊的說胡話,這可把老鄉急壞了,幾個老大娘黑夜白日的守著我,給我熬姜湯,煮掛面……。看我啥也不吃,李大娘急的成天啼哭 。臘月二十六晚上,雪下的有半尺多厚,貧農委員楊小保(五十多幾)和李北瓜雨人,胃著大風雪,連夜趕了十幾里地去給我請醫生。在路上,他們幾次跌到雪坑里。這些事情,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我們走的那天,開剛亮,他們就都來了。一個個都搶著替我背背包,他們把我圍得緊緊的,十幾雙手一齊伸了過來,你一把花生,她一把紅棗,制服口袋、背包、棉帽子……凡是能盛東西的物品,都給塞滿了。當時農民們那種熱情,使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我含著淚向他們告別。路上我默默地自己發誓,今后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缺點,提高政治覺悟,與工農群眾結合,做工農群眾的一個好勤務員。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