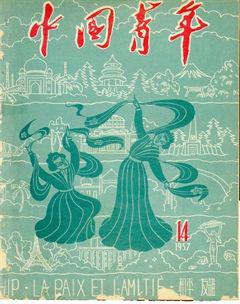斗爭正在進行中
雪琴
五月下旬,城市建設部萬里部長在全體干部大會上,作了整風動員報告,號召群眾大鳴大放,于是,這個機關里的一小撮興風作浪的右派分子就猖狂地行動起來了。該部城市建設出版社干部,右派分子錢輝煜(共青團員)在五月二十三日辦公廳召開的座談會上,首先在“幫助黨整風”的借口下,提出了自己的綱領性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九條意見。
九點綱領
她的九點意見中,露骨地暴露了她利用黨整風的時機,向黨進攻的陰謀。她污蔑黨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是“狂風暴雨”地整別人,而在這次整風運動中卻強調“和風細雨”,這是“厚己薄人”。她號召“大家一起來幫助黨糾正歪風”。如何來“幫助”呢?她公然提出要重新“對歷次運動作一總結”。她和許多右派分子一樣,把提“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免不了的”稱作是“庸俗公式”;說提成績是“甜酒迷人”,講缺點才是“良藥苦口”,以此來達到抹煞成績,夸大缺點的目的。線輝煜全面否定黨的成績,夸大缺點的矛頭,又集中在肅反問題上。她把1955年的肅反運動說成是在斯大林“愈向社會主義前進,階級斗爭愈加尖銳”的理論指導下的“實踐”。她認為1955年國際形勢趨于緩和,國內的主要矛盾也已經是落后的農業國和先進的工業國之間的矛盾,因而毫無必要進行肅反運動;又認為1955年肅反運動中所采取的方法,是“疑神疑鬼,捕風捉影”的“唯心主義”作法。她毫無根據地說肅反斗對的只有“百分之一”;并公然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申冤,認為“百花齊放”為什么胡風的“萬言書”就不能放?她污蔑在肅反運動中叫反革命分子或有歷史問題的人交待問題是“侮辱人格”,“施以精神極刑”,并提出“公民在未逮捕以前,不得進行斗爭”。當時右派分子儲安平的“黨天下”謬論還沒有發表,錢輝煜卻和他“所見略同”。她提出從全國范圍來看,各個大大小小崗位上都要安插一個共產黨員,讓他們當領導,真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懂原子時代科學的人當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不懂城市建設業務的人,當城市建設部的部長,不懂俄文的人,當專家工作科科長,這種現象遍天下皆是。”她認為黨的干部“大多數”都是“不學無術的人”,而“不學無術的人不能當領導”,應該“讓懂業務的人來領導業務”,黨委,黨支部或黨員則應該退出領導崗位,只能從勞“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監督工作的進行,做思想教育工作。”她認為這樣“工作效率一定會提高好幾倍”。她提出要改變“以黨代政或黨政合一”的現象。她要求“人事檔案公開。”她又抓住個別黨員的一些缺點,大肆攻擊,認為“共產黨員吃苦在先,享樂在后”,“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等名言,“說得好聽點,是沒有兌現的教條,說得難聽點,那簡直就是空話。”“評級時先提黨員,房子先給黨員住,補助先照顧黨員,犯了錯誤,也保密于群眾,為的是照顧黨的威信。”
以后,這些意見在機關黑板上公之于眾。在六月一日錢輝煜又作了公開講演,繼續宣傳她的反共、反人民的所謂“幫助黨整風”的綱領。
這些意見的實質是什么呢?突質上就是號召群眾狂風暴雨地向黨進攻;就是否定一切,打垮黨的政治威信;就是歪曲肅反運動,向肅反運動中被審查過的同志點火;就是要求釋放胡風,企圖為反革命分子撐腰,為今后的反動言行開辟道路;就是要求黨下臺,取消黨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就是把秘密供手送給敵人;就是挑撥黨群關系,把黨員在群眾中孤立超來。把這些意見聯系起來看,不是一個完整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嗎?
這樣說,是不是扣得太厲害了呢?為什么總是從最壞的地方去設想別人呢?為什么不多從好的方面去考慮考慮呢?難道這些意見中就沒有可取的地方嗎?這是當初在批駁錢輝煜的九條意見時,該部有些同志所想不通的。而當時錢輝煜也的確取得了一都分同志的支持。出版社團的支部書記就成了錢輝煜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由于團支部書記的叛變,有一部分團員在一時也曾迷失了方向。他們認為團支書干的事大概不會錯吧,于是也就跟著錢輝煜跑了幾步。當錢輝煜張貼了自己的九點意見以后,立即有人(其中包括共青團員)貼出大字報,表示同意她的意見。特別是她在肅反問題和黨的領導問題上的意見,曾經迷感了一部分同志。有些在肅反運動中被斗,對黨有意見的人,很同意他的看法;有些工程技術人員也同意她的“不懂業務,不能領導”的一些觀點。因此當她公開講演時,有人給她端水,還有不少人為她鼓掌。有些人還贊揚她敢于向領導提意見的“膽量”。
煽動群眾,趕走領導
當錢輝煜看到她的“九點意見”已經俘虜了一部分立場不穩的群眾以后,她就積極組織力量,形成一個以錢輝煜為首的向黨進攻的核心。他們主要目的是在政治上向黨進政,但為了爭取群眾,他們就首先抓住群眾有意見的一些具體問題,和個別黨員在生活作風上的一些缺點,來煽動群眾對黨的不滿。
房子問題,福利補助問題。是在整風初期,同志們意見提得比較多的問題都中絕大部分都是善意的批評,該部在這方面的工作上的確存在著一些缺點和錯誤。錢輝煜等右派分子就緊緊抓住這些問題,來煽動群眾。他們到處搜集材料,到處找岔,看誰住房多,誰多領了補助,只要是黨員,是老干部,就設法加以夸大、渲染、丑化。比如該部有一個處長,家屬都在上海,原來預備接到北京來,因而向行政處要了三間住房和一些家俱,但是家屬一直沒有接來,在當前房子緊張情況下,最好是先讓出幾間,等家屬接來后,再設法解決,但是那個處長沒有及時讓出房子。這樣做,對一個共產黨員來說,是有缺點的,可以提出意見,然而右派分子又是怎樣對待這個問題呢?當他們發現這個事例以后,興高采烈,他們立即寫了一篇題為“涂了漆的共產黨員”的大字報,張貼在機關大院內。文章一開頭,就煽動性她說:“同志們,住房為什么不夠,主要是特權階級(司局長一級)多占了住房”。看,她們攻擊黨的手法是多么卑鄙,把一個處長多占了兩間房子,就夸大為整個司局長一級干部都多占了房子,而且馬上給他們扣上了一頂帽子:“特權階級”;并且認為住房緊張的根源:就是因為這批“特權階級”多占了住房。
又如該部在分配福利補助金方面有些缺點,對個別老干部照顧過多。右派分子便利用章回小說的形式,寫了一篇“新官場現形記”,惡毒地謾罵了主管這一工作的人事處某處長,說他是“馬庇精”,拿“人民幣”當作“法寶”,去向那些負責干部“拍馬”。這樣寫還不夠,錢輝煜還作了這樣一個批語:“這決不是城市建設部中的偶然事件,行政處實際上就是首長們的公務班,這些忠實的仆人,哈腰磕頭,忠心耿耿,鞠躬盡粹,死而后已”。
他們活動的另一個目標,就是策劃趕走城市建設出版社的黨的領導力量。這個出版社是去年新建的,領導干部還沒有配備全,全社只有三個黨員負責干部:副社長、辦公室主任和出版部主任。這些右派分子根本看不起這三個領導干部。他們認為“領導”只要“業務領導”,這些黨員領導干部都是“不懂”“不學”又“管不了”的人,是不能領導他們的。只有他們這批人,懂得業務,可以來擔任各種領導工作。他們吹捧和他們合污的那個“團支書”,認為他有才能,懂業務,可當編輯室主任。在整風會上,他們瞪眼拍桌要副社長滾出出版社。會上只準發表和他們一致的意見,有不同的意見,他們就立即起哄。在一個短時間內,他們幾乎控制了他們所在的那個組。有的同志在回溯當時的情景時說:如果社會上不起來反擊右派,我們這個出版社就很難反起來。
三次論戰
為了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六月十二日下午,在城市設計院禮堂,召開了有兩千多干部參加的大辯論會。報名要求發言的有四十一人,其中支持錢輝煜的意見的,有七人,部分支持的有二人,反對的有三十二人。在這次會議上,兩陣擺開,明確了正面和反面意見的中心和觀點。在發言的九個人中,正面意見略占優勢,反面意見也未氣餒。
六月十四日,接著召開第二會,以錢輝煜為首的右派分子的意見集中在兩個問題上,即肅反問題和黨在領導問題,這是他們的核心問題,因而會議就集中在這兩個問題上展開尖銳的論戰。
關于肅反問題,城市設計院的一個共青團員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駁得右派分子啞口無言。
他首先批駁那些認為我國的肅反運動是在斯大林關于肅反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他說:在肅反運動中,我們的政策從來就是“有反必肅”,“有錯必糾”;肅反工作的指針就是“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而且在肅反運動中,又執行了更加慎重的處理方針。這些方針政策和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毫無共同之點。可是在爭辯中,有人說公安部羅瑞卿部長在肅反初期寫的文章中所說的“階級斗爭規律”是與斯大林的錯誤理論有關的。對這個問題,他又作了進一步的反駁。他重念了一遍羅部長的文章原文。羅部長在文章中批評了某些同志輕敵麻痹思想以后,指出階級斗爭的一條規律是:“革命的事業越前進、越勝利,而革命的敵人的報復破壞就必然越兇狠越加劇。”這樣說與斯大林的理論是沒有關系的。首先,這句話中只說了“革命的敵人的報復破壞必然越兇很、越加劇”,并沒有說“階級斗爭越尖銳”;相反,在同一篇文章中,羅部長就首先指出:“經過幾年來對反革命活動的鎮壓和其他方面的斗爭,國內的殘余反革命勢力是被大大削弱了,人民民主專政是更加鞏固了,社會秩序是更加安定了,……”并沒有說敵人越來越增多了。更重要的是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五五年初期寫的,當時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取得基本勝利,我國還處于過渡時期,這和當時蘇聯社會主義已經建成,斯大林還說愈向“社會主義前進,階級斗爭就越尖銳”的國內情況是完全不相同的。錢輝煜對當時我國國內情況的分析也是錯誤
的。這時,他又批判了錢輝煜從當時國際形勢趨向緩和,認為肅反沒有必要的觀點。他說:毛主席指出的“有反必肅”就是肅反運動的依據。國際局勢緊張,反革命可能猖狂些,局勢和緩,反革命分子并不等于就不活動了。而且,按一般規律,帝國主義“熱戰”打不成,就特別加緊“冷戰”和顛復活動。匈牙利事件就是一個例子。這就說明“有反必肅”的必要性。
接著,他分析了肅反的成績與缺點。他說,肅反運運中是有缺點的,例如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甚至錯捕了個別好人;在拘留某些嫌疑犯時,不完全符合法定手績等。但是無疑的,成績是主要的,從全國范圍來說,清除了一批暗藏在工人階級和人民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大大縮小了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的空隙;廣大群眾大大提高了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覺悟,大大發揮了革命斗爭和各種建設的積極性;鞏固了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保證了國民經濟恢復工作的完成,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前進。這三大成績是絲毫不能抹殺的。他又進一步指出,就是從城市建設都來看,成績也是主要的。他批駁了錢輝煜等認為部里斗錯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荒謬論點。他以他所了解的十個肅反斗爭對象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在這十個對象中,雖然只有一人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但是其他沒有逮捕的,也都是有問題的。在九人中,歷史上有罪惡有血債的反革命分子三人,厲史上的軍統中統特務分子三人,一貫招搖撞騙,長期偽造歷史的二人,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一人,就是這個人也做過偽軍官,解放后偽造學歷,并且有檢舉材料。這些事實說明未判刑、未逮捕的人,不一定就沒有反革命罪行,沒有做過壞事,只是我們的黨和人民對他們給以最大的寬恕,使一些該殺的沒殺,該捕的沒捕。所以不能只從逮捕的數字上來看肅反工作的成績和缺點。
在肅反運動中,曾經被作為審查對象的一位共青團員,更以自己親身的事實來無情地粉碎右派分子的誑言。他說他自己歷史上有問題,當過國民黨的義務警察,解放以后思想反動,資助過一個人去臺灣,認識過兩個特務。他認為組織懷疑他是完全有根據的。經過肅反,把問題弄清楚了,難道這不是成績,這是“疑神疑鬼,捕風捉影”嗎?他義正辭嚴地責問錢輝煜:“你自稱是好人,為什么怕肅反,你是替誰說話。”
關于黨的領導問題上,發言的同志們從兩方面駁斥了右派分子的謬論。勘測設計局的一個技術員駁斥了錢輝煜所謂“從全國范圍來看,各個大大小小崗位都要安插一個共產黨員,讓他們當領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說法。他首先例舉了很多事實,說明民主人士當副委員長、部長、司局長、校長等多得很,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他指出:共產黨是為了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最高利益不惜犧牲奮斗的黨:黨的這種性質和任務,就決定了黨非團結一切積極力量不可。早在一九二三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就確定了統一戰線政策,這一政策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各國兄弟黨都很重視。他責問右派分子,把“鐵的事實,成功的政策”,偏要說成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這是什么意思。
在規劃局工作的一個同志對這個問題也作了有力的批駁,他說根據錢輝煜的觀點,領導同志的業務等于“技術”,這種說法是非常片面的,他認為領導同志應該懂得業務知識,但更重要的是正確貫徹國家的方針政策。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作為一個領導同志,首先必須具有明確的階級立場。他所領導的全部工作必須符合整個國家的利益。他例舉了他自己的工作,他說,他是做城市規劃的,他們常常喜歡爭論城市建設采用什么標準,有人認為現在的標準低了,到底是高是低?看法很不一致,后來知道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房屋投資竟占8.8%,這樣高的投資比例,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再要求提高標準呢?中央提出“勤儉建國”四個字,就使許多同志的設計思想明確了,這就是黨的領導。作為城市建設部的部長,要貫徹勤儉建國的方針,就必須要有明確的立場,高度的群眾觀點。
他說:領導同志的業務,還在于集中群眾智慧,發揮群眾力量。任何一個領導同志即使是技術上的專家,也不可能代替全體工作人員。假定我們的部長是個規劃專家,他也不可能做出全國各城市的城市規劃。
根據錢輝煜的論點,業務就是技術,那么全世界也沒有人能當城市建設部部長。有誰既懂城市規劃,又懂建筑設計、給水排水,還要精通測量鉆探呢?
錢輝煜認為等共產黨把刀子交給別人以后,黨委和黨員還可以從旁“監督工作的進行”,“做思想教育工作”。他認為這種看法也是不對的。只有思想領導,只有政治領導,而沒有組織領導的保證,是不能實現工人階級的領導的。這樣實質上就否定了共產黨的領導權。
通過這些辯論,把右派分子的基本論點打垮了,他們的氣熄已經低落下來,群眾也能分清是非了。
在六月十五日的第三次辯論會上,對錢輝煜的其他一些論點,也都一一加以批駁,右派的理論徹底地批判了,這次論戰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在這次會上并著重提出了立場問題,要求大家站穩立場,堅決與右派分子劃清界限。
勝敗戰局已定,然而右派分子錢輝煜等人并不干心,他們又以另一個面目出現——裝著一付可憐相。她認為自己的意見只是有些尖銳、刻薄,基本上還是正確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的“片面”,“掌握資料不全面”,“主觀上完全為了幫助黨整風”,企圖再來迷惑一部分群眾。但是,情況已經變了,他們只是孤立的幾個人,廣大干部的認識提高了。
當然,三次辯論大會只是對右派分子的全面擊潰,要他們徹底繳械,還需深入戰斗,現在這場斗爭正在深入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