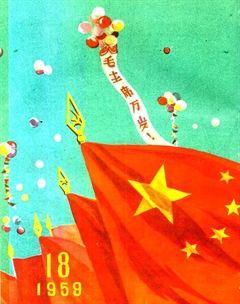牡丹江畔學飛行
韓明陽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我們一百多架各式飛機,以整齊的隊形,飛過天安門上空,接受毛主席和全國人民的檢閱。我們建國才兩周年,已經有一支人民自己的空軍了。
二日下午,我們接到通知參知加酒會,可以見到毛主席、朱總司令和其他中央首長。聽了這個消息,大家高興得鼓掌足足鼓了五分鐘。
酒會開始后,總領隊吳愷師長領著大家給領袖敬酒。我舉著酒杯,心簡直要跳出來。我們走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面前,說:“祝賀毛主席、朱總司令、劉副主席和周總理身體健康。”
“謝謝你們。”毛主席笑著說,并向左右看看其他同志,一面又繼續說:“我們有了空軍了。”這時我感到作為一個空軍戰士是多么光榮啊!
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樣也不能人睡。我的心自然地回到了空軍初建時的那些難忘的日子里……
那是一九四七年,在牡丹江,人民解放軍航空學校里,我們一百多名學員,靠著日寇遺留下來的四架英格曼式初級教練機學習飛行。因為人多機少,我們分成甲乙兩班,讓甲班學員先飛。半年過去了,他們還沒有放單飛,什么時候能輪上我們呢?
一天,常乾坤校長向我們乙班學員宣布了校黨委的決定:讓我們直接從高級教練機開始學飛行,不飛初級教練機和中級教練機了。這真是一個大膽的決定,也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過去日本人在這種高級教練機上學飛行,必須在初級和中級教練機上飛過三四年,而我們文化低,底子差,一下就飛這個。偽滿留下來的技術人員譏笑我們這些“土包子”簡直是開玩笑,但所有這些猜疑,很快就被我們打破了。
我們和教員見了面,他們有些是抗戰期間黨派到新疆盛世才辦的航校學飛行的,這是我們黨為建設空軍撒下的第一批種子;有些是起義軍官。
我和林虎、劉玉堤、王洪智編在一組,教員就是吳愷隊長。他不但飛的很好,而且是一個久經鍛煉的老共產黨員。我們組的飛機是108號。當我們看到這架“九九”高級教練機時,真吃了一驚。飛機滿身不但有厚厚的油泥和塵土,而且有許許多多補綻。有的補綻一個接一個,還有的下邊一個大的上邊又補上個小的。我們好奇地數起補綻來,整整一百二十五個。
飛機這樣舊,能飛嗎?我想著,但是沒說出口,因為我明白,這就是我們唯一的飛機,比這再好的是沒有了。
午后,我們四個人找了兩付水桶,弄了些破襯衣和舊軍衣。王洪智用自己的津貼買了四五塊固本肥皂,趁大家還休息的時候,偷偷地跑到機場擦洗飛機。吳隊長也參加了。從此給飛機“洗澡”就成了一個制度。我們的108號,在我們長年的勞動中,它永遠是那樣的清潔和年輕。
我們先在地面進行飛行動作的操作實習。不久,就被教員帶到空中作“感覺飛行”了。過去我們熟悉在操場上立正、稍息,在山川平原上打仗;如今我們要到天空中學本領,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早上,三點鐘就起了床,天空還是一片漆黑。那天早餐也變了,小米飯換成了饅頭,在大碗的粉條白菜里還有星星點點的肉塊,就象過節會餐一樣。
機場上機械員忙著準備飛機,教員和飛行員就準備加油。那時汽油對我們來說比金子還貴重,加油時特別小心,用手捂著,生怕撒到外邊,三十五立特的油,足足加了半個鐘頭。
飛行開始了。第一個飛行的是劉玉堤,他和吳隊長走上了飛機。我和機械師耿得水同志在發動機右側搖著大搖把,就象現在冬天發動汽車時那樣,一圈一圈地搖。由于天氣很冷,不易起動,搖了好久,螺旋漿只嗚嗚轉了兩圈就不動了。林虎、王洪智插上手,我們四人搖了三次,發動機才吼叫起來。飛機滑到了起機線,我們親愛的108號飛向了蔚藍的天空。
飛機降落了,第二名輪到我。我個子矮,就帶著一個早準備好的稻草墊子進了座艙。飛機重又滑上了跑道,象箭一樣向前射出去。我感到挺新奇,沒有想到那個墊在屁股下邊的破草墊,被風一吹,碎稻草和麈土飛滿了全座艙,迷的我的眼睛一個勁地流淚,什么也看不到,我忙著擦眼淚。這時飛機已經在吳隊長的操縱下高高地飛翔在天空了。那彎彎曲曲小河,那航駛在牡丹江上的帆船,……好似都向機翼下飛來。我正看出神,背后突然被觸動了一下,我回過頭,只見吳隊長的右手伸著食指前后擺動,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讓我試驗試驗操縱。我高興地用手抓住駕駛桿,蹬
緊方向舵。但是飛機一到我手,就象一匹不聽話的野馬,忽高忽低,忽快忽慢,兩只翅膀左上右下象喝醉了酒似的。我吃力地作完兩個轉彎,飛機又掌握在教員手里。我聚精會神地看著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是那樣地柔和自然,我恨不得能及早象教員這樣,掌握住這門復雜的飛行技術。
我們這里林虎進步最快,第一個放了單飛,唯獨我進步最慢。尤其在每次著陸前,保持一米平飛的時候,高度老是看不準,不是高了就是低了,因而出現一些危險動作。
有一次飛行隊教員、學員都乘一輛大卡車回宿舍去,我正為著今天又沒有能飛好而難過發呆,突然吳隊長用手往前面一指,象發現什么意外似地對我說:“向前看,汽車前方40——50米遠的地面,反映和飛機在著陸前一米平飛時一樣。我一看,確實不錯,從此每坐飛車我都擠到前面看地面,很快就突破了一米拉平的這個難點,被批準放單飛了。
這是難忘的一天!座艙里在教員的位置上放了一個五十公斤的沙袋。教員又親手在機尾上結了塊小紅布,這是新飛行員放單飛的標志,別的飛機在空中都要為它讓路。教員半年來的心血現在要開花結果了,吳隊長是那么的高興,又是那樣的不放心。當我把飛機滑行對正跑道以后,他還是一直跟著我,站在機翼上再三囑咐。
“飛吧,祝你成功!”教員最后很有信心地說。我一聽,沒有來得及看信號員白旗,便急忙做起飛的動作,我的心好象要跳出喉嚨似的,兩眼直祖著的方,加滿油門,筆直一線地騰空而起。這時飛機在我手里,不再象是不聽話的野馬,而是那樣操縱自如。我真的會飛了,我感到興奮和自豪。我感謝黨,感謝同志們。
飛機滑回停機線,吳隊長迎面走來,老遠伸著手,放開嗓子笑著說:“很好!很好!”同志們也圍過來向我祝賀,這時我才發現教員走路腿一跛一跛的,怎么搞的?起飛前他站在機冀上還是好好的,十幾分鐘后為什么就壞了呢!一問,才知道,原來是當我起飛加油門時,教員還沒從機翼上下來,我松剎車,飛機向前一跑,就把他從機翼上摔下來。我望著教員,不知道該說什么才好,真悔恨自己為什么那樣粗心。
單飛以后,課目一天天地加深。1948年正當麥黃的季節,有一次吳隊長坐在后邊的駕駛艙里,檢查我的技術。正當飛機爬高的時候,“拍!拍!”發動機放了兩個“炮”,螺旋槳轉動變慢了。糟了,飛機有故障!“向后轉!回機場著陸!”我想,但馬上又否定了這個念頭。因為這時離地面才100公尺!向后轉是危險的。“直線向前滑?”前方是一片大水坑,也不行。在這緊張的關頭,我手忙腳亂起來,眼看就有跌撞在地面上的危險。這時只覺得后座艙的吳隊長迅速地將飛機向右轉了30度,正對準一塊平坦的麥田滑去。我的心安定下來了。我松開駕駛桿,讓吳隊長操縱,我幫他放下了襟冀,飛機安全地落在麥田里,人機無損。我們為這次安全的迫降而高興。
吳隊長事后總結這次迫降事故說:“緊急的情況可能一輩子也遇不到,但對一個飛行員來講,要常準備面臨緊急和危險的情況,它最能考驗一個飛行員的勇敢和技術。
在器材缺乏,飛機破舊的惡劣條件下,我們就這樣頑強地學習著飛行。我們終于在種種考驗中逐漸成長起來。
這一年,國民黨的飛機天一亮,就從沈陽起飛,一批一批來到我們機場上空輪番轟炸和掃射,直到天黑前兩小時才竄回沈陽去。天天都是如此。那時我們一缺乏高射武器,二沒有可以用來打仗的飛機,在這種情況下,敵人就把普通運輸機也裝上炸彈對我們的學校.村座無目標地亂扔。我們氣的眼發紅,唯一的念頭就是要迅速學好技術,將來成為一個保衛領空的空軍戰斗員。
敵人的轟炸怎能難倒我們?!我們把六個機堡(放飛機的地方)偽裝成了小樹林,機場上再也看不到飛機了。我們利用每天早上敵機從沈陽起飛,但還沒有到達我們上空以及天黑前他們離開我們上空回沈陽的各兩小時,來進行訓練。這真是與國民黨搶時間。人民多么迫切需要一支自己的空軍呀!
萬一在空中和敵人遭遇,我們的飛機不但速度小,而且又沒有炮,怎么辦呢?我們學會了一種特殊技能——超低空飛行。飛機飛的特別低,如果迎面遇到山峰就要升高爬過去,遇到山溝就要轉彎鉆過去。有時兩邊的山峰遮住了陽光,山峰的影子就時時從座艙蓋上面掠過。這樣的練習進行了好多次,每次著陸后不但汗流浹背,而且兩只眼睛酸痛。我們當時每一個飛行學員,都經過這種特別本領的訓練。我們用這套辦法對付著瘋狂一時的美造蔣機的攻擊,把它叫做空中打游擊。正因為這樣做,訓練從來不曾中斷過。一批批的飛行員,在打游擊中不斷成長起來了。
1948年底,我們畢業了。吳隊長和林虎、劉玉堤,王洪智都到新的飛機上去了,我被留下當教員,仍然使用著這架有著一百二十五個補綻的“九九”高級教練機,將我的飛行技術教給那些和我一樣從陸軍調來的同志。
以后,航校來了大批新的飛機,裝備著噴氣式飛機的飛行部隊也一個個接連建立起來了。現在距我們兩百多名飛行員飛過天安門受檢閱的日子,又有八年。八年來在黨和毛主席培養下,我們有了一支強大的空軍。每當我們駕著最新式的噴氣式飛機,飛翔在祖國的天空,保衛著祖國的時候,我就不禁想起我們在困難中成長的那些難忘的日子,并感到萬分的激動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