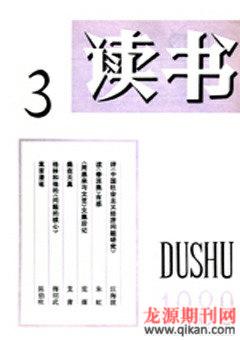茅 盾
清·李調元的《雨村曲話》評明·屠隆(赤水)所作《彩毫記》(是以李白作為主人公的),說“其詞涂金繪碧,求一真語、雋語、快語、本色語,終卷不可得。”這個評語大致公平。或謂《彩毫記》第二十折“乘醉騎驢”敘述李白騎驢過華陰縣衙門而不下驢,門卒與之爭吵,縣官命喚李白進,問是何等樣人。李白答:“我是海上釣鰲客。”縣官又問:“以何物為鉤線?”李白答:“我以四海為魚池,三山為釣臺,虹霓為絲,明月為鉤。”縣官又問:“以何物為餌?”李白答:“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這一段問答,可算得“雋語”罷。但是這段問答是抄來的。
南宋的曾,編了一部《類說》;這是從二百五十二種筆記小說里輯出來的(書中引有此二百五十二種書目),其中一部分,宋后就亡了。《類說》成書于紹興六年。曾字端伯,號至游居士,初為尚書郎,直寶文閣奉祠。除《類說》外,他又編有《高齋漫錄》、《樂府雅詞》。
《類說》卷二十一有《釣巨鰲客》一條全文如下:“張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李盛曰:‘以何為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鉤?曰:‘以月為鉤。‘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此據解放后影印明·天啟刊本)
《類說》此條云出《大唐遺事》,可知是唐代的事。但《彩毫記》比《類說》此條多了“以四海為魚池,三山為釣臺”兩句。又《彩毫記》說是“虹霓為絲”,而《類說》卻是“以虹為竿”。《彩毫記》是“明月為鉤”,《類說》僅只一“月”字。《彩毫記》提到“虹霓為絲”,卻沒有了釣竿。
李紳,字公垂,元和進士,擢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宗時累官尚書右仆射、門下侍郎。紳為人短小精悍,號“短李”。這是《類說》的“以短李相為餌”的由來。李紳有詩集名《追昔游》三卷,雜詩一卷,《全唐詩》合編為四卷。
但是明刊本《類說》此條的張卻錯了,應是“張祜”。解放后,古典文學出版社于一九五七年鉛印《唐才子傳》,說是“用日本天瀑山人刻的《佚存叢書》中的十卷足本重印,并校正了其中一些明顯的脫誤,所校均在句下加注說明。另附《指海》本校記。”此所謂《指海》是清·道光年間錢熙祚所刊的類書,其第八集為《唐才子傳》,也是以日本天瀑山人活字印本為底本,又用《四庫全書》本勘過,識其異同。《指海》的《唐才子傳》正作張祜。奇怪的是:古典文學出版社既把《指海》中的《唐才子傳》也校勘過,已在附錄中說“本篇‘字,指海本皆作‘祜”,卻又為什么不進一步查明到底是張還是張祜。
查《全唐詩》中并無張,故知明刊本《類說》的“”字是錯的。但究竟有沒有張其人呢?我在商務印書館于一九二一年初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查到了兩個張(見該書頁九四九)。第一個張,是后魏·安定人,字安福。父成坐事誅,充腐刑。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以供承合旨,寵冠諸閹,累官尚書左仆射,進爵新平王(大辭典張條下注)。第二個張,是明·南海人,字天佑。襲世職為廣州衛指揮使,正德中累立戰功,擢副總兵,鎮守廣西,嘉靖中以王守仁薦,鎮思田(大辭典張條下原注)。這兩個張都不是詩人。
《唐才子傳》是元代西域人辛文房所作,全書十卷,敘寫了三百九十八個詩人的傳略(其中附帶敘及的一百二十人)。辛文房本人也是詩人,有詩集名《披沙詩集》,已佚。現在僅能從元·蘇天爵編的《國朝文類》中讀到辛文房的七律《蘇小小歌》及七絕《清明日游太傅林亭》。
張祜與杜牧友善,元稹說“張祜雕蟲小巧,壯夫不為”,杜牧大為不平。杜牧高度評價張祜的詩:“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唐才子傳》亦載張祜謁李紳事,文如下:“祜稱釣鰲客,李怪之曰:‘釣鰲以何為竿?曰:‘以虹。‘以何為鉤?曰:‘新月。‘以何為餌?曰:‘以短李相也。紳壯之,厚贈而去。”這里,說以“新月”為鉤,是比《類說》的“以月為鉤”,更具體而明白。因為“新月”呈鉤形,比喻恰當。《彩毫記》作“明月”,是滿月,如何作鉤?
至于釣鰲,出《列子·湯問》,說,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略五山之名),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圣毒之,訴之于帝。帝乃命禺疆,使巨鰲(據列子,此所謂鰲,乃大龜,諸家注釋并同)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此處文義不甚明晰,意為三鰲戴一山),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數步,北宋本作數千,是錯的,詳見楊伯峻《列子集釋》九六頁),一釣而連六鰲,于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沉于大海。只剩下三個山了。《彩毫記》所謂以“三山為釣臺”是從這里來的。但是《彩毫記》作者卻沒想到在三山上釣鰲,就是釣三山的基礎,如果釣得,則釣者自己將落海中。《湯問》又有: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魚之大可滿一車)于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這是說,以極小之釣竿、鉤,極弱之綸,在極深極急迅的水中釣起了其大可以裝滿一個車子的大魚。或者,張祜的吊巨鰲,是從這里變化出來的,從極小變為極大,以虹為竿,以新月為鉤,以短李相為餌了。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四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