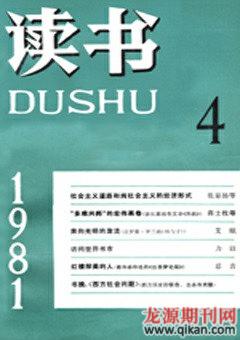在輕松的氣氛中受到教育
曹天鵬
我不是一個語言工作者,也不大喜歡讀語言學著作,而這次,卻被陳原的新著《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雜記》(三聯書店一九八○年版)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幾乎是一口氣把它讀完的,讀完之后還舍不得將它放下,于是又重讀了一遍。
這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才六萬來字,但在它那絮絮如話家常的文字中,卻包蘊著豐富的內容。細讀這本書,我不僅從中學到了許多語言的產生、發展、變化及其性質的一般知識,而且,還從作者對社會語言現象的剖析里,看到了在那些生產力發達的國度里,物質文明的帷幕后面,空虛的精神生活和腐敗的“精神文明”的綽約影子;也看到了在我國那“史無前例”的運動中,許許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可悲可嘆的現象,看到了“四人幫”所煽起的極左妖風如何狂暴地侵入到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包括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語言領域。我還從某些語言習慣的變化中,了解到不少風土人情,窺視到社會發展的足跡。總之,這本書所告訴我的遠不止如作者在“前記”中所說的“動蕩年代小小側面的反映”;這種反映的內涵是豐富的,而且又都是站在社會生活對語言的影響和語言對社會影響的反應這樣一個語言學的角度,稍加生發,略作點染而生動地表達出來的。讀了這本書,既開闊了我的知識眼界,又使我得到了某些思想認識上的啟發。
這本書一沒有經院氣,二沒有說教味,而是清新流暢,讀來別有一番韻味。作者在“精神空虛的語匯學”一節里有這樣的介紹:
“為了向傳統的一夫一妻制挑戰,在西方社會又出現了另一種‘活動,反映這種‘活動的語詞swap或Wife-swap(‘換妻)就出現了。前幾年出現的‘群居,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集體的‘換妻。但‘換妻據說也不時髦了。它讓位于‘同性戀——與此有關的語詞homosexual,homo sexuality等等就天天充塞西方報刊……美國某些大學生去年還示威反對當局禁止同性戀,并且肉麻當有趣地宣揚只有這樣地生活,才能嘗到‘美妙的人生味道云云。”(第14—15頁)
說得多么輕松自如,就象老朋友促膝笑談海外奇聞,全不象在講社會語言學知識。我讀到這里不覺隨之一笑,而“隨之一笑”之余,忽覺大有所得:語言這東西也象個社會的晴雨表呢;多糟糕的“精神文明”!
作者在“見面語的社會學”一節里寫道:
“社會習慣的改變——這常常是社會變革或某種非社會變革所帶來的結果,也會對人們的語言發生積極的影響。日常用的見面語,就是明顯的例證。……現在都用了‘你好!你好!這樣的見面語。當然,在一部分人中間,也還有這樣的習慣語:
‘吃過啦?
‘吃過了。……這樣的見面語當然是毫無意義的……問的人,答的人,在一般情況下,說了這樣的習慣語,他們心里根本沒想到大米、饅頭、面包或什么菜之類。這樣的對話倒是由來已久,也許它反映出一條真理:在人類生活中,吃飯永遠是一個非得解決而又不容易解決的‘永恒主題。……前幾年‘四人幫橫行時,人們不敢提‘生產,一提,便被誣為‘唯生產力論,這就違反了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真理——人非吃飯不可!不生產那里能解決吃飯問題呢?……這種形而上學反映到語言上,兩朋友一見面,互相問候既不能說‘吃了?‘吃啦!這種‘唯吃飯論即‘唯生產力論,也不能說‘你好!你好!這種不‘突出政治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語言,而只能象下面那樣的進行見面對話:
‘您革了命?
‘革了!您呢?
‘革過了!還要繼續革命!
‘繼續革命!……”(第28,30—31頁)
任誰看了這樣的文字,也是要捧腹大笑的喲,無奈這笑中竟含著一個國家在一段并不算短的時間里的辛酸淚!象這樣的文字,我們說它有將生活中熟視無睹的現象“撕破了給人看”的喜劇效果,是不算過分的。
作者在指斥形而上學瘋子們反對使用所謂“消極詞”的一段里舉了這么個例:
“……(詞典里)‘悲字項下一大串復合詞,例如悲哀,悲傷,悲痛,悲愴,悲愁,悲觀,悲憤……每一個語詞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含義,也都具備一定的語感,可是形而上學的瘋子們卻說是這么一大堆‘悲的東西,太消極了,不符合無產階級的需要,不符合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不符合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需要。因為無產階級是抱著樂觀主義的,抱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等等。真是扯不上一塊。但是生活卻不聽你那一套。甚至有一個時期連‘沙發也犯了罪。辦公室里的沙發被‘清洗到地下室去,讓它發霉,因為這是外國資產階級的屁股坐在那上頭而后來傳入中國的,由中國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的屁股坐過的那種家具,發霉活該!……不幸的是,這個語詞成為‘眾矢之的,‘消極的家具不僅要從生活上‘清除,還要從詞典中以及一切文字記載的東西中清除。回頭一望,可笑亦復可恨啊!”(第101—102頁)
生活中是沒有笑罵的,一罵,準動氣,往往失掉了幽默感,怎么笑得起來?——如果開玩笑,又當別論——可是在本書里卻不乏笑罵的佳例。這種寓莊于諧、化怒為謔,讓人在一種輕松的氣氛中受到教育的手法,誰不嘆服!我想,我們做宣傳工作或行政工作的同志,如果多一點這樣的本領,其工作效率也許要高好幾倍呢!
象上面那些信手拈來,涉筆成趣的文字,書中俯拾皆是。因此,讀它的時候,我很少感到專業上的隔閡而時添樂趣;它象一位技藝嫻熟的老人,在月光如瀉的夏夜,手抱琵琶面對我續續而彈,那悠揚曼妙的琴聲縈繞在紅花綠樹之間,懂行的會不自主地赴節投袂、應弦遣聲(陸機《文賦》:“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弦而遣聲。”),不懂行的也會覺得有一股股可人的涼風吹過心田,拂去那一天的勞倦……我這不是在作詩,而只是由衷地感到:這本裝幀別致美觀的小書,確實具有雅俗共賞的特點,賞心悅目的長處。它不失為我們大家特別是渴求知識的青年一代的良師和益友(這樣的良師益友,目前并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