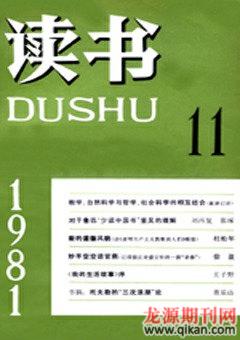生活.知識.想象
趙 昔
我觀《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的插圖藝術
我想,自有書以來,也許就有插圖了。我國古代,文字與繪畫同源,形義之間,本就難舍難分。對于書籍來說,插圖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它對于啟迪人們的智慧和想象,豐富讀者的知識素養,滿足人們對美的渴求,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對讀書產生濃厚的興趣,竟首先是由那些引人入勝的插圖引發的。幼年時的魯迅初次看到繪圖的《山海經》時那種驚喜的感受,就很能說明問題。
通常,為文學作品作插圖,使畫家們更感興趣。因為文學作品屬于形象思維,畫家們僅憑自己的生活感受,就能與文學家之間溝通形象的想象。而為哲學社會科學一類的書籍作插圖,卻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畫家們常常感到吃力不討好。盡管近年來這類書籍也間或帶有一些插圖,但看過之后,總使人有意猶未足之感,覺著還差點兒什么。
齊魯書社最近出版的《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一書卻別開生面,使插圖藝術和哲學緊密聯系起來。《評傳》一書,雖然記敘的是人物,但卻大都是有著睿智深邃思想的哲學家;他們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可又很難具體考證出他們的確切像貌。為這些古代哲學家作插圖或肖像,能否符合人們心目中的想象,想必這是曾使畫家們傷過腦筋的問題。當然,象或不象,似乎一作為問題提出來,就不免近于迂腐,但看過本書這些插圖后,卻往往覺得其中的人物恰恰與自己的想象相合。
所謂想象中的人物,也絕不是憑空臆造出來的。它是讀者根據哲學家們各自的思想、行狀在心目中形成的一個若明若暗的想象。說這些插圖恰似自己想象中的人物形象,就是指畫家們創造的這些人物是完成了的讀者心目中的那個模糊的形象,使原來那個若明若暗的形象具體化了。這無疑是畫家與哲學工作者通力合作魚水相得的共同成果。因此,我認為《評傳》的嘗試為插圖藝術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天地。它吸引著我們第一流的畫家們來參加這樣的協作。
插圖藝術有自己的功能,它不是文字的簡單附庸,也不僅僅是內容的重復和模寫,而是通過形象補充、強化、深化內容,或突出內容的某個方面,使讀者通過可視的藝術形象加深對內容的理解,獲得美的享受。成功的插圖,具有永久的魅力,往往使人過目之后終生難忘,甚或成為美術史上不朽的作品。因此,它除了具有一般造型藝術的功能外,還具有其獨特的功能。正因于此,它對藝術家提出的要求就更高,除了要藝術家具備造型能力外,還要求他具備廣博深厚的知識修養。為《評傳》作插圖的畫家們以其成功的作品證明了這一點。
讓我們來欣賞一下《評傳》中的插圖吧。通過畫家的藝術處理顯現在讀者面前的這些人物,是那么真實可信,栩栩如生,我們仿佛可以與之接談,與之交游。
先看看賀友直為孔丘作的肖像和插圖:
如何全面地正確地評價孔丘,自然不是畫家的事,但畫家在從事插圖之前,必須對這樣一位復雜的歷史人物有一個全面的歷史的了解。從《行教圖》和孔丘肖像,我們可以看到,畫家緊緊把握住孔丘的氣質特征,摒棄一切無關緊要的細節,著力刻劃其精神風貌的努力。在這兩幅插圖的創作中,畫家參考了歷代孔丘造像,馳騁想象,描摹出這位一生仕途偃蹇,卻又誨人不倦的教育家形象。插圖中的人物各具神態,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其中哪一個是貧不堪憂的顏回,哪一個是帶些武勇氣概的子路,……耳畔似聞杏壇的弦歌,兩千年前的往事,如狀目前。
插圖原本以文字內容為創作契機,然而好的插圖,卻不僅能道盡文中曲折,而且還能彌補文字表達之不足,甚或具有獨立的欣賞價值。正如好劇本還需要好演員一樣,杰出的表演藝術家,并不意味著只是背誦臺詞和完成規定的出場動作。從文字到舞臺,成功的表演是一次再創作。舞臺上固然不乏拙劣的表演損傷了腳本的例子,但也同樣有過杰出的表演藝術家使一個死劇復活的例證。這和插圖之于文字內容之間的關系是頗為相似的。
我們再來欣賞一下顧炳鑫為嵇康作的兩幅插圖。嵇康在歷史上記載并不多,畫家選擇了最能突出其性格操守的情節,匠心獨運,刻劃出這位性格純真,率性任意,“剛腸疾惡,遇事便發”,處污濁而不染,不肯與時俯仰的思想家的感人的形象。先看《鐘會來訪圖》:一方是心懷險惡,形容猥瑣,神色尷尬的鐘會;一方是操錘鍛鐵,襟懷坦蕩,旁若無人的嵇康。嵇康此刻的神態,正合魯迅說過的,“最高的輕蔑是無言,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真偽善惡,一目了然,給讀者以多少文字都難能名狀的形象感受。我們再來看《嵇康撫琴圖》:嵇康雖然隱居不仕,但在司馬氏的殘暴統治的淫威下,亦難免為人所誣陷,終至被殺。畫面上,臨刑的嵇康從容端坐,神態自若,索琴撫彈,以生命之音響,叩死亡之鬼門。畫面語言簡潔干凈,深深地傳達出畫家的痛惜之情。這樣的插圖,發人深省。它使人聯想到,在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酷迫害下,那許許多多的講求氣節操守的正直的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和結局。它對我們理解封建時代的“士”的悲劇,給以形象的啟示。
此外,如林鍇的王充像,張廣的呂不韋、范縝像;劉繼卣的郭象像,樓家本的墨翟像等等,都畫得很有個性,表現出畫家在刻劃歷史人物形象的深入探索精神和嚴肅的創作態度,從而為《評傳》一書增色不少。
為《評傳》中的人物插圖,畫家除了要表現出他們都是屹立在思想史上的杰出人物外,還要著力描繪出每個人物的個性。在這方面,讀者也得到了滿足。我們看到了威嚴中見親切的孔丘,飄逸而沉著的老聃,恢宏大度的墨翟,放達灑脫的莊周等這些個性鮮明、血肉豐滿的歷史人物。
但對為這些古代哲學家繪像,也有人持保留態度。其實,僅僅憑歷史上的文字作根據褒貶臧否,這是牽強的。古時那些著書立說,議論風生,或叱咤風云,左右歷史事件的著名人物,后世讀者想見其為人,往往肅然起敬,或以為其身量不知如何高大魁偉,其相貌不知何等超群出眾。倘使古人真能幻形顯現在我們面前,也許又不免使人感到失望,會說“不過如此”云云。司馬遷之于“貌如婦人好女”的張良,就是一例。對于古人,讀者通過閱讀,有自己的形象聯想,畫家在創作時,也一樣會在思想家的著作言論與史料的映照間,產生自己理想的形象,也一樣是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借助于想象產生的。
我認為,為《評傳》插圖的畫家們所以能成功地創作這些個性不同的歷史人物,除了要具備其他條件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因為他們具備一個藝術家最可寶貴的素質——善于想象。沒有想象,也就沒有藝術;沒有想象的繪畫,只能是僵死的圖解。這種圖解沒有色彩,沒有光澤,沒有生命,當然更談不上美感和藝術的魅力。當我們的民族正處在充滿美的饑渴,知識的饑渴的今天,愿一切藝術家自由馳騁你們的想象,為人類的文化藝術寶庫創造更多的精神財富吧!
(《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譯傳》,辛冠潔等主編,齊魯書社一九八○年九、十一月出版,第一卷〔精〕2.90元,第二卷〔精〕3.40元,第三卷即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