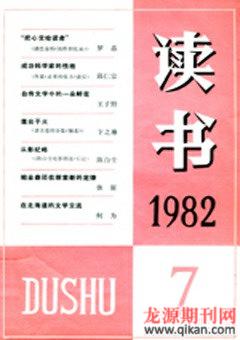《西廂記新注》
乾 浩
《西廂記》在元雜劇中堪稱“天下奪魁”(明初賈仲名《凌波仙》吊詞中語)。這個新注本的校注工作做得比較認真,特別是兼顧學術性和知識性,算得上是一本雅俗共賞的戲曲“入門書”,并沒有辱沒這一名劇。
《西廂記》的刊本不下百種,較流行的也達十余種,《新注》以現存刊印最早的《新刊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為底本,廣泛吸收了王伯良、凌
〔滾繡球〕:
恨相見得遲,怨歸去得疾。柳絲長玉驄難系,恨不得倩疏林掛住斜暉。馬兒
正襯一分,讀起來節奏更有跌宕,對崔鶯鶯此時此刻翻騰起伏的心緒會有更深一層的理解。讀者在方便之余定會對校注者深為感激的。
《新注》注釋得當,舉一反三,對一些單注詞語尚不能說透的唱詞,聯系曲情加以疏通,力求深入淺出。如惠明下書一段的〔耍孩兒〕曲文中有“不似恁惹草招花沒掂三”句,注釋中既寫出了“沒掂三”是糊涂、魯莽、不著緊要的意思,又以《董西廂》、高文秀《好酒上元遇上皇》的例子互相參證,最后并串講為“不象您只會談情說愛,做事糊糊涂涂沒個主張”。
《新注》還跳出單純分析“案頭之作”的窠臼,從舞臺演出的角度來進行必要的注釋,適當地傳播戲曲知識。它對元雜劇中經常碰到的“折”、“楔子”、“旦本”、“末本”、“白”、“科”等戲曲名詞有準確的介紹。即使是“鬼門道”這樣比較冷僻的術語,也找到了合適的譬喻:戲臺上左右兩邊演員的上、下場門,并以明代朱權的《太和正音譜》中的原文來說明當時為何這么稱呼。更有創造性的是,校注者在總結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提出一些人所未發的觀點。如蔦鶯送別張生一折,在最末尾的(下)字舞臺提示后面,校注者指出:張生與鶯鶯的分別實際應提前到〔一煞〕〔收尾〕兩支曲文之前,后面的曲子全是鶯鶯面對山遮林障、暮靄籠罩的情景,悵望親人,觸景生情的感覺。他們更大膽地認為,當時的演出張生并未下場,鶯鶯與張生同在舞臺的兩側,通過雙方傳神的表演活畫出兩地相望、二情依依的種種情狀。這是中國戲曲藝術采用時間、空間不固定的形式,在有限的舞臺上表現更為廣闊的生活內容的出色創造。閱讀這樣一些注釋,讀者思路為之打開,再通讀全劇,當別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西廂記新注》,張燕瑾、彌松頤校注,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第一版,0.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