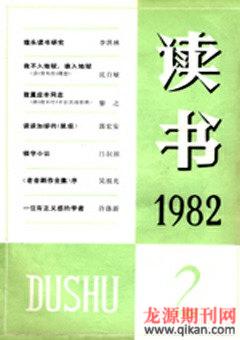胡如雷
《汪隋唐史論稿》的問世,確實是史壇上的一件值得慶幸的喜事,其所以特別值得慶幸,理由有二:其一,個人久聞汪同志治隋唐史有年,成果不少,然而已發表者屈指可數,難解急切求讀之情。這次《論稿》出版,雖猶不能滿足欲睹汪同志成果全貌的宿愿,但總可以看到其中的大部分了。其二,汪同志在“文化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熱心隋唐史的史學工作者廣搜汪同志的遺稿,編綴成集,不僅為饗讀者,亦為紀念死者的最有意義之舉。我是在興奮與沉痛相交織的心情下一口氣讀完這部著作的。
《論稿》是汪同志一生學術生涯的總結,是作者在治學中所走過的學術道路的見證,讀后不僅為其中的精辟論證所吸引,而且為汪同志逐步走向革命的進取精神所感動。對《論稿》不敢妄加評論,在這里只寫一點雜感性質的東西,略事介紹,亦借以表達個人對作者的緬懷之情。
解放前,汪同志在陳寅恪先生門下專攻隋唐史多年,無庸諱言,《論稿》中的很多文章是受陳先生的學術觀點、治學方法的影響而寫成的,師徒相承之跡,躍然紙上。譬如陳先生的重要論點之一,是西魏、北周、隋、唐諾朝的上層統治集團例行所謂“關隴本位政策”,很多復雜的政治斗爭均與此有關。《論稿》承其余緒,并加以發揮,在《唐太宗之拔擢山東微族與各集團人士之并進》、《唐太宗樹立新門閥的意圖》、《唐高宗王武二后廢立之爭》及《唐室之克定關中》諸文中都明顯而系統地貫穿著這一重要論點。再如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下篇《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中達到了樸素辯證法的高度,力求從事物的相互聯系、因果關系中探求歷史發展的規律,而汪同志在《李密之失敗與其內部組織之關系》、《西涼李軌之興亡》及《宇文化及之殺煬帝及其失敗》等文中亦一再談“連環性”、“連鎖性”問題,一望而知是在《述論稿》的啟發下使用了相同的研究方法。陳寅恪先生過人的優點之一,是觀察問題目光敏銳,往往能從常人所忽略的細微之處發現能說明重大現象的契機,這樣寫成的文章異常引人入勝,如《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一文(見《寒柳堂集》)就是如此。汪同志確實也具有同樣的優點,他在《西涼李軌之興亡》一文中,首先揭示李軌起事時涼州之漢胡共同舉兵以抗薛秦;接著指出最后執李軌之安氏兄弟系昭武九姓之裔,代表商胡利益;最終得出結論,李軌旨在割據河西,安修仁、安興貴則渴望唐朝統一以通商業孔道,故兩種勢力發生沖突,宜其西涼之亡。經過這樣的論證,確有發人所未發之處。對照《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與《西涼李軌之興亡》一讀,確實感到二文前后輝映,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后,陳寅恪先生治學謹嚴,每條史料都經過核校諸書方始引用,無一字一句茍且,此點素為后學所景仰。汪同志在這方面也繼承了陳先生的學風,所用史料無不細加考校,從無信手拈來、濫事引用之處。這種嚴肅的治學態度,對于今天的中青年史學工作者來說,無疑也是應當繼續承襲的。總之,名師出高徒,讀了《論稿》之后,確實感到汪同志不愧為陳門高足。
也應當看到,陳寅恪先生的某些欠缺或不足之處,在汪著《論稿》中也有所反映。陳先生看問題敏銳是其所長,但做得過了頭就易于走向牽強附會,如他硬把陶潛《桃花源記》所描寫的離奇故事說成是實有的塢堡組織,就難以令人信服。種族(即民族)和文化在魏晉至隋唐時期確實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但陳先生把二者說成是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決定歷史發展的關鍵,就未見允當。汪同志把隋唐之際宮闈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斗爭及其他一些重要歷史事變都同“關隴本位政策”聯系起來,就是受陳先生的影響而走向絕對化的反映。歷史上的一些政爭有不少是無謂的爾虞我詐之爭,有些事件甚至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用一個原則或原理解釋一切,就未免有走極端之嫌。再如戰馬在古代戰爭中無疑是影響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汪同志在《唐初之騎兵》一文中通過對各個戰例的分析,最后好象給讀者造成了這樣的印象:有馬則勝,無馬則敗;騎多則勝,騎少則敗。實際上,決定敵我雙方此勝彼敗的條件很多,這個問題很復雜,決不單純取決于騎兵的有無或多少,甚至也不僅取決于經濟力、軍力的對比,各方的政治形勢和情況也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如薛秦之亡,就與薛氏父子嗜殺成性、刻薄寡恩、統治殘暴有關,而恰恰這一點在《論稿》諸文中被忽略了。在師生關系上,學生能做到就其師之長,棄其師之短,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汪同志在陳先生的影響下產生某些類似的欠缺,亦非常近乎情理。指出上述缺陷,旨在有利于擺正今天的師承關系,原無意于苛求汪同志。
《論稿》是著者畢生治隋唐史的心血結晶,也清楚地反映了汪同志在學術上所走過的曲折道路。陳、汪二位先生都親歷了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與成長的歷程,但他們的學術道路卻判然有別,主要區別在于:陳先生在政治上熱愛祖國,堅持留在大陸而不去國棄土,但在治學上,解放后卻沒有發生什么明顯的變化,文風一仍故我;汪同志卻有所不同,他沒有在導師的老圈子里故步自封,而是力求突破原來的藩籬,自覺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而走向了一個新天地。這正是汪同志的難能可貴之處。
陳寅恪先生精于考證是素為大家所稱道的,但不足之處是不擇巨細,往往為考辨一些無足輕重的歷史瑣事而勞心費力。汪同志繼承了陳先生嚴考謹辨的學風,但在解放后所寫的一些考證文章中卻明顯地反映出,他在選題上是有過慎重考慮的,即首先研究那些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歷史資料,而不肯在無謂而繁瑣的問題上浪擲精力。如對隋代戶口數增長的考證、隋唐時期田畝數及實際墾田數的考證,就是與他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以后重視社會經濟的發展分不開的。《隋唐時期絲產地之分布》一文雖然寫竟于解放以前,恐怕也與他“在解放前曾參加過我黨領導的進步的革命運動”(《論稿后記》)有密切的關系。
至于《唐太宗“貞觀之治”與隋末農民戰爭的關系》、《關于隋末農民大起義的發源地問題》、《唐太宗》、《武則天》諸文,已經非常重視階級斗爭及其作用,一望而知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下寫成的。《論稿》的《附錄》中還特別選入了一篇以題為《關于農民的階級斗爭在封建社會中的歷史作用問題》的文章,更能集中地說明作者的興奮點已經從統治集團的內爭轉移到階級斗爭方面來了。甚至象“玄武門之變”這樣一些純屬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史實,《論稿》也能運用階級觀點指出:“地主階級的剝削本性和剝削階級的政治制度決定著他們要爭權奪利,從而也就決定著他們必然要爾虞我詐,以致互相殘殺。”(頁91)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汪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沒有流于庸俗的貼標簽方式,而是努力做到具體事物具體分析。譬如他在探討隋末農民起義與“貞觀之治”的關系時,一再強調這次起義不是爆發于一個衰朽的時代,恰恰是爆發于一個“號稱富強的時期”,隋朝“由全盛而驟告覆亡”,對唐太宗來說是教訓太深刻了。再如分析隋末農民起義的發源地時,也是具體研究了這些地區的具體情況,而不是泛泛地羅列一些剝削、壓迫的史料就算了事。正因為如此,所以《論稿》中的某幾篇文章不但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而且論史結合得比較好。
舊的歷史學家大致有兩種情況:一部分人專門埋頭于考證校刊,不肯從總體上考慮歷史發展的全貌和規律,可以說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另一部分人好作空泛的議論,卻又缺乏具體深入的探討,可以說是不見樹木,只見森林,而且他們所看到的森林也是被歪曲了的形象。在這方面,陳寅恪先生是超邁古人的,他不但細致入微地考辨史料和史實,而且由小見大,力求探討魏晉到隋唐的歷史發展的全局性問題,無怪乎解放前讀了陳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人,無不驚呼大開了眼界,有茅塞頓開之感。遺憾的是,陳先生雖然力求從總體上說明中國中古史的發展規律,但由于不是在正確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研究,所以看不到生產力的發展、階級斗爭的進行、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制約等等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也看不到勞動人民是歷史的主人翁,而片面地把“種族”與“文化”錯看成了最主要的因素。在這一點上,汪同志由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所以在解放后所寫的幾篇文章中,既進行過史實、史料的考訂,又力求從經濟發展、階級斗爭的高度分析隋唐之際的歷史,可以說是既繼承了陳先生的長處,又在陳先生的基礎上大大前進了一步。回顧解放以來我國發表過的隋唐史論文,其中少數也存在兩種偏向:重視運用馬列主義研究歷史的某些史學家往往忽視具體史料、史實的考證,文章顯得不夠扎實;熱衷于考證的某些史學家往往忽略從理論上加以概括,文章寫得功力雖深,卻缺乏高度。如果我們能夠象陳寅恪先生那樣,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而且在馬克思主義陽光的照耀下不歪曲森林的形象,而能恢復其本來的面目,則在隋唐史的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使這項工作攀登到一個新的高峰,是可計日而待的。
《論稿》的絕大部分篇幅集中在隋末和唐初的幾個問題上,開天之際稍有涉及,至于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國的歷史,就很少論列了,不能不說這是本書的美中不足之處。就這一歷史時期而言,從“安史之亂”到五代十國是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后期發展的重要轉折階段,在這二百年中社會經濟、財政制度、階級關系以及哲學、文學等方面都在發生劇烈的變化,農民起義“均貧富”的新口號也在這一時期初露端倪。解放以來,在隋唐史的研究中,不獨汪同志一人,大部分史學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隋朝和唐朝前期。如關于隋末農民起義、均田制、租庸調制、府兵制、唐太宗、武則天的文章比較多;而唐代后期,除關于兩稅法、黃巢起義和黨爭等少數問題發表過相當數量的文章外,對其他很多重大問題就很少有人問津了。可見這不僅是《論稿》的一個缺陷,也是整個隋唐五代史領域中的短線。有志于治隋唐五代史的史學工作者,我建議不妨在這方面大顯一下身手,在這二百年的史學陣地上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此外,《論稿》的大部分文章集中討論政治斗爭,包括階級斗爭和統治集團中的內爭,而對很多重要制度、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研究尚付闕如。在經濟史方面,除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考證戶數、田畝數及絲產地的分布外,也沒有對生產關系多所探討。這是本書的缺陷,也是目前隋唐史領域中的通病。回顧解放以來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少數幾個問題上,在面上沒有展開。諸如隋唐時期的官制、行政地理、漕運、鹽鐵業、手工業和商業等方面,我們的成果還顯得遠遠不足。至于對敦煌、吐魯番發現的各種資料的研究,則不免落在其他國家敦煌學研究的后面。因此,我們不僅從縱的方面看存在短線,從橫的方面看短線更多。針對上述情況,必須奮起努力,從縱橫兩方面都進行補課。
汪同志不肯故步自封而堅決走革命的學術道路,這種進取精神值得后人景仰和學習;《論稿》的優點和長處,很值得我們借鑒和參考,從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啟迪;汪著的一些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我們認真對待也能對自己有所裨益。相信《論稿》的面世必能使我國隋唐史的研究更前進一步。
(《汪隋唐史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