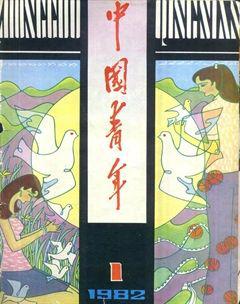相遇在異國的家人
梁良興
前年夏天,我和另外兩位同志到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進修,于去年初夏結業(yè)回國。
在我們到達伊州大學之前,我就知道該校有不少從臺灣和香港來的中國學生,而我們則是三十年來第一批來自大陸的中國學生。我和臺灣學生從來沒有接觸過,臺灣同學思想、學習和生活是怎樣的?在未來的一年里我們能否相處得很好呢?我的心里不是沒有疑問的。
他們有炎黃子孫的美德
伊州大學的臺灣學生有五十人左右,男女生約各占一半。年齡一般在二十五歲左右,多數主修經濟、工商管理、會計、電腦等專業(yè),大多是念碩士學位的研究生。除一位是由其受雇公司資助的外,其余都是自費留學生。
剛來時,我以為他們能自費留學,恐怕是高官顯貴或富商巨賈的子女。后來才了解,他們大多數出身于中產階級,如教授、醫(yī)生、公務人員、公司職員、中學教師等中等家庭。他們到美國,一般只要求帶足第一年的全部費用,以后的費用可由家里匯寄。不過伊州大學的許多臺灣同學,一年以后的費用主要靠自己勤工儉學。他們什么活都干,如在校園里的自助餐廳、系辦公室、實驗室等工作,到家庭當保姆,或在校外餐館當服務員,等等。一個會計系的女生對我說:“你別看我在這里什么都干,在家里我可是爸爸媽媽的掌上明珠呢!”
從這些臺灣同學身上,可以看到中國人吃苦耐勞的固有美德。他們遠涉重洋來到美國后,一般在學習上都非常刻苦。周末晚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許多學生都喜歡去參加舞會。但在圖書館里我常常看見不少臺灣同學埋頭案首。平時課余時間,他們也不貪玩,只在宿舍里聽聽他們最喜愛的“龍的傳人”和其他臺灣流行的校園歌曲以自娛,有些男生則打開錄音機,傾聽遠在天涯的女朋友的歌聲或說話聲以自慰。
“血濃于水”
英語里有句俗話:“血濃于水。”確實如此。不管是從大陸來的還是從臺灣來的,到了美國,我們都成了外國人。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風尚一—所有這些擰結在一起,形成一股無形的紐帶,使我們彼此容易接近。
我們到學校的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料理內務,忽然聽見輕輕的叩門聲。我開了房門,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高高個子的陌生的中國青年。他似乎因為自己的冒昧而臉上露出不好意思的神色。過了一會兒他才用普通話說到:“我是從臺灣來的,我聽說這個房里要住進一位大陸來的學生,你是從大陸來的嗎?”我把他讓進房里,他告訴我:他是學經濟的,只比我早到幾天,來到學校后就聽說有幾個學生要從北平來。說到這里,他象發(fā)現什么似的,微帶歉意地說:“對了,你們叫北京,我們叫北平,叫順嘴了。”他說,他是在臺灣生長的,祖籍蘇北;剛來到美國很不習慣,看到中國人就格外高興。臨走時,他還告訴我他的房號,并希望以后多接觸。
在此后幾天,當我在校園里走的時候,常常會有臺灣學生上前來問:“你是中國人嗎?”“你是從大陸來的中國人嗎?”“我看你不象是臺灣或香港來的中國人,果然是從大陸來的!”當我答稱是的時候,他們都會驚喜交集,繼而是問長問短。雖然是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但可以感到彼此都為能在異國遇到同胞而高興。
有一次,一個孟加拉國學生看見我和幾個臺灣學生在談笑,特意走過來半開玩笑地問道:“你們不會打起來嗎?”其中一個臺灣學生反問他:“干么要打起來?我們都是中國人嘛!”
“我們都是中國人!”這句話體現了多么深的民族感情。正是這種民族感情,使得許多臺灣同學關心祖國的富強。一個在伊州大學中國同學會當干事的臺灣同學告訴我:“在越戰(zhàn)中(按指一九七九年中越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你們狠揍了越南侵略者,消息傳來,我們高興極了。你們替我們中國人出了一口氣!”有一個愛打乒乓球的小伙子充滿民族自豪感地對我說:“你們大陸是國際乒壇的霸主。你們的乒乓球運動員這些年來拿了那么多世界冠軍,為中國人揚眉吐氣,他們真是好樣的!”
由于很多臺灣學生都是學工商管理或經濟的,所以他們對于目前中國大陸進行的經濟改革和四化建設都比較關心。有一個學企業(yè)管理的臺灣學生到我宿舍來串門時說:“每當美國老師談到世界上的窮國時,總是拿大陸和印度當典型例子,作為中國人,我每次聽了都感到臉上無光,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說,在歷史上我們中國人發(fā)明了造紙、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我們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在今天應該有新的建樹。有個臺灣學生對我說:“我是學經濟的。依我看,你們政府今天的經濟政策對頭,照這樣干下去,大陸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夠很快提高。”他表示,將來他拿到學位后希望能到大陸去工作或講學一段時間。
同游異國情倍深經過一段時間相處后,我們和臺灣同學常常互相串門;在學生自助餐廳吃飯時常常同桌而食;有什么事情彼此幫忙。有一個學鋼琴的女生因為用英語寫樂理論文有困難,常常找我們之中的一位女同志幫忙。我是進修英語的,常常利用課余時間去看電視連續(xù)劇,這個女生為了練習聽英語能力,也約我一起去看電視,以便聽不懂時好問我。
在美國,放假期間學生宿舍一律關閉,外國學生的住宿問題自行解決。去年快放寒假時,我們三人正為找不到住處而焦急,那位由公司資助來進修的臺灣同學知道后,便替我們張羅找好了住處。他說:“我們中國人有句老話:‘出門靠朋友,有我們住的,就有你們住的。”后來我們沒有到這位同學找到的住處去,因為美國朋友已安排我們去鄰近的衣阿華州農村過寒假。這位同學又主動開車,送我們到附近一個市鎮(zhèn)的長途汽車站。他在頭一天來回開車二百多英里,送一個同學到芝加哥搭機回臺灣,回來時已經很晚,而第二天又一大早就來送我們。臨分手時,他還熱情地說:“你們度假回來時,只要從長途汽車站打個電話到宿舍,我就開車去接你們。”對于他的樂于助人的精神,我是感激良深的。
逢到節(jié)假日,我們和臺灣同學還互相邀請吃飯。去年九月一日(美國人的勞動節(jié))的頭一天傍晚,有兩個我還不認識的臺灣女生來敲我的房門,告訴我自助餐廳不開晚飯,并約我們三人跟她們一起做晚飯吃。如果不是她們提醒,我們還真可能餓肚子呢。去年三月春假期間,我們三人和新從廣州暨南大學來進修的兩位教師,相約到住在校外的一位新來伊州大學學習的同志那里去聚餐,邀請了跟他住在同一座房子里的兩個臺灣學生。來自海峽兩邊的同胞象一家人一樣,大家動手,洗菜的洗菜,切菜的切菜,掌勺的掌勺,有說有笑,熱鬧非凡。飯后,又促膝長談,情同手足,十分相得。
我們和臺灣學生在一起的時候,更多的是互相詢問大陸和臺灣的情況,偶爾也談政治問題。這些臺灣同學,除由公司資助來進修的那位同學外,都是臺灣出生的。他們對于國共兩黨間的斗爭只是間接從書本上或從父母、祖父母那里知道一些,自己并無親身經歷。他們雖然也受臺灣官方宣傳的影響,如他們曾問我們:大陸上是否夫妻分居,外出旅行是否要通行證,是不是買什么東西都要票證等,但終究成見較少,很多方面我們是有共同語言的。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在臺灣歸屬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即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和大陸應該統一。
鄉(xiāng)土感情意更濃
這些在臺灣土生土長的同學,他們不一定有老一輩人那種強烈的回歸思想,但他們對于他們父母生長和自己民族的發(fā)祥地并不乏鄉(xiāng)土感情。平常聊天的時候,他們常說,我原籍山東、上海、大連、湖南,等等。對于大陸上千嬌百媚的河山,那就更為神往了。許多臺灣學生都說,他們從中小學時候起就從地理、歷史和國文課上知道黃河、長江、西湖、長城、紫禁城等。有一個學工業(yè)技術的臺灣學生說:“每當我吟誦蘇軾的‘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詩句時,我真希望將來有一天能親眼看看杭州西湖的豐采。”那個希望到大陸來的經濟系研究生也說:“將來如果我有機會去大陸,我一定要登上號稱世界七大奇觀的長城,‘不到長城非好漢嘛!”他們對大陸上的許多東西都感興趣,好多人都向我要過大陸上的郵票和硬幣。有些人表示,畢業(yè)后如果能在美國定居,便可拿著美國護照去大陸觀光。而對持臺灣護照去大陸再回臺灣就會產生麻煩一事,則感到很遺憾。
當我們結束在美國的學習,就要回國的時候,許多臺灣同學都來看望我們,有些人還專門為我們三人設宴餞行。那種依依惜別的情景是多么動人心弦啊!以至直到今天,在我的耳邊還仿佛經常響起我們臨別時彼此之間一再說的話:“在北京見!”“在臺灣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