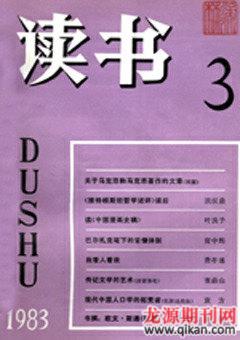現代中國人口學的拓荒者
袁 方
憶陳達先生
已故陳達教授的英文著作《現代中國人口》的中譯本,歷盡滄桑,終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興捧讀之余,使我更加懷念這位現代中國人口學的拓荒者、我的老師陳達先生。
一
陳達是著名的人口學家,也是舊中國組織人口普查實驗的先驅者之一。
要振興祖國就要了解國情。舊中國號稱有四萬萬人口,但四億人口的基本狀況究竟怎樣,誰也說不清楚,因為當時從未進行過全國性的人口普查。對于組織人口普查這種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腐敗不堪的國民黨政府是毫無興趣的。當日本侵略戰爭的炮火逼近西南,敵機日夜肆虐于昆明上空之際,其時任西南聯大社會學系主任的陳達,不顧環境險惡,條件困難,毅然組建了呈貢縣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并親自擔任所長,在李景漢、戴世光兩教授以及農志儼博士等人的協助下,開始了人口普查實驗工作。他們力圖通過解剖麻雀的辦法,來研究中國人口問題。
這次實驗工作,普查地區包括云南環湖地區一市(昆明)四縣(昆明縣、呈貢縣、昆陽縣、晉寧縣),普查人口合共五十七萬多人。普查應用了現代人口普查方法,進行直接調查,并在呈貢縣和昆陽縣主辦了人事登記。進行普查工作的人員,都經過了專門訓練。普查所得各種資料,經過核實整理,計有六十五種統計報表。最后寫成十四萬多字的《現代中國人口》一書。這本書,既是呈貢縣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經驗的科學總結,也可看作是舊中國現代人口普查工作的實驗總結。陳達教授認為,只有通過這種挨門逐戶進行直接調查的方法,才能使人口普查建立在真正可靠的科學基礎上,才能把人口資料的收集,由“傳統的間接方法轉移到采用現代普查方法”的軌道上來;從此無須再以間接方法來估計人口。
對這次人口普查實驗,國內外一些著名的人口學家和社會學家均極為重視,并給予了高度評價。當時的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奧格朋教授就認為,這種用現代普查方法所進行的人口普查實驗,“還是中國破題兒第一遭的嘗試。對于中國以外的讀者閱了這本書之后,不但對中國人口有了一個梗概,而且還給予研究人口問題的學者一些基本表格內有價值的參考資料。”可見,陳達教授在我國現代人口普查的科學實驗,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在國際上得到了承認;從《現代中國人口》這本專著的寫作到中譯本的出版,盡管其間已經過了三十多年,但無論是該書所探討的人口普查方法,還是在人口普查和人事登記的資料基礎上所進行的人口靜態與人口動態的研究,對于我們從事人口普查和人口學研究來說,仍可從中得到啟發和教益。
二
陳達教授又是一位熱心宣傳和致力于社會改革的社會學家。他進行人口普查實驗,搜集我國人口資料,目的就在于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服務。在《現代中國人口》的原序中他寫道:“希望本書不但在戰后為中國社會科學上,準備著有關事實研究的根基;而且希望這種工作,可以成為國家現代化的一部分基礎。”這段話寫于抗日戰爭尚未取得最后勝利的年代;然而,作為一名人口學者的陳達,卻已在勝利的曙光中,從科學研究的角度籌劃著如何在戰后振興祖國的宏圖大業了。
概述陳達一生關于人口問題研究的主要見解,一是要控制人口的數量,二是要提高人口的質量。他所以堅持中國人口必須控制數量的增長,是“因人口有大量的增加或增加率太速時,對于人民的謀生,當然要發生惡劣影響”,如不改變這一舊習,就無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此,他主張每對夫婦只生一對子女,實行“對等的更替”。他所以強調提高人口質量,是因為每個人的質量和品質不可能完全一樣。人口品質越高,其中聰明能干的人所占比重越大,越有益于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文化水平。為此,他主張加強遺傳學、優生學的研究,從先天遺傳方面采取更為根本的措施;要在推行生育節制過程中,適當實行區別生育率,例如勸說有遺傳疾病的成年男女自動絕育;他還主張大力興辦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等等。這些見解,構成了陳達從人口問題方面提出的救國論。
陳達的人口救國論,從科學角度看,當然有其價值;但是從政治角度看,如同當年流行的教育救國論和實業救國論等一樣,在舊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實上也確乎如此,陳達當時在人口問題研究方面提出的諸多科學建議,國民黨政府根本不予理睬,相反,他的親密同事聞一多教授卻在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斗爭中,慘死于國民黨特務的槍口之下。同事的鮮血和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教育了平日絕不過問政治的陳達。他不僅清醒地認識到人口救國論的局限,而且借諸報紙公開發泄了他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憤懣。
作為一個學者,陳達并沒有因為國事日非而中斷自己的科學研究。一九四四年,陳達應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的邀請,出席該校建校兩百周年紀念的學術討論會。為了準備論文,他用英文起草了這本《現代中國人口》。一九四六年,他赴美并在討論會上宣讀了這本著作。會后芝加哥大學邀請他講學半年,同時《美國社會學雜志》(一九六四年七月號)以該期全部篇幅全文發表了這本著作。這在美國學術期刊上也是極為罕見的事。此后本文又被印成專書,在歐美暢銷,受到了國際人口學界的重視。國外學者評價此書說:“在中國人口學上有一本好的著作,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這是“一本真正以科學態度討論中國的書”(見該書第4頁)。
當然,這本書作為一部三十多年前的舊著,沒有以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來觀察和研究人口現象,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局限性。例如他對歷史上人口循環曲線的分析就缺乏階級觀點(第5-9頁)。一九五三年,他在為本書寫的《再序》中說:“本書的立場與觀點在有些方面與今日的情形相比是有錯誤的或是不正確的。”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但是,我們也不應當認為這本書有某些缺點錯誤,就否認它的價值,因為這不是對前人的著作應持的態度。
三
陳達教授平生以治學嚴謹著稱。他極為重視調查研究,一貫主張靠資料立論,用數字說話。我于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聯大社會學系學習和工作,陳教授先是我的老師、后是我的領導。他平日就是以他的上述治學經驗教育我們,要求我們。他認為:即使道理再好,沒有材料說服力也不強。他說:“你有一分材料便說一分話;有兩分材料,便說兩分話;有十分材料,可以只說九分話,但不可以說十一分話。”因此他對材料的要求,一要大量搜集,二要力求翔實。他多次對我們說:“什么叫專家?你在一個問題上長期堅持調查研究,積累的資料多了,又經過篩選核實確實是可靠的,在此基礎上進行精心研究,就能提出科學的正確見解,這時你就是專家了。”陳老先生自己治學成家就是走的這樣一條路:他研究問題不求面廣,堅持抓住一點就鍥而不舍,狠狠地鉆下去,務求深透。他常說:“我自己除本行之外其它都是外行。”有一次,先生回顧他的治學道路時,曾經意味深長地對我說:“我覺得一個人不容易通。我的辦法是一條路,要走一條路才有成績和貢獻。”先生當年字斟句酌、反復品味“一條路”這三個字的神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斯人,斯語,斯情,斯景,我是終生難忘的。
我追隨老師多年,深深知道他老人家在這一條路上做學問,具有多么驚人的毅力,付出了多么巨大的超乎尋常的精力。他平日過的是三點式的機械一樣的生活,在家中吃飯和睡覺,在體育館鍛煉身體和洗澡,在圖書館讀書和研究。他不看戲,不看電影,極少會客,極少開會,一上班就全神貫注地工作,絕不允許別人任意干擾他的工作。
陳先生在社交方面是時間的吝嗇者,然而在調查研究上他卻從不吝惜時間。他時常親自帶領助手進行直接調查,調查內容十分細致,記錄更是一絲不茍。當別人的調查資料出現疑點時,他就抓住不放,非弄準確不可。為此他能雇上馬和調查人員一起下鄉核實,有時甚至不惜徒步往返幾十里山路。云南呈貢人口普查實驗,正是在他的這種嚴格要求下,才得到了準確可靠的數據和資料。也正是因為擁有這些大量翔實可靠的資料作基礎,才使他眾多的著作獲得了較高的科學價值,并贏得了國際學術界的重視。例如,一九二三年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被美國眾議院第六十八次會議選為檔案出版的《中國移民的勞動狀況》;一九二八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人口問題》,一九三八年由商務出版的《南洋華僑和閩粵社會》(此書有英、日兩文譯本)等等,直到今天,國內外學者凡討論到舊中國的人口、勞動和華僑問題時,都少不了要參考他的這些著作。國外學者稱贊他是“以研究人口著稱的科學家”,是“中國人口研究最著名的權威”。他是世界人口學會副會長,國際統計學會和國際社會學會會員,還是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分會負責人之一并兼該會研究部主任。聯合國成立后,他又被聘為遠東經濟委員會顧問。
四
陳達教授是一位愛國的學者。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前夕,他毅然拒絕前往臺灣,堅持留在祖國大陸迎接了解放。建國以后,他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繼續收集資料,從事人口和勞動問題的研究,先后完成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市鎮工人生活》和《解放區的工人生活》這兩部約一百五十萬字的著作。此外,他還積極從事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學術研究和論文的寫作。
陳達教授早就提倡計劃生育。解放以后,曾在五十年代和《新人口論》的作者馬寅初先生等相呼應,在政協會議上積極向黨和政府提出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議,受到了重視。一九五六年周恩來總理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的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他非常擁護這一主張。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在黨的雙百方針鼓舞下,我國人口問題研究開始蓬勃興起,陳達教授寫了《節育、晚婚和新中國人口問題》一文,在《新建設》發表。在這篇論文里,他說:“自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以后,新中國的人口每年均有增加。全國出生人數超過于死亡人數每年約在一千萬人以上。這種龐大的自然增加數額,從人口學的角度看,產生了一系列有重大影響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概括為兩類:(1)人民的就業;(2)出生率的降低。”當時他提出這兩類問題是富于卓見的,由于工作的失誤和左傾思潮的干擾,這些問題今天不是更為突出地擺在我們的面前嗎?陳達以大量事實論述了只有實行節育和晚婚,才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這篇文章發表后,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即使在今天看來,它依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可是不幸的是,一九五七年陳達教授卻因此蒙受了錯誤的批判。實踐證明,他提出節制生育的論點根本不是什么馬爾薩斯主義,而是實事求是的科學結論。
一九五七年,國際統計學會和人口學會聯合邀請陳達去瑞典參加年會。由于當時的形勢,他沒有去成,但仍用英文寫了《一九五三年新中國的人口普查——國家建設和人口研究的基礎》這篇論文寄給大會,后來發表在一九五七年的《國際統計學報》上(現已譯成中文,編入《人口問題研究搞些什么》一書)。在這篇論文中,他論述了一九五三年人口普查與國家建設和人口研究的關系,認為這次普查的意義很大:第一,這是我國第一次在全國范圍用科學方法進行的人口普查,搞清了全國人口總數。這在舊中國是不可能的。第二,在一九五三年前中國總人口沒有一個可靠的數字。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人口數字不準確,世界人口也就不可能有一個精確的數字。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普查為解決這一難題前進了一大步。第三,我國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需要可靠的人口統計數字作為依據。這次人口普查為國家經濟建設和人口研究提供了材料。他還針對當時一些外國人口學家懷疑這次普查結果的可靠性,高度評價這次人口普查,認為這次普查“由于運用了現代科學方法和人民熱情地支持這項工作。這兩者相結合,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普查的成功。”(《人口問題研究搞些什么》第33頁)
陳達教授已于一九七五年不幸逝世了。如果他能看到去年的全國人口普查,看到黨和政府將以人口普查資料作為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依據,他該是何等高興!作為他的學生和助手的我撫今追昔,不能不引起對他的深情憶念。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