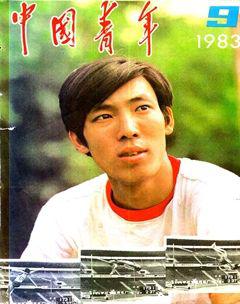任弼時與《中國青年》
丁洪章
今年十月二十日,被我國廣大青年尊為良師益友的《中國青年》已經創刊六十周年了。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里,人們情不自禁地懷念起曾經為《中國青年》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任弼時同志。
事情有巧合,弼時同志參加革命后的第一篇文章和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都是為《中國青年》而寫的。他一生為我國青年工作嘔盡心血,這是永遠值得后世青年銘記和敬仰的。
弼時同志是湖南省淚羅縣(原屬湘陰縣)人,1904年4月30日出生在一貧苦的鄉村教師家庭里。1916年,弼時同志考入湖南省第一師范附屬高等小學讀書。由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連年混戰,中國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弼時同志熱切地關心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如饑似渴地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在一篇《富國論》的作文里寫道:“嗚呼!吾國勢之孱弱至今而日極矣,外有強鄰之逼,內有劇寇之萌,愛國者曰:國危矣!國危矣!……”他到長沙不久,結識了當時在第一師范高年級讀書的毛澤東同志,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和教育。后來他入長郡中學讀書,經常閱讀馬列主義書刊,開始向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靠攏。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后,弼時積極投入這場斗爭,開展廢止二十一條、懲辦賣國賊、爭回青島、抵制日貨的愛國運動。1920年,經毛澤東同志介紹,他同肖勁光、任作民等同志準備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他們先到上海學習俄文,任弼時于這一年在上海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在黨組織安排下,他們歷盡艱難,終于到了莫斯科東方大學,開始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經驗。1922年弼時同志在這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任弼時結束了學習,回到了還在災難中的祖國。他到了上海,和惲代英、張太雷同志一起負責團中央的工作,同時在我黨創辦的干部學較—上海大學兼任俄文教授,并講授馬列主義理論知識。
一天,惲代英來到了任弼時的住處,一起討論團的工作。兩個人促膝交談,心心相印。代英是《中國青年》的第一任主編,他特意向弼時介紹了這個刊物的情況,臨走時又說:“你抽空給刊物寫點東西吧!”弼時高興地答應了:“好的,可不一定能寫好啊!”當天夜里,他在燈下鋪開稿紙,一直寫到深夜,為《中國青年》撰寫了第一篇文章《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刊登在1924年10月第49期上。
此后,他以辟世、弼時、PS等筆名,為《中國青年》寫下了許多文章。這些文章,大體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介紹馬列主義理論的,如《馬克思主義概略》《列寧主義的要義》等,比較全面地闡述了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他指出,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必須結合實際情形去解釋,特別強調馬列主義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和農民問題,批判了第二國際的改良派,批判了排斥農民的錯誤傾向。另一部分是關于青年工作的,如《蘇俄與青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意義》《怎樣青年群眾化》等。其基本思想是,強調青年團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團體,指出了它應當有堅實的基礎,能團結廣大革命青年一道前進。還有一部分是配合當時的政治斗爭寫的時事評論文章,如《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結果》《自五卅慘殺到北京慘殺》等,揭露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罪惡,對當時的斗爭起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弼時同志的文章,為青年團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提供了理論武器,有力地指導了當時的青年運動。由于他的文章熱情奔放,立論精辟,深入淺出,說服力強,深受廣大青年的歡迎。
弼時同志用他的文章和言行,吸引、教育了廣大青年。這同他的學習、思想、作風是分不開的。吳玉章同志曾說他品德好,作風好,才能全面,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又有策略的靈活性,既有高度的馬列主義修養,又有極為豐富的實際斗爭經驗。弼時同志高深的理論素養是在留學時打下的基礎。他在莫斯科學習非常刻苦,經常是出了教室就進圖書館。他的俄文學得很好,是同學中少有的能熟練閱讀馬列主義俄文版著作的人,所以他的理論學習成績也很好。當時在東方大學任助教的瞿秋白同志稱贊他是個誠實而用功的學生,是大家的榜樣。弼時同志謙虛樸實、平易近人,處處注意向群眾學習,向實際學習。唯其如此,所以他對生活有敏銳的洞察力,寫出的文章鞭辟入里,生動感人。實際生活是一本讀不完的教科書,弼時同志的文章首先得益于生活。有一次,他在工人夜校講“階級”問題,不少工人覺得概念深奧,聽不懂。當天夜里,他就隨工人到了工廠,進行調查,掌握了大量階級壓迫的生動材料。第二次上課,他就用大家熟悉的例子講解,使抽象的理論變成了有聲有色的故事,課堂活躍起來了。有的人聽著流了淚,有的當場用個人的經歷控訴剝削階級的罪惡。從此以后,他每寫文章,總要先向實際生活調查學習,寫出以后,讀給青年聽,征求他們的意見,有時讀給他的夫人陳琮英同志聽,請她幫助修改。雖然琮英同志是個童工出身的婦女,識字不多,但弼時同志非常尊重她的意見。
1925年,弼時同志代理團中央書記。1927年在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團中央書記。1928年,他轉到黨中央工作,此后,他雖然離開了團中央,但一直關心青年工作。1940年他參加了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后,又分管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的工作。1946年,根據當時的形勢,弼時同志又向黨中央建議重建青年團。后來,在他的親自指導和組織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于1949年誕生。
1948年,黨中央還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時,弼時同志就受中央的委托,著手指導中央青委創辦中央團校和《中國青年》的復刊工作。他和青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制訂了《中國青年》的出版方針。第一期的全部稿件,都經過了他仔細審閱。那時,他的健康狀況已經很差,一邊休息,一邊工作。但為了讓第一期《中國青年》盡快與全國青年見面,他經常深夜還在燈下一字一句地審改稿子,其中《活躍的延安馮莊青年》《慶祝中華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開幕》等稿,他詳細地修改了好幾遍。作為黨中央的負責同志,對我們一份青年刊物的具體編輯工作傾注如此多的精力,是我們后輩人銘感不忘的。
弼時同志為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在身體已近于不能工作的情況下,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審閱和修改了重要文件。1949年4月,他又抱病參加了大會,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就在這個報告中,他又一次講到《中國青年》,他說:“惲代英、蕭楚女等同志負責編輯的《中國青年》周刊,在中國學生知識界和各大城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在介紹共產主義思想、在與反動的國家主義派(即現在的青年黨)作斗爭中起過重大作用。……”但是,由于他重病在身,心力不支,這個報告只講了一半,就支撐不住了,是榮高棠同志代他讀完的。這件事傳達到團的基層組織,久久地留在團員們的記憶里,感動著他們。
這位終生關心青年成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1950年10月21日,又懷著滿腔的熱情,寫了《紀念<中國青年>二十七周年》一文,高度地贊揚了《中國青年》二十七年來發揮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辦好這個刊物的方針、任務。當時許多了解他的人,看到他的文章,都為他的健康好轉而高興。可誰曾料想,六天以后,10月27日,弼時同志因患腦溢血,猝然與世長辭,全國頓時沉浸在悲痛中。
弼時同志逝世后,人民悼念他,中國的青年悼念他。朱德同志題詞:“弼時同志不僅是中國人民偉大的戰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親密的導師。他一生為革命奮斗的歷史,永遠值得后輩青年同志學習。”在紀念《中國青年》誕生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們也應當紀念這位曾經為《中國青年》嘔心瀝血,披肝瀝膽,用先進思想哺育一代代青年的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