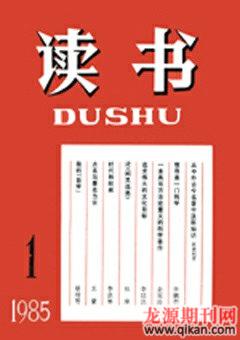時代和權威
李洪林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寫過一篇著名的論文——《論權威》。他用不可辯駁的邏輯證明了任何社會都需要權威。這并不是哪個人的主觀愿望,而是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如果沒有權威,最起碼的聯合行動都不可能,更不要說日益復雜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了。恩格斯寫道:
“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不管社會組織怎樣,在產品的生產和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下,都是我們所必需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553頁)
這一點對社會主義社會尤其重要,因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規模更加需要權威。這權威不是別的,只能是通曉社會發展規律、得到群眾擁護的共產黨。在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經過幾十年的斗爭,中國共產黨用自己的正確理論和路線以及優秀的作風贏得了人民的信任,形成了不可替代的權威。這是取得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也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法寶。
但是,這個權威后來卻受到嚴重的損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那種“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絕對權威”,排斥了黨的權威,使中國陷入空前的混亂。
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始的撥亂反正,同時也是恢復或重建黨的權威的過程。由于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這個過程非常迅速。權威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實踐中自然形成的。經過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全中國各族人民已經牢固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堅定不移地沿著四化的路線走下去。
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繼農村改革成功之后,一個全面的改革高潮已經興起,黨中央正在穩健地領導全國人民大步前進,這個事實說明什么呢?
它說明,現在的黨中央是成熟的。換句話說,黨中央的馬克思主義權威已經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當中確立了。這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最重要的保證,是中國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關心中國富強的人們的一大幸事。因為大家都親自體驗過,當中國共產黨的權威遭到破壞的時候,中國陷入多么痛苦的境地。
但是對于權威的認識,往往并不一致。有人反對一切權威,向往無政府狀態;有人很重視權威,卻把它簡單地等同于強制性的行政權力。事實上權威有多種,我們不能夠見權威就崇拜。權威也沒有永恒的,新舊交替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同樣在讀書,而且在讀同一本書,得到的東西卻不一樣。這個現象很有意思。恩格斯的《論權威》并沒有被人遺忘,不少人對它都很重視。但有人只從中看到個人權威,并且總是落實到自己身上,要別人都服從自己。這種理解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嗎?難道批判無政府主義,就是為了樹立個人的權威嗎?難道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不是民主的權威嗎?個人的權威當然是必要的,馬克思主義從來也不抹殺個人的作用。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更強調民主集中制,更強調集體領導的權威嗎?
這些問題我想過很久。一九八二年春節時在家里翻書,讀過恩格斯這篇《論權威》,順手寫了幾則札記。其中的一部分,題名為《民主的權威》,當時就發表了。這一部分,題名為《時代和權威》,還沒有來得及發表,一直放到現在,已經快三年了。寫這些札記的時候,新的權威正在建立當中。今天的情況和那時已經不同。當時所盼望的“使新的權威更快地確立”,如今已經成為事實。這是十分令人高興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日作者識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針對當時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寫過一篇著名的論文——《論權威》。
現在,我們正在經歷著建國以來最重要的歷史轉折。這個轉折的一項內容,就是新權威的確立。
使新權威更快地確立,是完成歷史轉折,使中國這艘大船沿著新的航線開足馬力前進的關鍵。
不過,到底什么是權威,我們今天需要的又是什么樣的權威,這些問題又很值得思索。
一
有人很喜歡權力,以為有了權力就有了權威。其實不一定,權力并不等于權威。
西漢初年,劉邦死后,呂后專權。呂家的人已經掌握了很大的權力。呂后一死,劉邦的老臣周勃陳平等人立刻發動政變。這時,權威的作用就表現出來了。當時統率“北軍”(首都警衛軍)的,是呂后的侄子呂祿。但是周勃闖入“北軍”軍營,大喊道:“為劉氏者左袒!”全軍士兵都把左臂袒露出來,服從周勃指揮。首都警衛軍站到周勃這一邊,局面就定下來了。這件事說明什么問題呢?它說明周勃有權威。呂祿雖然有軍權,但是缺乏應有的權威。當然,周勃到“北軍”軍營,是“持節”去的。“節”是權力的憑證。有了這根“節”,當然可以增強周勃的力量。不過,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還是周勃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如果換上另外一個無名氏,拿上一根“節”杖進入軍營,將士們能聽他的嗎?
一九七七年我去華北某大工廠調查。有一個“革委會副主任”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坐直升飛機上來的。她什么也不懂,廠里就讓她分管環境衛生。但她連這項工作也管不了,因為沒有人聽她的。她發動大掃除,誰也不動手,于是只好自己拿一把掃帚,一個人在院子里掃地。廠里的群眾先是討厭她,瞧不起她,后來又有點可憐她。她自己也很難堪,覺得是在活受罪。這件事也說明,權力也好,職位也好,不一定能帶來權威。
二
權威這種東西,是一種精神上的力量。不過它不是一般的精神力量,而是使人必須服從的一種精神力量。換句話說,權威以服從為前提。沒有人服從,權威就等于零。這樣,它就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第一,它應該擁有某種懲罰手段。或者,雖然不直接擁有此種手段,但是,如果不接受這個權威,必然要承擔不幸的后果。比如,在大海上航行,船長不必用武力強制乘客來服從,就有足夠的權威,因為失去船長的權威,輪船就有沉沒的危險。所謂“學術權威”,大體上也是這樣。沒有掌握政治上或行政上的權力,然而掌握了真理,就有權威,因為它符合客觀規律。誰要是違背了權威的意見,實際上就是違反了客觀規律,因而必然受到懲罰。共產黨的權威就是這樣。黨決不可以強制群眾服從自己,而只能靠真理、靠正確的路線來吸引群眾,得到群眾的擁護,因而建立起自己的權威。誰要是違背了正確路線,也必然受到懲罰,但不是由黨來懲罰,而是由客觀規律來懲罰(當然,黨組織對違反黨紀的黨員是能夠處分的,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第二,人們必須了解權威的意義,和拒絕服從權威的后果。也就是說,權威必須樹立在人們的心中,或使人尊敬,或使人恐懼。尊敬使人自愿服從權威,恐懼使人被迫服從權威。服從的人越多,權威就越大。不論自愿服從或被迫服從,一個先決條件是必須了解權威。如果人們都不了解某個權威,當然也就談不到服從。在這種情況下,那個“權威”也就沒有意義。比如,一個樂隊的指揮,在一群不懂音樂的人們面前,便沒有權威可言,因為這些人并不了解他的手勢和那根指揮棒的意義。“初生牛犢不怕虎”,是個形象的比喻,也包含著這個道理。虎為百獸之王,那權威是無可置疑的。老虎大吼一聲,百獸無不逃竄,因為大家都知道老虎的爪牙有多么厲害。但是初生的牛犢尚未了解此種厲害,就不懂得害怕,所以虎威對它毫無意義。當然,那代價也是可怕的,牛犢要為自己的無知付出生命。但是在此之前,虎威在牛犢心目中并未樹立,卻是事實。經過許多牛犢被吃之后,經驗終究會使活下來的牛懂得老虎的可怕,但那已經是后來的事情了。
三
自有人類社會,就有權威。這不是某個偉人的發明,而是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即使幾個人共同勞動,也得有人喊叫一聲,以便同時用力。這一聲喊叫,可以說是權威的萌芽。事實上在任何組織當中,只要牽涉到公共活動,不論是機關、工廠、商店、學校,不論是生產或生活,是工作還是學習,都需要某種權威使大家都來服從。否則,連起碼的秩序都沒有,更不要說大規模的協同動作了。
權威有個人的,有集體的。比如黨中央就是一個集體。個人的權威有時也不僅是個人的,而是集中體現了一個集體或階級的權威。馬克思主義反對個人崇拜,因為它神化了個人,不符合實際。我們就吃過個人崇拜的大虧。但是馬克思主義并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只不過對這種作用給以科學的解釋,并且把個人和群眾的關系擺得恰當而已。事實上,個人在歷史上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或推遲歷史的發展。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也都需要權威。一些杰出的權威人物,常常是一個方面、一個領域、一個時代的象征,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驕傲。
在戰爭中,權威的作用尤其明顯。一支軍隊不能沒有統帥,統帥也不能沒有權威。一個卓越的統帥本身,就是克敵致勝的重大因素,因為他的權威足以使敵軍聞風喪膽,而使自己的將士信心百倍。如果換上一個昏庸無能或是剛愎自用的統帥,同樣的軍隊就會是另外一種士氣,不但戰斗力要大大降低,甚至會全軍覆沒。戰國時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不是把四十萬大軍全部斷送在長平嗎?
四
每個領域都可以有自己的權威,比如學術權威,水稻權威,象棋權威。外國還有什么“汽車大王”之類的壟斷權威。這些權威在各自的領域里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在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還是政治權威。
原始社會就有領導公共事務的權威,然而不具有政治的性質。政治權威是從階級斗爭中產生的。
在階級社會,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現有的生產方式,必然運用國家機器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反抗。被統治階級的反抗,不管自覺或不自覺,總要指向現存的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是政治上的權力,為鞏固或反對一種政權而進行的斗爭,就是政治。所謂政治權威,就是統治階級借以團結本階級并威懾被統治階級以便鞏固現存社會秩序的那種力量。當一個統治者失掉權威的時候,便會有另一個人通過某種方式來代替他的位置。當整個統治集團的權威已經喪失了的時候,這個政權就要滅亡了。
任何政治權威,不管它看起來多么強大,不管它的代表人物多么顯赫,歸根到底,是經濟在起決定作用,它決定著一種政治權威的命運。能保護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政治權威,盡管代表少數人的意志,也能為多數人所接受。對生產力起阻礙或破壞作用的政治權威,最后必然被經濟的力量掃到歷史垃圾堆里去。當一種生產方式走到盡頭的時候,在舊經濟制度上產生的政治權威,不管統治者多么英明,必然沒落下去。有時候,一種生產方式并沒有走到盡頭,甚至還處在上升時期,但是統治者犯了嚴重的錯誤,也會使他喪失自己的權威。這時,縱然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也挽救不了這個權威的沒落,因為它和經濟的運動背道而馳。原來服從它的人民,已經不再服從了;對這個權威的尊敬或懼怕,已經被冷淡或憤怒所代替了。這時,能和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新的權威,必然要戰勝舊的權威,成為整個社會的支配力量。秦朝的滅亡和漢朝的興起就是這樣。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統一中國,正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上。他本來可以順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把國事辦的很好,但是他沒有弄好,使“天下苦秦暴政”,結果使自己的政權崩潰了。
五
社會上不可能出現權威的真空。不是這種權威在支配,就是另一種權威在支配。
歷史上有過這種情形:老的權威崩潰了,能夠代替它的新權威暫時還沒有形成,或者還沒有發展到足夠強大的程度。這時就是天下大亂,群雄并起。群雄,就是可能代替老權威的各種力量,所謂“群雄逐鹿”,就是新權威形成的過程。
當舊權威沒落的時候,社會便產生了對于新權威的需要。在這個時候,對于社會來說,最大的利益莫過于新權威快些建立。這個新舊交替的過程越快越好。相反,如果該滅亡的舊權威遲遲不退出歷史舞臺,新權威遲遲不能建立,將給社會帶來非常大的痛苦。天下大亂的時候“人心思治”,就反映了這種社會需要。
封建社會中間,為什么農民往往盼望“真龍天子”出世?能怪農民落后嗎?不能。社會生產要進行,總不能沒有秩序。當新的生產方式尚未產生的時候,客觀上只能照樣是封建主義的秩序。而所謂“真龍天子”也就是好皇帝,無非是在那種歷史條件下代表一種有利于發展生產的政治權威而已。改朝換代雖然并不改變封建制度,但在新的生產方式沒有成長以前,不同的封建統治者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確有不同的作用。當舊的權威已經沒落的時候,破舊立新的過程確實是愈快愈好,這對社會是有利的。
上面說的還是在同一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新舊政治權威的更替。至于舊的生產方式被新的生產方式所代替的時候,代表新生產方式的政治權威就更應該快一點代替舊的權威了。然而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這種新陳代謝的過程往往拖得很長,因為舊的權威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它要為自己的生存而掙扎。社會往往要為這個過程付出高昂的代價。
六
六
歷史上任何統治者都要竭力鞏固自己的權威,并且使它永遠保持下去。當然,一種權威的興起和衰落,并不以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拿中國的封建王朝來說,有的延續幾百年,有的只有幾十年。強大的秦朝,傳到第二代就滅亡了。按照秦始皇自己的設想,是要“二世”“三世”地傳下去,一直傳到千秋萬世的。
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后,也要鞏固自己的權威。這不是為了把政治統治永遠保持下去,而是為了消滅階級,從而消滅政治權威,使人類進入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也有權威,那將是和政治統治根本不同的另一種權威。
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之一,就是自己破壞自己的權威。我們黨經過長期的革命實踐,在中國人民中間擁有極高的權威。然而按照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必須發動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自下而上來破壞這個權威。代替這個權威的,是“左”的指導方針。在十年當中,這種“左”的東西具有極大的權威,簡直成了神物。然而正是這種“權威”,以破壞為目的,以致弄得天下大亂。現在我們好不容易才扭轉了混亂的局面,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了政治上的安定,這才能夠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從此得到一條非常重要的教訓:以后切不可再去破壞自己的權威了。
七
我們現在正處在新舊交替的時期。什么是“新”,什么是“舊”?“左”的東西是“舊”,三中全會路線是“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權威有興替,這是歷史的規律。
有人說現在存在著“信任危機”。這是只著眼于過去,而沒有看到現在和將來。這種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學,不是辯證法。對于導致我們民族經歷了十年災難的那種“左”的權威,人們不再信任了,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一個國家,支配全局的政治權威只能有一個。某種權威的衰落,意味著另一種權威在興起。人們對于“左”的權威不再相信了,就表示大家正在轉向新的權威。新的權威是什么?就是制定了三中全會路線的新的黨中央,就是堅決糾正過去錯誤的新的黨中央,就是認真平反冤假錯案的新的黨中央,就是決心領導人民把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的新的黨中央。
黨中央從三中全會以來,實際上是在實踐中重建黨的權威。不過也不單純是重建。更重要的是在前進中樹立新的權威。歷史在向前走,重要的不是回顧過去,而是面向將來。每個時代都需要自己的權威并且一定會產生出這種權威。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要現代化,人民要富裕,要過幸福的生活,不能再以階級斗爭為綱了。這是時代的要求。糾正了“左”傾錯誤、總結了歷史經驗的黨中央,制定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路線。這條路線不但在新的時期給群眾帶來現實的物質利益,而且使大家能看見光輝燦爛的前途。這就大大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威望。目前普遍有一種“怕變”的心情,它說明群眾對黨的路線的熱愛和擁護。群眾的擁護是發自內心的,這就是黨的權威之所在。群眾對三中全會的路線是這樣歡迎,對堅決貫徹這條路線的黨中央是這樣愛戴,哪里有什么“信任危機”?
當然,新權威的確立要有個過程,何況現在黨風不正的問題還嚴重影響黨的威信。不過飯要一口一口地吃,過去遺留的問題太多了,黨風只是其中的一個。新的黨中央連“文化大革命”那樣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都糾正了,難道對于不正之風還不敢下手嗎?看問題不單要看現狀,還要看趨勢。中國這艘大船過去走錯了路,幾乎沉沒,現在已經撥正船頭,駛上正確的航線。因為剛剛啟航,所以離目的地還遠,有人還心神不定,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只要舵掌的穩,大家齊心,就一定能夠達到目的地。
一九八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