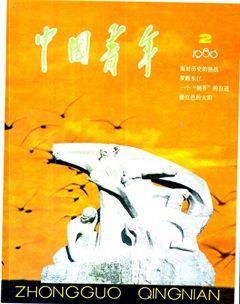成功者的啟示
石灣
文學創作是個迷人的事業,尤其對于青年。近幾年來,喜愛文學創作的青年人數之多,已經超過了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這既令人高興,又不免使人有幾分憂慮:這么多青年都擠到“文學小道”上來,能有多少可以到達那輝煌目標呢?王銀花的“我患了‘文學病嗎?”的疑問,正道出千百萬個“欲爭無望,欲罷不忍”的文學青年那種痛苦、矛盾的心情。
今年仲夏,一家寫作函授中心曾邀我去北戴河給參加筆會的學員講課。我知道,學員來自四面八方,水平參差不齊,差別是相當大的。講深了不是,講淺了也不是,很難“討好”。于是,我一再推辭。但是,主持筆會的同志懇切地對我說:“您不知道,他們的熱情可有多高!有兩個農民學員,是一對親兄弟,為了湊足來參加筆會的費用,賣掉了一頭牛呢!……”
我吃了一驚,琢磨了半天,我才下了“講課”的決心。講什么呢?就講怎樣才能成為一個作家。其實并沒有什么新鮮貨色,無非是舉了一些當代作家如何成長起來的例子。我的用意是很明確的,希望學員們能認真權衡一下自己的條件和境況,如果很難有成功的可能,就趕快剎車,千萬不要再為寫作耗費精力和錢財。因為,我很為那賣了一頭牛來赴筆會的兄弟倆擔心,萬一此行一無所獲,豈不要后悔一輩子嗎?
根據我個人的體驗和我所接觸到的情況,象王銀花那樣下點苦功夫,“記卡片,記人物思想筆記,注意觀察人物和了解人物……”對提高自己的文學素養和寫作能力是不無益處的。但是,這樣做未必就能成為一個作家。同時,文學創作也不象祖傳秘方和特種技藝,可以父子相傳,師徒授受。各種各樣的創作函授中心也未必就能培養出作家來。事情往往是這樣,一心想當作家的人成不了作家,而無意當作家的卻冷不丁地寫出了不起的作品。
我以為,有一個文學現象發人深省:“文革”之前,由大學中文系培養出來的作家(文學理論工作者除外)可謂鳳毛麟角;而在“文革”之后,大學中文系卻出了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梁曉聲和王兆軍,中央戲劇學院文學系畢業的喬雪竹、肖復興、陸星兒及新近以《桑樹坪紀事》而成名的朱小平,竟都是同屆同班!我們不否認這兩所大學對他們的培養,但他們之所以能成為作家,主要還在于他們都曾是在十年動亂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當今活躍在文壇的青年作家中,張承志、鄭義、史鐵生、甘鐵生、陶正和譚甫成,“文革”前夕原都是清華附中的同學。不用說,他們以前考入清華附中都是為了學理工。而一場動亂卻使他們全都改變了志向,搞起文學創作來了。可見,作家并不是誰培養出來的,更不是哪個名作家或名編輯培養出來的,而是接受了時代和整個社會的培養,受了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熏陶,經歷了各種生活和政治的磨煉而后才有可能成為有希望的作家。記得著名作家秦牧在“文革”前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現代中國作家中,幾乎找不出一個其子女也是作家的例子。“文革”之后,情況有了變化,父子、母女均是作家或詩人的例子已不再希罕但是,這決不是身為父親或母親的作家把什么寫作的訣竅授給了自己子女的結果。
就說在文壇上傳為佳話的母女作家茹志鵑和王安憶吧。曾有人問茹志鵑:“你是怎樣培養安憶的?”她是這樣回答的:“我有三個孩子,如果我能夠培養作家的話,我應當培養三個,而不是一個。事實上我的大女兒是個稱職的語文教師,兒子老三是售票員。可見我培養不了作家,作家也絕不是某一個人所能夠培養出來的。”實際情況也如是,直到王安憶成名之后,她的好些作品茹志鵑都沒有讀過。阿城的情況也極相似。不少人知道,阿城的父親鐘惦棐是大名鼎鼎的文藝理論家。前些天,我陪一位記者采訪阿城,當記者問道“你父親是怎樣輔導你”時,阿城頗為幽默地回答:“去年,我對父親說,《上海文學》上發表了我的一篇小說,叫《棋王》,有空你看一看。我父親很驚異,說:‘你會寫小說?”我舉這兩個例子,不是說茹志鵑對王安憶、鐘惦棐對阿城在文學修養方面一點家庭的熏陶和影響都沒有,只是說,文學創作這件事是不能靠他人傳授的,關鍵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又靠自己的什么呢?我覺得,問題的關鍵又不在于你如何刻苦地練習寫作,而首先在于你究竟為什么要寫和有多少非寫不可的東西。茹志鵑曾對文學愛好者說過:“千萬不要抱著當作家的目的去硬寫,一定要有話想說再寫,只有這時候再來進行創作實踐才是有益的。”王銀花的信,只談她怎樣半夜里在被窩里打著電筒寫,村里唱戲、演電影都不看,有了病也繼續躲在屋里寫等等,專一到了連婚姻大事都置之腦后的程度,至于她有什么不吐不快的題材、人物、故事和情感,卻只字未提。似乎一切都是為了寫,為了求得發表而已。
搞文學創作無疑是一種艱苦的勞動,要想獲得成功,自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王銀花已經寫了四年,許多稿子投寄出去之后杳無音信,好象編輯們都瞧不起她,令她感到“心寒”。其實,一篇稿子不被采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真正的好作品一般說來是不會被埋沒的。如邵振國的《麥客》,曾多次遭到“槍斃”的命運,后來,他抱著最后一試的心理,投寄給了《當代》,結果被采用了,并獲得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而那些“一投即中”“一炮打響”的作家也絕不是憑著僥幸成功的。著名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就是“一炮打響”的作家。在他21歲那年,科爾沁草原上發生了一起驚心動魄的案件,整個破獲過程是可歌可泣的。這件事強烈地打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寫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科爾沁草原的人們》。初稿信筆寫來,洋洋灑灑,竟有四萬五千多字,事件很不集中,主題也不夠突出。他改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寫不好,沒有辦法,他只好跟自己“作對”,將所有的原稿投進爐膛燒掉了。焚稿是痛苦的,但終于逼出了新路。寫就了的新稿投到《人民文學》,很快就發表了。
我舉這兩個例子無疑是要說明,向大刊物投寄的稿子,最好是凝聚著自己心血的發憤之作。而王銀花呢,四年來投寄出的許多稿件至今未響一炮。這時,我以為她應該審時度勢,考慮一下是否應該改弦更張了。
“偉大的成績和辛勤的勞動是成正比的,有一分勞動,就有一分收獲……”這話,一般來說是對的。但是文學創作畢竟是一種特殊的、復雜的勞動,假若你不具備合適的“土地”,那么,辛勤的勞動與偉大的成績就未必是成正比的。這里就用得著“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句老話了。因為文學作品是由思想、感情、生活、技法等組成,通過語言文字加以體現的。而這幾者之中,生活是最為重要的。我們常說,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但不是凡有豐富閱歷的人都能寫出好作品來。就拿近幾年出現的“知青”作家群來說吧,較之“文革”中數以百萬計的上山下鄉的知青來,其比例是微乎其微的。一位也曾在云南生產建設兵團勞動過的青年朋友對我說:“真是人和人不一樣。那時候,我和阿城在一塊地里干活,一張鋪上睡覺,他經歷過的事,我都經歷過。沒想到,他這兩年寫出了《棋王》、《樹王》、《孩子王》,而我卻一個字也寫不出。更奇怪的,那時候誰也沒見他寫過什么。他愛好美術,大家是知道的;可沒想到,他還會寫小說,成了作家!這小子怕是有什么特異功能。”
阿城真有什么特異功能嗎?沒有。他在一份“小傳”中寫道:“……中學未完,‘文化革命。于是去山西、內蒙插隊,后來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1979年退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與別人的孩子一樣可愛。這樣的經歷,不超過任何中國人的想象力。大家怎么活過,我就怎么活過。大家怎么活著,我也怎么活著。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寫些字,投到能鉛印出來的地方,換一些錢來貼補家用。但這與一個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樣,也是手藝人。因此,我與大家一樣,沒有什么不同。”我曾經問過他,為什么要這樣寫自己的小傳?他說:“我是要告訴一些青年朋友,創作并不神秘,我能寫出小說,他們也能寫出小說,而且會比我寫得好。”我說:“與你有相同經歷的知青畢竟只有你寫出了‘三王(即《棋王》《樹王》《孩子王》)。”他笑了笑說:“那當然,有相同的生活經歷,在內心未必有相同的感情經歷。”我感到,他這句話道出了創作的真諦:要成為一個作家,就必須善于體察和感受生活,在生活中發現文學的美感!我想,王銀花同志也是可以從中得到某些啟發的。
最后,還得申明一點:我決不是想給王銀花潑冷水,而只是想說,愛好文學,業余練習寫作,就象人們業余愛好養花、釣魚、打球、練拳一樣,對陶冶情操、豐富生活是大有好處的,我十分贊成;但是不顧自身物質環境條件,不去認真體驗感受生活與感情的內蘊,一頭鉆進所謂的文學創作里而難以自拔,并且把自己的成敗榮辱與親朋的理解、同情、支持聯系起來,一旦無所建樹,就怨天怨地,遷怒旁人,甚至失去生活、奮斗的信心,這都是不足取的。要知道,當作家,并不是誰立志要當就能當得成的,當你拿起筆的時候,要好好掂一掂它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