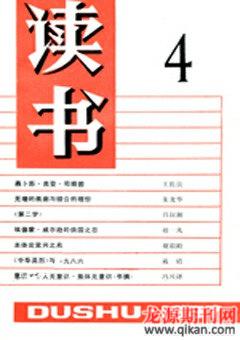《中華英烈》與一九八六
戴 晴
“這是一個不合邏輯的題目,”看到的人都會說,“一本刊物跟一個年號怎么‘與起來了?”
是這樣。但《中華英烈》與一九八六是不可分的。這倒不是因為這是她創刊的一年,而在于,不談一九八六而光說《中華英烈》就不帶勁。
很難說后世的中國史學家會怎么看待一九八六。一九八六這四個字,會不會如一八四○、一九一一、一九三七、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六那樣,深深融進中國的歷史與中國人的記憶。親身經歷過一九八六年的人,有誰會忘記它是怎樣地令人鼓舞、振奮、緊迫、張惶、惱怒、惴惴不安與茫然不知所措呢?
這當然都屬于同樣在一九八六年特別時興的“三論”所研究的課題之列。“三論”在忽地一下子開了門的中國學界已經時興到如此程度:如果有誰纂出一篇千字文而不來幾串信息基質、數論對策、內環境穩定場等等,就有被同人斥為老背晦的危險——雖然只有“三論”而沒有計算機為伴,就算作者與讀者同入五里云霧中,依然有點過洋癮之嫌。
然而在一九八六年出現了《中華英烈》——
當不僅責任田、時裝攤、副食鋪、旅館、化肥廠……連鋼鐵企業乃至鐵路都有可能承包的時候;
當愛慕孔方先生之風從沿海北漸,弄得將右手三個指頭撮在一起輕捻,同時神秘地眨著眼睛,已經成了時髦的中國人標準手勢的時候;
當居于領先地位的大、中、小型刊物的作者與編者已經不耐煩再說什么夫妻之愛、情侶之愛——這在八年前對中國人說來還是那樣新鮮,只要想想《愛情的位置》那種小說在當時引起的轟動——而孜孜于陽萎、盜嫂、畸型戀、不開化戀與早戀……
中國人在以就某種層次而言,連四十年代末都從未有過的速度改變著周圍,改變著自己。誰也幫不上誰,誰也不想幫誰或者讓別人幫。跟不上的人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哪怕在同一張桌子上吃飯、同一張床上睡覺,或者受制于同樣的染色體。
《中華英烈》出現在這時。
我知道,心理學家能舉出無數實例論及“極致”對正常欣賞趣味的損害,論及強制性勸導將誘發出的逆反心理。如果說,幾乎動員起全套最優秀演出與編導班底的《中國革命之歌》,要靠共青團請客學生才去看,而《白發魔女》卻在家家電影院賣到最高票額,是一九八六年中國的一大悲劇的話,那么制造悲劇的那只手,徹底倒掉了中國人的胃口的,恰恰是以那一整批油光水滑、容光煥發、從頭發到腳趾無一絲毛病、從生下來到死掉沒一毫差錯的樣板們為代表的高大形象。當相聲演員已經用戰士的犧牲來作笑料——混身打得跟蜂窩煤似的:“班長,這是我最后的黨費”,而觀眾也真的咧著嘴哈哈大笑起來,此時的中國人與半個世紀前沾著夏瑜的血治肺病的老栓小栓們已沒了多大區別,誰造成的?
《中華英烈》正出在這時。
曾與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與氫彈之父特勒親密共事的美國著名物理學家,也即我們通常所謂的標準資產階級學者戴森,懷著純真的欽敬與友愛,回想起他少年時候同為富裕家庭出生、才華出眾、通體詩人氣質,卻獻身于共產主義反法西斯事業的朋友:
弗蘭克是作為英國的聯絡官,與保加利亞抵抗運動取得聯系,一九四四年被空投到德國占領的南斯拉夫。
半年之后:
六月十日左右,在利特科沃的假審判之后,弗蘭克·湯普森少校就被處死了。他大約被關了十天。和他一起被處死的有另外四名官員:一名美國人、一名塞爾維亞人和兩名保加利亞人。還有八名別的犯人。
在村公所里,很匆忙地舉行了一次公開的“審判”。村公所里擠滿了旁觀者。目擊者看見弗蘭克背靠柱子坐著,在用煙斗抽煙,當問到他的時候,他操著一口地道的保加利亞語,根本不需要翻譯,這使每個人都感到驚奇。他被問道:“你是英國人,憑什么權力到我們國家來發動反對我們的戰爭?”弗蘭克少校答道,“我來到這里是因為這次戰爭的規模遠遠超出了一國反對另一國的斗爭。現在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你難道不知道持你這種觀點的人是要槍斃的?”“我已準備為自由而獻身,有保加利亞的愛國者和我一起獻身,我感到自豪。”……
就我而言,這是少數的、看過一遍就再也忘不掉的文字之一。捫心自問,之所以如此為它所激動,恐怕主要因為某些高尚純凈的情操,某些因為常被無恥之徒掛在嘴邊而失了光澤的圣潔的理想,某些為官場劣跡所浸染,弄到連自己都懷疑起來的原則,終因在一個不同膚色、不同“階級”、不同職業、不同經歷、不同的世界觀與不同的行為準則的人身上得到共鳴而格外明亮起來。我不信中國人會被深深的苦難與淺薄的福利所麻痹,會打算忘掉聞一多的無畏、忘掉李大釗的從容、忘掉陳毅的磊落、忘掉差不多一文不名的堯茂書只身跳進旋渦向長江挑戰的豪邁。
《中華英烈》于是在此時出現。
已故的周恩來總理說過:“如果我寫一本書,我就要寫我犯過的錯誤。”這句話不知說于何時,也不知有沒有特指,當然更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考據出在這之前或是之后,他是否受到過這個念頭的鼓舞與折磨。可以告慰的是,也許,他想做的事,在他溘然長逝之后,由他的繼任人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九七八年以來,全國的知識界與準知識界,無論是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還是九十歲,無論是受過打擊還是打擊過別人的人,都懷著難于言喻的酸甜苦辣,注視著一張張發黃的紙頭從卷宗里抽出,化作家人重聚的熱淚和對不復再來的歲月的嘆息。當二十八歲的司機在追悼會上吃驚地望著“胡風同志”的橫標,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這接受祭奠的主人就是“窺測方向、以求一逞”的陰謀家的時候,中國人其實都已經知道,繁榮強大的中國,離不開聰明熱忱的人民;而聰明熱忱的人民是一定要了解與他們息息相關的歷史的真實的——用數學的語言,后者是前者的完全必要條件,歷史與現實不容它有絲毫的因循。
于是,有了《中華英烈》。
《中華英烈》得以在一九八六年這樣的時代問世,是因為我與我的同志者始終信守著的是,熱血與正氣從來不曾也永遠不會在中國人身上泯滅。我們不打算只是嘖嘖贊嘆索爾茲伯里的《長征》。我們不信,中國的事,包括我們自己父兄的事,只能由或將繼續只由與中國文化如此隔膜、對中國風情如此陌生、甚至連中文都不懂的人來寫。我們不信感動讀者的只有被窩里的喁喁私話。健全與健康的人一定更為它所激勵——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進程。
這就是一九八六年出世的《中華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