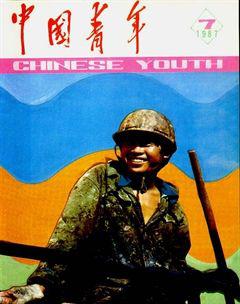流淚的7萬元
常揚
為了不使他陷入更深的困境,我只得隱去他的姓名和所在地。
他是一位農民企業家,自從承包了這個廠子后,便徹底擺脫了貧困。他手里有了錢,不是急著蓋自家的小樓,而是想到了村上破廟般的小學校。那一間間行將倒塌的教室撞得他心痛。他聽說教師們怕負不起責任,硬逼著村上寫出保證—“房屋倒塌,壓傷學生,全由村上承擔”。但這一張保證管什么用呢!自己過去窮得不能讀書,今日娃兒能上學了,還能讓他們在這種環境中學習嗎?他決定將企業盈利的7萬元捐贈出來。
當他捧著7萬元走進這所學校的時候,當他向縣教育局明確表示捐巨款重建校舍的時候,他的舉動迎來了紅花,迎來了電視臺的記者,迎來了省、市教育系統眾多領導的祝賀,7萬元笑了,象主人一樣憨厚地笑了。尤其聽說縣上答應另撥3萬元作為自己的同伙時,它笑得更加愜意……
很快,這笑容就收斂了。
表彰歸表彰,真到實際干的時候,縣上答應的3萬元卻不見了動靜。他多次去找,得到的回答卻是“經濟困難,無力支出”。他軟纏硬磨,弄得縣長都繞著道、低著頭、避著他走。
他找到省教育廳某領導,征求修建校舍的意見。該領導不耐煩地說:“我正忙著呢,你看著辦吧!”
他無可奈何地在校舍前徘徊,口袋里的支票不安分地跳動著。不能等了!過去總等,等來的是一下雨學校就停課的慘象,等來的是60%的文盲,等來的是無文化窮、窮了更無文化的惡性循環。實在的,不能等了!他要親眼看到7萬元變成新校舍,而不能光交錢了事。
事情就是這么怪,管教育的天天喊教育經費緊張,真的有人捐了款,卻又沒人張羅辦,好象全是這農民企業家一個人的事。他扔下正經營的工廠,風風火火跑到市建筑設計院,一腔熱血燃起設計師的責任感。設計師很快為他設計出一座既漂亮又實用的校舍。他又四處招標,引來一支技術強、要價低的建筑隊。短短時間,一座1200平方米的兩層小樓平地而起,40多間教室堅實明亮,還有圖書室、娛樂室、教研室……
這真是本地開天辟地的大事!
按常規,按常情,上面的人該來驗收和慶賀。村民們都盼著。然而,新校舍卻沉在一派蕭瑟的空氣里。不但省、市、縣教育局的領導不見人影,不曾舉行有意義的落成儀式,而且大門與圍墻也因資金不足,難以建起。小小樓房就象無爹無媽而坦露軀體的嬰兒,在野洼里無力地哭泣著。
他又找縣領導,希望能將原答應的3萬元用來修建大門和道路,結果只討來7千元儀器費。
他痛苦。不僅為這期間企業損失的10萬元,也為捐出的7萬元所遭受的冷遇。
豈止是冷遇,他和7萬元都開始流淚了。
捐款7萬元的消息傳出,全廠嘩然。不少人同室揮戈,以辭職怠工作為威脅。采購員纏著他要錢,工人起哄鬧獎金。一個與他共事多年的助手竟然私自將產品賣給他人,揣著巨款跑了,并四處揚言:“他倒是大方,今天助小學。明天還會幫中學,我們無盼頭了!”
他的舉動在那些與他一起致富的專業戶眼里無疑是鶴立雞群,于是專業戶們大表不滿:“他這一捐款,把我們往哪放,不是明擺著給我們難看嗎?”
“他的錢肯定來得不義,不然能這么大方?”
“他做這事,不會有好下場,小心半夜鬼來挖墻腳。”
這喊叫被春節的醉酒掀到了高潮。幾個用他的產品富裕起來,幾乎都是腰纏萬貫的專業戶,有意聚集在他附近的一家大擺宴席,劃拳酗酒。酒席上嚷聲甚高:“媽的,他不義,咱也不仁,我們合起來斷他的銷路,看他還顯能不顯能!”
而幫大伙致富,并捐出巨款的他,似乎成了敗兵,不但蒙受伙伴的污辱,還陷入了親戚的討伐之中。
親戚:“你有錢為什么不給我們?”
他:“不是都給過了?你們蓋房、娶親,哪家我沒給千兒八百的。”
親戚:“不行,我們還沒致富呢!”
他:“我富了嗎?你們也不看看我的家境。”
親戚對屋中的土炕舊席全然不顧,只盯住那捐出的7萬元,一個勁地起哄:“那為什么把7萬元扔出去?為什么?”
跟他們怎么能纏得清?他只得息事寧人地安撫各位:“算了,算了,我再給你們一人五百,行了吧?”他拿著存折寒心地走了。
在鎮上,他遇到一位認識的公安干警。那人對他說話的口氣象是訓一個犯人:“你閑得癢癢了?小心將來我辦你的案!”
他真不明白自己的義舉為什么會招來那么多人的忌恨。20年前,他窮得背著柴禾到鎮上去賣,好換口飯吃,被人抓住,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了;今日,他靠國家政策富了,把余款捐給集體,依然遭到妒忌、挖苦和誹謗,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為了擺脫困境,他選擇了這樣的辦法:
他整日小心翼翼,探聽各家“情報”。
哦,張家女人死了,他忙送去一副棺材。李家父親病了,他忙給200元。趙家蓋房了,他資助300元。甚至,他還“做賊”似的,從窗口給一些人家扔進錢……
哦,春耕了,他租來拖拉機,免費為全村耕地。夏收了,他獻出脫粒機,義務為大伙服務。
他以為,這就可以堵住那些非議,這就可以結束那些無休止的索要,就可以平安地進行他以為神圣的事業。然而,他錯了。
200多封要求資助、施舍的信接踵而來,弄得他應接不暇。他是縣人大代表,在人代會上,他所在小組的十幾個代表并非玩笑地要求他給每人一份禮物,攪得他哭笑不得。
他似乎成了一架性能良好,隨要隨動的造錢機器。
更嚴重的是,縣稅務局一位干部竟然歪曲事實,在一本稅務雜志上發表文章,誣陷他偷稅漏稅,7萬元捐款都是不義之財。
他一下被激怒了,善良的小羊也變成了憤怒的雄獅。他直闖縣稅務局。一位副局長輕描淡寫地勸慰他:“那是本小雜志,不必介意嘛。”
他又找縣長。縣長匆匆掠過文章,非常憤怒,即刻打電話要稅務局局長來。局長不敢來,只在電話里保證讓那位干部再寫篇更正文章。
此事終于引起了縣委的重視,他們認為現在到了公開的、大力支持這位農民企業家的時候了,便專門在縣廣播站為他播放了20分鐘的錄音講話。
“我捐獻7萬元圖什么呢?一不圖名,二不圖利,只圖學生們有個好校舍。因為,我受無文化的苦太深了。我辦廠賺了錢,不是我本事大,而是政策好。要是沒有這個政策,我還得過窮日子。那么,我感激這個政策的唯一表示就是讓我們下一代在經濟富裕的同時,精神上也富裕起來,使這個政策更鞏固、更發展……”
話雖痛快地講出去了,但他內心的后怕并未消除。分手時,他拉住筆者的手痛苦地說:“看來,我得把廠子交了,把剩余的錢都用到家庭建設上。因為,我畢竟生活在現實中。我想安寧,我得為老婆孩子著想,過幾天小康的日子。我不能再讓用勞動掙來的錢與我一起流淚了……”
我覺得他的手在顫抖,使我感到了心靈上的強刺激。他,是萬千富裕起來的農民中的一員,又是一位有追求的、具有一定新人素質的農民。盡管他對追求的目標還不能從理性上深刻認識,但他已從一個質樸農民的良知和本能上感覺到了。
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新人,然而他所立足的富裕起來的土地仍沒有擺脫傳統的意識。如果他把7萬元全部用在個人生活上,如果他一毛不拔,人們不但不會有議論,而且還會投去羨慕的眼光。眼紅當然會眼紅,但對“個人財產”,也只是眼紅而已。軒然大波的掀起,主要在于這7萬元的歸屬性質發生了變化。長期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已使人們養成了難以改變的痼疾,即對“公”的理所當然的貪欲。既然能把個人財產捐出一部分為公眾事業,那也該捐出另一部分讓人人有分。無形中這位農民企業家已經成了“公”的化身,誰都伸手,毫不臉紅。這中間“吃大戶”“均貧富”的小農思想也在推波助瀾。那位公安干警、那位稅務局干部的無名火從何而來?7萬元的捐款與他們有何相干?不言自明,也是這種意識在作怪。
對公共事業的漠視、對文化教育的無動于衷也是7萬元遭冷遇的原因之一。只有缺少文化的地方才會對辦教育不感興趣,才會如此輕視個人捐助教育的意義,這也是沒有文化的悲劇。
然而新人畢竟產生了。從各方面為這種新人的生存和發展創造條件已成當務之急。否則,類似他這樣的新人還要退縮,還要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