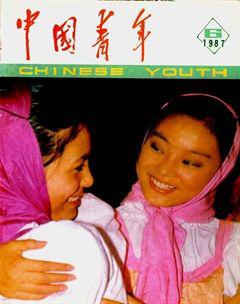戰爭啟示錄
梁中
3年前,一個20歲剛出頭的共和國小軍官,行囊中帶著幾本舊書,中間夾著一張英文本科畢業證書和一張學士學位證書,心酸酸仿佛充軍一樣 ,來到了云南邊境前線。那便是我。
3年的時間,我不能說自己已經成熟。但在不知不覺中,我便在生與死、得與失、忠與孝以及個人與社會這些價值觀念所構成的坐標系上繪下了一條條雜亂而曲折的線。
我在這場戰爭中艱難地走了3年。最后,在戰爭與和平的交界處撿到一部啟示錄,并發現上頭簽著自己的名字。于是決心帶回給人看。那便是我的《戰爭啟示錄》。
一此致軍禮——寫給朋友
前線的苦與樂,自然不同于后方。比如說我們的樂,其中之一便是讀后方來信。什么樣的信都有。比如,有的人寫信告訴你,他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仿佛只是為了跟你打聲招呼;有的人在寫滿動人文字的信紙上,再畫上一個占滿全頁的心字形圖案;有的人(女孩)卻在信封里裝一張精美潔凈的黃色紙張……就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在信中向你談及各種事情,向你傾述一切心中的奧秘和情感。面對這些袒露著的心懷,我的心不由得戰栗著:他們在把你當上帝呢!希冀著能在你這里表達一切和實現一切。
我不明白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給前線寫信,卻又象著了魔一樣地愛讀這些后方來信。
久而久之,我終于明白:僅僅因為我們是軍人,身在疆場浴血奮戰的軍人。在后方的許多人眼里,軍人是英雄,是榜樣,從他們身上可以找到理解和信賴、風情和安慰。在他們心里,也許把前線和前線軍人都神圣化了。特別是他們在和平環境中對現實失望或者對自己的過去懷有深刻內疚的時候表現得尤為明顯。他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前線仿佛是理想國,有著理想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士兵不僅僅是英雄,而且是力量、道德、正義及理性的化身。因此,后方的青年朋友便把軍人作為幻想中的任意對象與之交談。
我最終不可能讀懂每一封信。但在許許多多的來信中,有一類總使我讀后肅然起敬。他們是這樣一些人:天生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對前線將士似乎總有一種內疚和不安。他們對自己經歷的痛苦并不在乎,反過來在信中卻對我們大加鼓勵和安慰,把我們當作悲劇中的人物加以同情。他們之所以這樣,不過是想到自己置身于別人保護的和平之中。而實際上,比起我們來,他們多的不過是一點點生命的保障而已。多么偉大的同情。
我們不是萬能的上帝,我們不可能給所有的后方人回信,更不可能解答一切問題,滿足一切要求。然而,我又是多么希望能給所有的后方人回信。即便要回,也不能千言萬語。我只是想讓所有的朋友明白,我們都是普普通通、實實在在的軍人。在奔赴疆場之前,在穿上軍裝之前,我們與你們都一樣。
不論你是誰,不論你寫來怎樣的信,你都將受到軍人的感謝。你們的信,使我們感到了責任;你們的信,讓我們得到了理解。我們彼此走近,彼此溫暖,彼此凈化和升華著各自的靈魂。
二你的困惑——寫給妹妹
你的信不算長,說了一些話,卻又沒有展開講,有些話根本就是欲言又止。這真讓我有點兒難受——這不是你。顯然,你在思索許多問題,可你又不愿和我探討。為什么,我們仿佛突然變得陌生了?
把你的信反復看了幾遍,發現半截話一句接一句的信中,你提到了這場戰爭,提到了剛發生的學潮……由此,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你寫信給我時的復雜心情,理解了你異乎尋常的緘默,也看到了你困惑心靈的一角。
從我們的隔閡談起吧!我們曾經相同——都是大學生;而今卻又有不同——我已成為一個身在前線的軍人。這個差異竟因為游行這一特殊因素,使我們之間形成了指責與被指責,說服與被說服的關系。
此刻,我決不想象老頭子訓人那樣,擺出資格,以絕對權威的口氣,以必須服從的架勢同你講話。我只想和你交心,就你這封沒有提出任何論題卻使我再不能沉默的信,說說你的困惑。
在收到你的來信的同時,我也收到不少其他朋友的信。他們都挺坦率,有的直截了當地提出某些問題讓我回答。你和他們,實際上把問題都集中到了一點:民主選舉。這也是這次游行的導火索之一。本來,作為學生,選舉是你們參與政治的正式機會。但這次大家普遍感到被愚弄了。因為候選人的情況你們一概不知,還硬讓去投票。為此你們惱火,牢騷頗多。盡管游行早已平息了,而你們至今卻仍在困惑之中。
我不想說教,只想提醒你考慮兩點:
第一,永遠不要為在中國不能實現美國式的選舉而煩惱,而失望。中國能否實行美國式選舉,這不是民主化進程的快慢問題,而是中國最終是否愿意并且能夠采取美國式選舉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能在中國掌握政權是由于歷史的必然,這是你絕對不會否認的。既然如此,那么你就必須承認一點,即那種歷史的必然在中國造成的現實也必然規定、約束著中國今后的一切,即社會主義體制。因而可以這樣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不僅是歷史的結果,而且還是符合客觀規律的,且是長期的。所以,如果有人希冀選舉美國化,這純屬幻想,只能是自尋煩惱。毋庸諱言,現在的民主選舉存在問題,但有一點你該相信,隨著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的推進,你就會用不著因與候選人陌生而惱火了。這是中國解放后憲法修改走過的路所顯示的邏輯趨勢。
第二,群眾運動的局限性。80年代的學生與10年動亂中的學生已有著巨大的差別。我們再也不會象他們當年那樣幼稚,再也不會那樣狂熱地去充當一場慘劇中的角色。“為了偉大之最偉大而永遠橫臥,由于目光的清淺而永久閉上眼睛。”(韓作榮《紅衛兵墓》)但是,十年浩劫的悲劇難道不永遠值得我們用來警惕自己?很好地了解我們這塊古老土地的歷史吧,歷史是公正的。
有人譴責你們的行動是隨意丟棄和平的果實,你們自己也在自責。其實我倒認為,人們不應該讓當兵的去說:“我們在前線流血,你們卻在后方胡鬧。”真正胡鬧的有幾個?我們之間不應當是指責與被指責的關系。你們積極參與改革,這證明你們具有社會責任感,也證明我們的目的是一致的。為了和平、安寧與幸福。
3年前,你在入學后的第一封信中對我大談弗洛伊德,我為你接受西方文化之快而驚嘆,同時又為你僅僅是接受而擔憂。今天,你的困惑雖使我不安,卻也使我欣慰。因為你的困惑中包含了對現實很強的責任感,對事物的認識和感覺也具有了相當明顯的現實主義態度。這證明你在走向成熟。我相信你。
三幸存者之夢——寫給生者
1986年5月4日前夕的一個傍晚,我永生難忘。我和我的戰友們喝完酒,七八個人硬擠進一輛吉普車,瘋狂地駛向前線墓地。
可能是由于順路,也可能是為了讓自己的心不至于麻木,我在戰區時帶來此逗留。每到這里,我便有一種置身另一個世界的感覺;每當此刻,我的心總會奇怪地體驗到一種十分強烈的歸宿感。這使我不由得常去想,死亡究竟是什么東西?如果我自己躺在這里,那將是怎么一回事?因而我試著以一個死者的身分來回味生活,感覺現實,思索生命的意義。
今天,我又來到這里,在一塊空地的破木板上,掛起一條長長的白絹,上面抄著我的一首40余行的詩——《輕點兒,人們》。它就是在這墓地寫就的。我們掛完它,站在旁邊,看著它被強勁的晚風吹得劈啪直響。我們幾個人竟也抑制不住感情,和著那白絹的響聲,破著嗓子胡亂喊了幾聲。當時喊的什么,現在已全然不記得了。大概是當時戰區流行的一些口號吧。一個叫張榮生的戰友(名字吉利得叫人羨慕),也是我大學的同班,異常激動地信筆在白絹的空白處寫下了“要和平”“祖國萬歲”幾個潦草的字,并把我的另一首短詩《尚待鐫刻的墓志銘》抄了上去。
那天,我們全醉了。由于酒精,也由于血。
此后,戰區便開始流行一首詩,就是那首《輕點兒,人們》。再以后,一位后方的詩刊編緝找我要去發表。我說我不想當詩人。這是假話。我對當詩人并不反對。我之所以不愿發表這首詩,是因為我擔心把它們拿到后方去,那些沒有經過戰爭、沒有去過前線烈士墓地的人們是否真正欣賞和理解。我寧愿讓它非正式流傳。直到今天,我仍以為,它產生于那片神圣的墓地,那里是它最理想的版面。是那些死去的戰友給了它以生命,這詩屬于他們。
就這樣過了將近一年。此幅詩絹曾幾次被人揭走,而每揭一次,我都固執地搞來白絹,重新抄好掛上。當它最后一次被人揭走時,我遺憾極了。一位戰友告訴我,揭走之前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來自四面八方人們的留言。我后悔揭的人不是我自己。但我從心底里原諒揭走白絹的人。他們肯定不是百姓而是軍人。因為我很清楚,一個戰場上的軍人的超常心理——藐視一切,將一切置之度外,甚至包括正常的道德和行為準則。他們從前線歸來,來這墓地匆匆一瞥之后,說不定他們又得趕緊奔往哪個地方去,那兒離這個埋著昨天死亡的地方很遠,卻距明天的死亡很近。“此刻聽聽他們的心聲吧,生者和死者都有什么要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去首都一游,把笑臉定格在天安門城樓。我最高的索取就是詩一首。”(紀宇《風流歌》)是的,如果你注定要為和平而死,你就會象他們一樣,希望自己的死不僅僅變成“尸”;你就會象他們一樣,希望自己的死象詩一樣壯麗輝煌,永遠被人歌,永遠被人頌。
我終于明白:活著的,死去的,都需要那首詩——死去的,默默接受,活著的,悄悄帶走。
然而,我再也沒有勇氣去掛了。
于是,我便做了一個夢:在那偏僻荒涼的山巒上的地上天國里,忽然間立起一塊石碑,上面刻著一段銘文,一首詩,致安息著的人——以生者的名義。
我把我的夢寫給所有的生者。
也許,你曾給前線將士寫過一封封熱情的信,寄過一件件慰問品;也許,你聽前線英雄事跡報告后的眼淚還未擦干;也許,《血染的風采》你聽了無數遍;也許,你曾和我一樣,在這里戰斗過,而今雖然回到了和平的懷抱,但這里的一切總在你的眼前,那些和你一道來卻再也沒有回去的伙伴也總在你的夢中出現……
偉人說:“死的不幸只是對于生者。”不幸的死者永遠地不幸了,而有幸的生者此刻怎樣了?生者又能為死者做點什么?
也許,這正是你心里惦記著的。果真如此,一個幸存者的夢便實現了;果真如此,那些死去的人們的夙愿——“最高的索取”便也實現了。
謝謝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