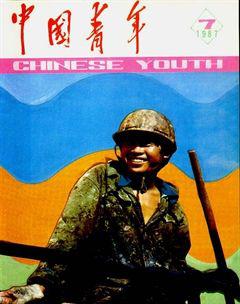暮雪(小說)
我最大的缺點是愛睡懶覺。冬天的早晨,陽光射在窗簾上,映出一幅墨竹圖。我大可安枕細觀,其樂融融。這時父親便把房門踢得打雷般響。然而夏天就無此雅興,睜眼就是光輝燦爛。春光迷人卻又短促。那么秋天呢,秋天是忙碌的,是做買賣的黃金季節,尤其是秋冬節氣相交的當口。父親頓頓要呷上二兩,喝了酒便罵我沒出息,懶蟲,廢物。可是對不起,那您是什么?我是說您為什么選擇這個晦氣的行當?我敢斷言,您的買賣永遠不會讓您實現發財的夢想,因為您不過是對面那家小醫院的附庸,守在太平間門口的一家花圈店的主人,一家個體戶。您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不過是給死人壯壯行色,如此而已。當今世界,只聽說鋼鐵大王,石油大王之類,還沒有花圈大王誕生。更可惱的是我必須繼承您的事業,終生不貳地為死者服務,因而失去了其他就業的機會和同齡人的許多樂趣,您還有什么資格罵兒子沒出息呢?
我堅守著那扇鑄滿悲哀的小門。我家小店真可憐,一間門臉,甚至連柜臺也不需要。面帶哀慟的顧客進門瞧一眼環墻而立的花圈,隨手一指,拍板成交。沒有討價還價,挑肥揀瘦,也不實行三包,物價局、稅務局的大員也極少蒞臨。父親的手藝在全城也屬一流,為保證質量和信譽,他很少讓我插手干活。
深秋的一個晌午,我正蜷在藤椅上,架著二郎腿,專心致志地鉆研一本武俠小說,忽聽店門吱呀一響,顧客光臨。我趕忙扔下書,起身接待。
如果換個場合,我這時肯定會笑出聲來。蹣跚而來的顧客活脫脫是蒲松齡筆下的兩個老怪。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對比鮮明。那高個的象根幡桿,臉色臘黃,一縷灰白的山羊胡子,兩眼瞇成一條細線,把眼珠結結實實地藏起來。胖的也很有特色,酒糟鼻,金魚眼,禿頭駝背,兩條奇短的腿艱難地支撐著一個奇大的肚子,嘴里咝咝地直喘。他們穿制式病員服,道袍似的肥大,而兩根手杖也象探雷器似的佇在腳邊。我真替對門醫院里的大夫們捏著把冷汗。
“兩位老伯,這邊請坐。”我忙搬過兩只板凳,殷勤相讓。不管二位形象如何,總是我們買賣人的上帝呀。
“不啦不啦。”瘦老頭搖搖腦袋,走上幾步,對著一個大號花圈上上下下、仔仔細細地端量。
“您老瞧好這貨色,工藝精細,色彩協調,古樸莊重,滿城里的絕活兒,沒二份兒。可不是那蒙人的玩藝兒。”我湊過去,貼著他耳根廣告一番。
瘦老頭又把頭搖,扭過臉,對著胖老頭,“老哥,您看?”
胖子還在喘個不停,他嗓子里似乎堵了口痰,卻咳不出,憋得呼嚕呼嚕響。這時他沉重地搖搖頭,嘴角往下一撇,看樣子他好象比瘦子更挑剔。
“小師傅,我們想定做兩個花圈。”呼嚕呼嚕地說。
“定做?”“對對,定做。”瘦子忽然興高采烈地做了個肯定的手勢,顯然對胖子的提議極力贊同。接著他捋著山羊胡子沉吟片刻,說:“當然了,還要相煩貴店代為保管,我們可以預付保管費。”
“保管?”我更覺納悶兒,真是兩個怪物。
“我們是給別人預備的。也許一時還用不著,不過有備無患,反正早晚要用的。”胖子怪笑一聲,令人毛骨悚然。
我還是頭回遇到這等怪事,預定花圈而且有備無患,何異于咒人家早死。荒唐。我疑惑地看著兩個老頭。“我說要有仙客來、鳳仙花、朱頂紅、扶桑。”胖子喘著說。
“還是君子蘭、百合、六月雪好,干嗎搞得花里胡哨的。”瘦子不以為然,顯然兩人的審美觀不同。“盡量大一些,氣派點,我們不怕多花點錢。”胖子也不和他爭執,又提出具體要求。瘦子意味深長地看我一眼,說:“怎么樣,小師傅,說定了,過兩天我們就來看貨。”
我答應了。不管他們是何居心,有何目的,這畢竟是樁好買賣,況且我想在經營方式上也跟上改革潮流,除了送貨上門,其他都可一試。
兩個老頭又說了些感謝話,才告辭而去。
我趴在窗口,望著兩個漸漸遠去的背影,他們步履艱難,幾乎全靠手杖的幫助才勉強拖動腳步。我心里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
在醫院的墻角處,他們站下了,大概是在歇息。這時馬路上一片喧囂,銀灰色的“皇冠”,鮮紅的“鈴木”,抱著孩子的婦女,拉蜂窩煤的架子車……萬花筒般的世界在他們面前匆匆閃過,誰也顧不上看他們一眼。
夕陽把昏蒙蒙的天空染得發紫,暮靄濃重,天快要黑了。
父親聽了我對兩個老頭的描述和奇怪的定貨并沒感到驚訝,只是把頭垂到胸口,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接著又喝酒,一盅接一盅。
父親精心制作了兩個特別花圈,擺在最顯眼的位置上。兩個老頭非常滿意,痛痛快快地付了款,又付了一筆保管費。有些很體面的顧客要出高價購買,都被我回絕了。那簡直就是一對藝術珍品,它們為小店增添了異彩。
以后每隔三兩天,兩位老人就要來看一次。每次都在下午。瘦老頭對著君子蘭,胖老頭盯住鳳仙花,都不說話。發一會呆,便踏著暮色回去了。
我已經揣摩出這兩個花圈的主人。我剛剛讀過一篇外國小說,講的是有個單身老頭,害怕死后孤獨,便給自己預定了許多花圈,使花圈店的老板大受感動。中國老頭畢竟沒有那么奢侈,大概他們各自給自己預備下一個。看著他們那副虔誠的樣子,我真以為他們要親自肩扛花圈,奔赴另一個世界。每當他們默默地站在花圈前,我的心就立刻緊縮起來,我恐懼地感到了什么叫孤獨、寂寞、凄涼與悲哀。
一個昏黃的傍晚,風緊云低,看樣子就要下雪了。我正要關店門,忽然瘦老頭來了。“是他一個人。”我立刻預感到了什么,心里象有只秤砣死命向下一墜。
他的氣色壞極了。臉上顴骨突現,沒一點血色,眼窩深深地眍了進去,露出一雙昏慘慘木呆呆的灰眼珠。他艱難地挪到那個扎著鳳仙花的花圈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接著慢慢轉過身,用暗啞的嗓音對我說:“小師傅,我來……再看他一眼。”
“那位老伯,他……”
“去了”
“幾時?”
“昨天晚上。”
我悵然若失,呆呆地看著那色如凝血的鳳仙花。“他不需要了,再也不需要了。可惜,他沒能帶走。”老伯的胡須微微顫抖著,他的腿和手杖也在顫抖。
“他沒子女嗎?”我忽然想到這一層。“四個。”他凄慘地笑了一聲,嘆道:“活著孤獨,倒是死了風光榮耀,花圈、車隊,象是躺著又游了一回街。可憐,可憐呀。”
“家屬為什么不來取?”我指指那花圈。
“兒媳婦怕花錢。”
“不是早已經付過了嗎?”
“她還沒來要錢嗎?嗯,會來的。”
“唉……”我還能說什么?我有權拒絕那個混帳女人來繼承這筆“遺產”嗎?
“小師傅,今天我才看透了,人死燈滅,還要什么風光排場,我空手去見閻王爺,隨便他如何打發我吧。”
我鼻子發酸,好象突然領悟了一點人生的真諦。看著他那副失魂落魄的哀容,我一時找不出合適的話安慰他。
我把老伯攙出門外。天上已紛紛揚揚地飄起了雪花。路上的行人和車輛都變得小心謹慎起來,這一刻人們把生活的節奏放慢了。有個背著書包的男孩奔跑而來,一邊興奮地大喊大叫。孩子的母親急得跺腳,喊聲都走了調:“寶貝,慢點,小心跌跤啊。”
來到醫院門口,老伯一把攥住我的手,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孩子,謝謝你了。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后一個朋友。我的時間不多了,可這段時間對我來說已經是太長了。我只求你一件事,你回去把那兩個花圈賣掉吧,趕緊賣掉。”說完,他頭也不回地去了。
冰冷的雪花落到我臉上,我不由打了個冷戰。好冷的天哪,一陣寒風把我的心冰得硬梆梆的。
我蒙頭大睡,但怎么也睡不踏實,紛亂的思緒哪里理得清。后來我終于下了決心,我要違背老伯的意愿,我要讓他把兩個花圈一起帶走。
窗外已是一片銀色的世界。天空放亮,漸漸地強烈炫目的光線直撲到我的臉上。不知為什么,父親竟破例沒來踢我的屋門。
我頭昏腦脹地走出里屋,倏地發現那兩個花圈竟然不見了。
“那倆花圈呢?”我氣急敗壞地沖父親吼道。
“賣啦。”父親得意地對我揚了揚手里的一沓鈔票,“嘿嘿,賣了個大價錢。”
作者簡介金弓,原名靳永強,男,32歲,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