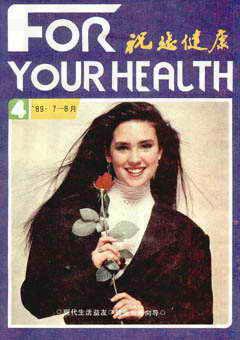端的是“靈丹妙藥”
南 北
我四歲上學,總是得第一名。不是全班第一,是全校第一。我的名字寫在大紅紙上,大紅紙貼在高高的墻上。我從小受到老師的寵愛和同學的崇敬。經常有全班罰站我獨坐的情形。初一時同學們就喊我“博士”;不到二十歲的大學生被稱為“托翁”。這固然包含玩笑性質,可這玩笑并不是沖什么人都開的啊。其實我上學的訣竅很簡單,就是“認真”二字。課前認真預習,課上認真聽講,課后認真復習和做作業。辦事認真無疑是一種好品格,它使我吃了不少甜頭。但我很快把這種好品格推到了它的反面。“認真”成了我的一種桎梏。比如,不認真做完作業我就不能安心干其他事,更不能去玩。我是個電影迷,但我總擔心學校在星期六下午組織看電影,因為星期六下午作業肯定沒有做完,電影也就肯定看不踏實。
耿直也無疑是一種好品格,但我也過于耿直,什么事都直來直去難免磕磕撞撞。
以我這樣一種個性缺陷,又在“左”的路線時期長大,經歷著過多的政治運動,心理的刺激和創傷可想而知。
大學畢業后,我就感到我特別過敏。別人不當回事的,我認為很重要或很嚴重,漸漸地產生了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態。1969年的一天,我去一所大學采訪,碰上那里正在批斗所謂“現行反革命”:一位女學生忙于寫大字報和大標語,幾天沒休息,昏昏沉沉中把一條標語組接錯了,成了一條反動標語。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從此后,我寫任何東西都要反復檢查,生怕寫錯了,但越檢查越不放心,以致幾乎不敢寫字。雖然我以極大的毅力進行克制,卻付出了許多不必要的重復勞動,尤其苦于終日里心情緊張。這種不放心的強迫觀念和反復檢查的強迫行為不斷加重和擴展,發展到極其怕臟,特別怕尿。這自然與我從小過于講衛生有關系,但這時的怕臟已不是擔心得病,而是擔心手臉沒洗干凈會妨礙眼睛看字而不小心寫出反動標語來。于是我成天不停地洗呀洗呀,一次可以洗掉一塊肥皂,一洗就是十來個小時。實在是苦不堪言。
為了治好強迫癥,我遍訪中西名醫,卻_二點效果也沒有。1986年lO月,我反復考慮得出以下結論:一、這種病太痛苦,不堪忍受;二、這種病不可能治愈;三、既然自己成了廢人,就沒有必要再活在世上。于是有一天趁家中無人,我毅然吞下400片利眠寧。
我被搶救過來后不久,朋友們聽說南京有個魯龍光,便不由分說將我送到南京。當時正值魯主任開辦“疏導心理療法”的集體治療,我漫不經心地坐在百十號病友中間聽講,不料,越聽越有昧,這些科學的正確的真實的可信的知識,竟是我前所未聞的,我仿佛從地獄門口看到了一線光明,立下決心,與魯主任密切配合,認真領悟、刻苦實踐,努力矯正強迫觀念和強迫行為。一周后,我寫了一封數千言的長信向關心我的朋友們報告喜訊:我的頑癥已經基本痊愈!我感到我簡直如風凰涅磐,獲得了再生,似乎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充滿活力和朝氣。曾經死死箍在我精神上心理上的那個“金箍”猝然斷裂,“乒”然落地。從南京回家后的幾個月里,我不斷加深認識、反復進行實踐,使認識與實踐和諧地同步,終于使所有癥狀全部消失,完全恢復了健康。
而這,完全歸功于魯龍光主任。
科學考察發現,人類當代各種疾病中,因心理因素致病的占80%以上,且日益呈上升趨勢,如神經官能癥、精神病、高血壓、心臟病,腸胃病等等。這類心身疾病光靠藥物是無法根治的,必須結合心理治療。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心理醫療相當發展,以美國言之,每年大約有l/3的美國人接受心理治療,耗資可觀。但仍有許多領域尚未獲得突破性進展,如強迫癥——就是我所患過的,一種患者甚多,極為痛苦的心理疾病——就被判為不治之癥。
南京神經精神病防治院心理醫療專家、主任醫師魯龍光一我的救命恩人——歷三十年潛心科學研究、廣泛社會調查和刻苦臨床實踐,率先取得突破。其首創的“疏導心理療法”,已治愈包括強迫癥在內的大量心理疾病和心身疾病患者,解除了他們的痛不欲生之苦,被國家授予科學技術進步獎,國外醫學界也驚為奇跡,我的親身經歷更證明其絕非虛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