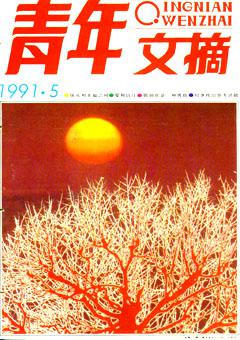艱難的價值
艾 菲
閑談時,友人說要看看我的手相。而當我將手伸開時,他看過卻說道:不用了,對于擁有這么一雙手的人來說,命運是不存在的。
我低頭瞧著自己的手:瘦小單薄,關節突出,紋路粗而密,手心內還有兩個蛻不掉的老繭。
這手使我又想起已很遙遠卻十分清晰的童年。
生在深山里,是家中的大女兒,沒有趕上好年頭,七、八歲時便開始割草、喂豬、放羊、砍柴、燒飯、領弟弟……兒時的我究竟做了多少事如今已記不清了,惟獨只清楚地記著那令我終生難忘的求學之路。
母親在五年內生養下四個孩子。最大的我和最小的小弟只相差5歲,父母都是靠掙工分糊口的農民,整天全泡在農田里忙,管小弟自然是我的事。七歲那年我上學了,小弟沒人管,于是我走上了一條奇特的求學之路。
家離學校有一里多遠,是山路,極不好走,且要走一段從石壁上鑿出的路。每天一大早,我便領著弟弟去學校,課堂里的小板凳極窄,容不下我和小弟同坐,只得把小弟放在我的課桌旁,然后聽老師的課。中午放學該回家了,又累又餓的小弟早已走不動了,我從課桌的抽屜里拿出一條寬寬的白布帶,將小弟捆在背上。
每天要領著小弟來回走四趟,有時,實在挨不住那份苦,便和小弟一起,坐在清清的溪水邊放聲大哭,哭過了,仍然彎腰背著小弟去學校。幼小的我就這樣度過了四年的小學生涯。
11歲那年考上了中學,中學在山外邊的公社里,離家足足十里地。每天天還沒亮就起身,挎上竹籃子(買不起書包,到高一時才攢下1.9元錢買了一個軍用挎包),籃子里放幾本書和練習本,還有一罐用一個破搪瓷杯裝的午飯。深山中人煙稀少,十里地不見一個村莊。我每天提心吊膽地走著,碰到野豬、野牛在山巖上嗷嗷地吼,我發瘋似地跑,邊跑邊哭叫。
夏天常下暴雨,山洪暴發溪水泛濫,我過不了溪,只能靠山的一邊走,硬是從樹林野草地里摸索著往家走。到家里,天已大黑,我渾身透濕,手上、臉上、腳上早已被山上的荊棘劃出一道道血口子。
冬天里,寒風順著山谷走,山谷里出奇的冷,溪邊的巖石上掛滿了冰柱,但我每天仍然得脫四次鞋子,光著腳趟過那刺骨的溪水,一上岸,腳便凍成又紅又腫的一團,不停地揉著,還得擦那止不住的眼淚,跑著趕到學校上早自修。碰到天晴的好日子,回家路上,我盡量撿些枯干的樹枝和竹根放在竹籃子里,帶回家,讓勞作了一天的父母燒火。許多年以后,同班里一個生在北京的同學聽我談起這段生活經歷時,她大睜著眼睛驚奇地問,那你為什么不住校?
生活得太難了,于是產生了一個強烈的愿望,我要走出這大山;離開那與世隔絕的山谷,要去看看書本上畫的大橋、高樓和大馬路……
也許是苦難的驅使,讓我克服了許許多多困難,真的看到了大橋、高樓和寬廣的大馬路。
清清晰晰地記得,上大學的第一年,我第一次見到了一個兒童公園,看到穿著花花綠綠衣服的城市孩子們在那里拍著手歌唱,我依著一棵樹,貪婪地望著,望著……眼淚撲簌簌地淌個不停。
以后,我帶著碩士學位,遠遠地離開了家鄉的山谷,來到了北京,童年的生活離我越來越遠了,但幼年的一切卻都與我的生命永遠地融合在一起了。
我不會象別的二十多歲的姑娘一樣,因為離開父母、離開京城去基層鍛煉一年而大吵大鬧,不會因一只死耗子大呼小叫,也不會對一雙沾滿糞土的大手表示不屑。我也會埋怨,也會發牢騷,但我在埋怨,在發牢騷的時候,從不敢拉起那副天下人皆負我,天下人必須為我、寵我的架勢。我也常會在艱難挫折面前垂頭喪氣,但我還從不曾絕望過。童年讓我學會了倒下了必須再爬起來,也開始知道了只要努力,總能爬起來,我知道了人生就是這樣,象上中學時那樣抹著眼淚,揉著腫成一團的腳往前走……沒有絕望的余地——你只能艱難地往前走!
(李璋立推薦,摘自《中國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