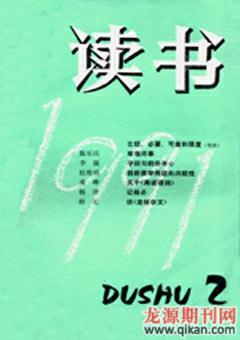影戀與社會病
蕭國亮
十月間在蓉城參加中國社會史學術討論會,遇柏石先生,他以潘光旦著《馮小青》一書相贈。這是我國著名優生學家、社會學家潘光旦的早年舊著,現經禎祥、柏石詮注,并用白話語體作了譯解,又補入作者生前曾發表過的兩篇考訂馮小青的文章,集錄了明清之際有關馮小青的部分史料,使該書舊貌換了新顏。《馮小青》這本研究我國傳統社會中性心理變態歷史現象的科學著作,經這番整理后,一是通俗化了,二是方便了對馮小青現象的進一步研究。性心理學的研究,在中國原本就不發達,后又中斷了幾十年。要恢復研究,第一步就是檢閱前輩學者的成果,以便在這基礎上,再上一層樓。唯獨感到遺憾的是,書名作了一點改動,變為《馮小青性心理變態揭秘》。這樣的改動,似乎是在迎合一種探“秘”的心理。本來對性的問題加以神秘化就不是科學的態度,因此潘先生倘若天上有靈,也許不會同意這么改動。
馮小青是明代萬歷年間的一個弱女子,生于揚州,十六歲時嫁與杭州一富翁馮姓作妾,遭馮妻嫉妒,幽居孤山,性受壓抑,遂患影戀,又添肺癆,不久歸仙。這是我國歷史上性心理變態的一個極好例證。潘光旦做小青的研究,始于他的學生時代。他在靄理士(HavelockEllis)《性心理學》一書的“譯序”里說:一九二○年,他“正在清華學校高等科肄業”,“發見了靄氏的六大本《性心理學研究錄》”,“費了不少的周章以后,才逐本的借閱了一遍”。一二年后,他讀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導論》。他“一向喜歡看稗官野史,于是又發見了明代末葉的一個奇女子,叫做馮小青,經與福(弗)氏的學說一度對照以后,立時覺察她是所謂影戀的絕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啟超)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班上責繳報告的機會,寫了一篇《馮小青考》”(《性心理學》“譯序”第2頁)。這篇《馮小青考》,便是《馮小青》一書的初稿。
梁啟超讀了潘光旦的《馮小青考》后,十分賞識,有評語曰:“對于部分的善為精密觀察,持此法以治百學,蔑不濟矣!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望將趣味集中,務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濫無歸耳!”(潘光旦:《馮小青》扉頁)。這《馮小青考》可視為中國性心理學研究的濫觴。潘光旦篳路藍縷之功,實是不可磨滅。試想當時乃民國初年,封建意識仍濃,在這個視談性為禁忌、為下流、為不正經的時代,《馮小青考》猶如一把投向道學先生營壘的匕首,其反封建的傾向是何等鮮明,其沖決封建羅網的科學精神又是何等可貴!潘光旦研究小青影戀現象,并非僅是出于對一不幸弱女子的同情,更非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改變社會對性的傳統錯誤認識和揭露傳統社會對女子性欲的粗暴壓抑。《詩經》周南召南之風教,所主張的是“好色而不淫”,提倡的是“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社會政策。但是,自理學興,這種關于性的社會觀與政策便湮沒無聞。像在“食”的方面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樣,在“性”的方面是少數權貴豪富的過度縱欲與大多數人民(尤其是婦女)的性欲壓抑。潘光旦正是為了挽回這種社會頹風而從事性心理學的研究的。
靄理士說:性沖動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正常的滿足一定要有另一個人(異性)幫忙,講到另一個人,我們就進到社會的領域,進到道德的領域了”。(《性心理學》第5頁)因此,在“食”與“色”的問題上出了毛病,就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了。既然是社會問題,那么要解決“食”與“色”方面的病態問題,就不僅僅是醫學的責任了。“假如一個病人的病是工作過度或營養不足的結果,試問他(醫生)對于所以造成工作過度與營養不足的種種因素,又何嘗能控制呢?”(《性心理學》第5頁)所以小青之患影戀,出現性心理的變態,或稱病態,除了性心理的原因之外,實在是社會病的反映。
性心理變態實際上是一種精神病。根據弗洛依德的學說,如果正常的性生活受到壓抑遏制,就會使人形成種種心理上的創傷和出現精神病狀態。“其以阻遏之方法行之者,必使欲流退潰或橫決,形成種種精神上之變態,名之曰精神拗戾(Psychoneuros-is)。”造成這種病態的原因,就主體而論,在于遺傳;就客體而論,在于社會環境。要從主體上根除這種病態,在于倡導優生;要從客體上根除這種病態,就在于改造社會環境,使性生活能夠合理而正常,減少壓抑與遏制。就此而論,潘光旦后來走上優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道路,正是為了從這兩個方面去根治人類的這種人造的病痛。
小青所患的影戀,是自我戀的一種,屬于性心理變態。所謂自我戀,是指一切不由旁人刺激而自發的性情緒的現象。廣義的自我戀也包括一切性沖動經抑止或禁錮后的變相的表現,這種表現有病態的,也有常態的。病態的自我戀,患者的性情緒可以大部分甚至全部分都被自我贊美所陶醉而吞并,因此在精神上已無異性戀存在的余地了。小青的影戀是病態的自我戀。她十六歲嫁給杭州馮公子作妾,先是在性生活方面橫遭馮生的蹂躪,她在與楊夫人永訣書中說:“結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如斯。”可見,這對她的性心理是重大的打擊。繼而遭馮妻之妒,幽居孤山別業,性生活受到禁錮,遂患影戀:“時時喜與影語,斜陽花際,煙空水清,輒臨池自照,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即止,但見眉痕慘然”。(《揭秘》第4頁)在小青影戀時期,其“幽憤凄怨,俱托之詩或小詞”,從中亦可窺見小青影戀的心跡,例如:
詞一首天仙子
文姬遠嫁昭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零零清涼界。
原不是鴛鴦一派,/休猜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著衫又捻裙雙帶!
這首詞中的影戀現象是十分明顯的。有的學者認為,詩詞等文藝作品是苦悶的象征。江河受到阻礙之時,會卷起浪花,兩塊硬石進行碰撞的時候,會迸發出燦爛的火花。小青的這些詩詞顯然是她的感情生活遭遇波折的產物。且不說小青日常的性生活遭到禁錮,就是這種影戀生活也難以順利進行。影戀生活與異性生活,形式不同,但是同樣不能不無相當之隱秘。小青時刻在馮妻監視之下,她身邊的“女奴”,名為隨侍小青,實則是小青影戀生活的障礙。中國封建社會根本不存在什么Privacy(隱私權),小青的影戀生活常遇阻礙,結果便以詩詞的形式渲泄出來了。
不久,小青又添癆癥,“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揭秘》第60頁)臨死之前,請來一良畫師,三易其圖,終成小青像。“取供榻前,
究小青患影戀而死,固然有種種原因。潘光旦在書中對此甚有研究,尤其于遺傳方面的原因探究尤詳。從社會環境方面來看,封建傳統對女性之壓迫,實是小青患影戀而死的重要原因。現舉要而論之如下:
其一是早婚。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氛圍之下,傳統社會崇尚早婚。小青十六歲結婚,實足年齡剛滿十五年,性發育尚未完全,此時就過婚姻生活,是較為容易引發性心理變態。何況小青體質贏弱,早婚更為有害。
其二是性生活之不調適。在傳統社會,視女子為男子發泄性欲之工具和生育的工具。婚姻根本不以感情為基礎,而決定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青是個重情感的女子,卻要她與一個沒有任何感情可言的陌生男子進行性生活,在心理上已是一次打擊。此外,這個馮公子“性憨跳不韻”,視小青為泄欲之工具,“結
其三,是婚姻制度。中國傳統社會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這種婚姻制度之下,妾在家庭中地位遠低于妻。因而妻妾有別,《白虎通·嫁娶》解釋為“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可見,妾只是男子為了淫欲或傳宗接代的需要而買來的“以時接見”的工具。在這樣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家庭關系格局中,小青對于馮妻,只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馮妻的淫威,對小青來說,是雪上加霜,迫使其影戀之加深。
社會的病態造成了小青影戀的性心理之病態,所以,小青除了被這個病態的社會所吞噬之外,根本沒有一條生路。小青對此,竟有幾分自覺。楊夫人曾勸小青改嫁,小青答曰:“妾夢手折一枝花,隨風片片墮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徒供群口描畫耳。”(《揭秘》第34頁)在這個病態的社會里,天下烏鴉一般黑,哪里有小青的活路。“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是當時極大多數婦女共同的怨訴!在這個病態的社會里,患有影戀,或其他性心理變態的女子實在不是少數。潘光旦通過對清代女子詞選的觀察后指出:“中國女子之體力脆弱,精神郁結者,為數必大,而智識階級中之女子為尤甚。此其原因大都與性生理或性心理之不能自然發展有密切關系。”(第49頁)所以“馮小青現象”的背后是傳統社會的病態,這樣的社會已經病入膏肓了!小青對于改嫁,又曰:“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里”(同上書,第34頁),表現出深刻的絕望。在這種絕望里,不僅反映了小青自己對于“應付異性戀之環境”能力的無把握,同時也表現出她對整個傳統社會的社會病態無藥可救的價值判斷。在那些封建衛道士對傳統社會的贊美聲中,一個身患精神病的弱女子卻已意識到它的僵死、沒落。真可謂世人皆醉,唯小青獨醒了。
留給小青的最后一條生路,只是絕情而遁入空門了。但是,小青卻說:“若使祝發空門,洗妝浣慮,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而未易言此也。”(《揭秘》第34頁)小青本有學佛的天賦,十歲時有老尼授以心經,即能成誦。但是她自知絕情之難,斷然拒絕了出家之路。佛經內典有說:三十三天,離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這是佛教徒從絕欲經驗中得來的真諦。小青自知做不到絕情,坦然言之,在舊禮教壓迫的女子之中,是難得的。情欲是生命的沖動,小青不愿絕情而遁入空門,真正表現了她對生的渴望,對生活的熱愛,對真摯感情的追求!但是,在這個病態的社會里,該生的卻死去了!小青之死,悲也夫,冤也哉!
一九九○年初冬于北大未名湖畔
(《馮小青心理變態揭秘》,潘光旦著,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年五月版,3.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