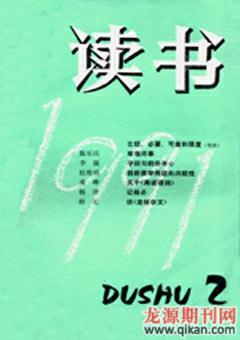詩靈的對話
許 結
十八世紀上半葉,中國詩論家黃子云于《野鴻詩的》中說:“詩猶一太極也,陰陽萬物于此而生生,變化無窮焉”,其領悟詩心之自然靈妙如此。一百年后,德國詩壇泰斗歌德合觀中國詩歌與法國詩人貝朗瑞的作品后情思充盈地感喟道:“我愈來愈相信,詩是人類的共同財產”(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可見詩的魔力已在詩人心中架起貫通歐、亞大陸的橋梁。歌德之 后,法國著名詩人吉約姆·阿波利奈爾對作為人類共有財富的詩藝有更深的理解“這種財富雖然是屬于全人類的,但是它是這個民族和這個環境的表現”。這一觀點如其說是對歌德思想的推闡,毋寧說是法國詩人對中、法詩歌交流的回味、思索。因為早于歌德一個世紀的法國傳教士叩開東方古國神秘大門時,中國古典詩歌這一人類奇妙的藝術已引起了法國詩靈的振蕩。由此肇端迄今歷時二百余年的法國漢詩研究,始終以“人類共同財產”的心胸和對漢詩所表現之“民族環境”的孜孜探求,而顯其審美價值的。近讀錢林森先生編譯的法國漢學家論中國古詩的論文集《牧女與蠶娘》,正以其慧心與史識向讀者展示了中、法文化交流過程中漫長但卻不乏精采的詩靈對語。
中國是詩的國度,其民族文學之精髓是詩歌藝術。漢詩創造,“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朱承爵《存余堂詩話》),以收“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嚴羽《滄浪詩話》)的美感效應,故對此高妙玄遠之藝術的理解,東、西方學者因時空的距離必然存在思想上的隔膜。而試圖打破這層隔膜,以詩人之心體味詩人之意,形成一種心靈的交互,正是《牧》書向我們介紹法國人探究中國古詩奧奇的可貴嘗試。法國漢學界第一位出版研究中國詩人專論《嵇康的生平和創作》的侯思孟(D·Halzman)于《牧女與蠶娘序》中直截了當地指出:對待中國古詩“試圖用‘科學辦法處理”“是徒勞的”。因此,他以“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之心,沉潛于漢詩的翻譯和研究,為《牧》書所選的《論阮籍二題》文,正其從“詩歌與政治”的微妙關系契入,對阮籍《詠懷》詩中內含“追求長生”與“神秘主義”之心態的昭示。這種詩靈的感蕩作用,在被法國漢學界譽為“我們的光芒”的保爾·戴密微(P·Demieville)對漢詩的研究中尤為顯著。他的《中國古詩選·導言》(譯者更名為《中國古詩概論》)對中國詩史之發展作縱向研究后品鑒詩歌之自然美時指出:“近三千年來,一個最平凡而又最靈敏的民族能夠用這種詩歌來溝通情感,她把這種詩歌看成是自己智慧的最高表現。她依靠這些詩歌營養而獲得新生;她在詩中尋找鼓勵和慰藉,追求一種近于酒醉,中魔或狂喜似的心搖神蕩的境界。”(第62頁)戴密微所感受到的如癡如迷、如醉如狂的境界,豈不正是來自中國詩人“靜言深溪里,長嘯高山頭”(王維)的寧靜之心、曠放之情,且與中國詩論家“妙造自然,伊誰與裁”(司空圖)的精神冥符默契。可以說,戴密微是沉醉在中國古詩的幽深智慧,才能從詩歌的題材、詞句和成千上萬的意象中“發現中國浩瀚無垠的疆土,與人類相適應的宇宙,以及從心靈深處發出來的超越語言的低沉的回響”,并在“一個一切都是寧靜、純樸、悠逸的世界里發現自我”。(第63頁)這個“自我”,無疑兼綜了詩人和研究者的雙重情愫,而使詩靈于交互中一體凸現。如果說前引戴密微的觀點是對中國詩歌審美世界的總括之論,那么,《牧》書中收錄了他的另外兩篇專論《禪與中國詩歌》、《中國文學藝術中的山岳》,則是這種理論觀念的具體闡發。前一篇文章是通過對中國佛教中的詩歌和詩歌中的佛教之互解,以明辨“禪”在漢詩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對日本詩歌唯美思潮的影響。后一篇文章標舉中國詩歌創作中“山”的意象,以發揚中國古人“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劉勰)的審美感受;同時又經過對眾作家復雜心態、眾作品多層趣味的開掘,揭示了中國文學之“游”的精神與“眩”的主題。法國學者研究漢詩能不拘抽象概念的詮釋,而作深層義理的發明,確有“以不息為體,以日新為道”(劉禹錫)之功。《牧》書選錄的吳德明(YvesHervouet)《李商隱詩歌中的短題詩》,文中倡言“把李商隱研究從自古到今評論家的拘謹與偏見中解放出來”,“然后,從詩作本身發現其象征意義或深一層意義”(第347頁),顯然是帶有極強之審美體驗的感悟之語。
法國人研治中國詩,是屬于兩個文化傳統的“對語”,因而其思維定勢與研究方法亦頗為不同。在中國古典詩論尚處于“言志”與“緣情”之辨,“性靈”與“格調”之爭時,法國學者卻已開辟了一種以全方位的文化視角對中國古詩進行研究的方法。如果說Ed·比奧一八四三年十一月發表的《根據<詩經>探討古代中國的風俗民情》啟響以文化學研究漢詩之新音,這經圣·德尼的長篇論文《中國詩歌藝術和詩律學》、馬塞爾·葛蘭言的著作《中國古代歌謠與節日》的發展而為法國漢學最基本的觀照方法,那么,中國近代學者聞一多于《匡齋尺牘》開創的用社會民俗學研究《詩經》的路子,顯然已晚于前者一世紀,此間包含的東、西文化交流之“反饋”意識,是不可輕忽的。就法國漢學本身言,假如說伏爾泰的《中國孤兒》開啟了法國漢學史上中法文化在戲劇中的交流,形成了十八世紀中法文學交融的第一個潮頭,則法國詩人克洛岱散文詩《認識東方》、瑟加蘭獨特的詩集《碑林集》以及大量的學者研究中國古詩專著的出版,無疑開拓了中法文化在詩歌中的交流,涌起了二十世紀中法文學交融的又一個潮頭。由此觀之,《牧》書的編譯問世,正是全面地向中國讀者展現了法國漢學界以文化學觀照中國文學之方法與法國漢詩研究在本世紀之興盛的雙重意義。在其選譯論文中,匈牙利漢學家特克依·費倫茨的法文專著《中國哀歌的產生》內《論屈原二題》,是從東、西方文化大氛圍作綜合的比較研究之典例。作者改變了法國早期漢學對漢詩所作的經院式文化考索,而是滲互著自己強烈的情感意識,通過對西方哀歌理論的鑒定和東方古代社會文化形態的檢測,不僅認為哀歌系“古代中國詩歌中最成功的、占主導地位的體裁”(第134頁),而且將屈原《離騷》對哀歌理論的積極貢獻與屈原詩派的雙向(尋求理想與拋棄理想)發展予以清晰地勾畫。能夠宏揚法國漢學以探求中國文化奧秘為主體、以多層面文化透視為方法之精神而達致一新境界的,是《牧》書選譯的桀溺(J·P·Diény)研究漢樂府《陌上桑》和《古詩十九首》的兩篇論文。在《牧女與蠶娘——論一個中國文學的題材》中,桀溺以大文化史觀從西方馬卡布律的《牧女詩》與中國漢樂府《陌上桑》的比較研究入手,對桑園文化背景和羅敷藝術形象進行了既通體觀照而又精深入微的歷史考察,作出羅敷詩“概括了一個悠長的過去,以及一個最有原始想象和基本沖突的領域;……它把同樣豐富、標志著中國文化兩個時代的前后作品連接起來”(第206頁)的見解。這一新見絕非蹈虛之語,而是作者從中西文化之異同探索“桑園文學”題材由“民間傳說階段”、“道德家反對階段”、“牧女詩與桑園詩平行發展階段”到“道德化階段”、“緩和階段”五層次的邏輯推衍得來;從此角度對中國詩學一古老主題的發現,誠如編者《譯后記》所云:“無疑會開闊我們的視野,具有啟迪意義”。至于《古詩十九首》,是中國詩壇之“謎”,無論其作者、創作時間或思想內容、藝術風格,都極為神奇地纏繞于我國研究家的腦際,致使結論齟齬,莫衷一是。而桀溺《論<古詩十九首>》一文,是于不同的文化視角對此“詩謎”的破譯,其中特別是對《古詩》何以博得“詩母”美名這一思想主旨的選擇,是彌足珍貴的。作者認為:《古詩十九首》取得“詩母”美名,關鍵在其“具有一股獨特的更新力量”(第208頁);而認識這一點,又必須深入《古詩》產生之時代(漢代)的文化機制,尋找來自先秦中國文學之源的詩、騷傳統,從而確認其對詩騷的整合、遞變、重建而出現的新詩體、新精神。清人章實齋論中國文學:“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所從,文人情深于詩、騷,古今一也。”(《文史通義·詩教》)誠哉斯言!倘對照桀溺予《古詩》的審美觀照,這種深諳中國文學精微奧妙之“悟心”為法國漢學家道破,不禁令人有云山萬里、靈犀自通之感。這一精辟之論為編者所擷取、所稱賞,又出于其對法國漢詩研究的深切理解。
由于《牧》書編者以其醇深的中國古典文學素養赴法國講授中國文學多年,與法國漢學家過從甚密,所以茲編“入選的篇目,多數是當代法國著名學者推薦的,因而在它研究的課題,使用的方法和達到的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較強的代表性”(程千帆《牧女與蠶娘序》)。在這部論文集中,我們不僅看到編者長期從事中法文學比較研究的心血凝聚和中法學界已建立起的學術友誼、研究信譽,而且能夠通過入選作品清晰顯示編者心中的一幅法國漢詩研究發展的歷史畫卷。概述法國漢詩研究史,大略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十八世紀的發端期;這時的漢詩研究主要表現在對《詩經》的引進、介紹方面。二是十九世紀的開拓期;這時的漢詩研究除了評介《詩經》外,又開辟了如《離騷》、“唐詩”、“宋詩”、“清詩”等新領域。三是二十世紀初的深化期;這時的漢詩研究已由簡單的文化詮釋轉向對漢詩深層文化結構的開掘,取得較大的理論成就。四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復興期;這是在法國三大漢學家葛蘭言、馬伯樂、伯希和相繼棄世形成一段空白后,由戴密微及其學生掀起的復興思潮,其對中國古詩藝術的文化觀照由單向而多元的理論轉移,意味著漢詩研究進入一輝煌時代。依據這一歷史線索,編者于“發端期”因缺乏理論價值未予譯選。在“開拓期”,編者擇取了圣·德尼《中國的詩歌藝術》和于阿里《中國古典詩歌的三個時期》兩篇論文;其中于阿里對“唐詩”“宋詩”“清詩”的理論分析,既有廓除中國古典詩學“唐以后無詩”偏見之功,又對法國漢詩研究有巨大的拓展。在“深化期”,編者選譯葛蘭言《<詩經>中的愛情詩篇》為代表,向讀者披示了該文以“主題”性研究恢復《詩經》之情歌本質、駁正宋儒《詩》學以“禮”窒“情”之曲誤的深邃思考和洞察能力。而《牧》書入選戴密微三篇論文,使該書學術價值達到高峰,這既標明法國漢詩研究的“復興”,又表現了編者廣闊視野中之精識所鐘。要言之,是戴密微以其精深的漢學造詣開創了法國科學的中國詩學研究新紀元,才贏得近代法國漢學的空前繁盛。這里包括了戴密微的高足桀溺、侯思孟、吳德明諸先生研究中國文學取得的卓著成就。在這些中國古詩專家的研究著作中,或從中華民族文化傳統和社會文化心理作宏觀透視,或從特定文化背景、語言環境對一作家、一主題、一門類作鉤汲眢沉的探究,然其以文化之觀照深入于詩靈之體悟,殊為一貫之精神。面循此“史”跡,讀者還可以看到法國漢詩研究方法因革推移、悉由漸進的發展。這在由圣·德尼的文化學之單向研究到戴密微、桀溺等文化學的多元研究有明確演示。應該特別一提《牧》書中法籍華人學者程紀賢(Franfois Cheng)《論<春江花月夜>的內容與形式》一文。這是一篇運用法國結構主義方法分析唐詩的佳什,文中首先從語言符號學的角度考析了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韻腳、音調的對稱與對偶,字的重復、音樂效果、詩的節奏等內部規律,攫住“江”和“月”的“內在的結構”(深層結構),進行歷時性和共時性雙重研究,以明其“孤篇橫絕”之意境美。如果說這僅是作者運用結構主義批評詩藝之個例,那么程氏《中國詩語言研究》便是采其方法描述中國古典詩歌藝術深蘊的精湛著述。這種以結構批評之符號學原理對中國古詩內部特征的細密解析,不僅意味著法國漢詩研究方法的嬗變,而且與近年來我國新生代古典文學研究更新方法之呼聲桴鼓相應,顯出中外文化在方法論層次上的新交互。可見編者之心,亦冀以“他山之石”提供給未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以借鑒。
鐘嶸《詩品序》云:“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這也許正是中法間詩心傳遞的個中妙趣。然“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中法文學交流同樣經過了興廢曲折的歷程,錢先生勤劬編譯這本論文集,未知亦寄寓此深沉意愿否?近悉錢先生新著《中國文學在法國》已由花城出版社付梓問世,其《中法文學交流史》也將結撰,歌德“東方西方,不可分離”之古老“預言”,在這里將奏響更為雄壯的樂章。
(《牧女與蠶娘》,錢林森編,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5.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