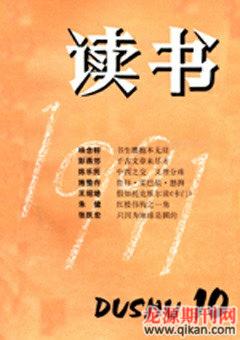假如托克維爾讀《卡門》
王紹培
今年的元月號《讀書》到了林斤瀾和許紀霖手里,大概會令他們分別高興吧——因為,林斤瀾在《讀<卡門>雜感》中提出的疑問,恰好在許紀霖的《終極關懷與現代化》文中有所討論。
林斤瀾的疑問是:
這個只要自由,死也要自由的吉卜賽女人,她的靈魂里卻有極不自由的宿命觀念。為了自由,毫不遲疑,全無懼色的去死。給她充分的機會逃走,也不脫逃,因為是“命中注定”!這個命又是鉛條、咖啡渣子……都可以左右的,難道這不是極不自由嗎?(86頁)
按照我們流行的觀點,自由是對必然的掌握,這當然與宿命觀念不相容。宿命觀念與宗教信仰還不同,起碼有層次、境界上的差異吧,但大類上也相同。總之是:信上帝的人也不自由。然而卡門既極為自由,又極為信命,故此,林斤瀾說:
我感受到深刻。(87頁)
為什么深刻?是什么深刻?林文沒有明確作答。因為,對作者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梅里美小說中的“魅力”是什么。從上述疑問和感受里,答案似乎有了線索:
天老爺是長眼睛的,連作者也這樣寫了,也沒有暗示更沒有明示這樣的意圖不過,我也長著眼睛,明明從寫出來的東西里看見了這個意義。再看三看,越發看見意義的深刻,一時以為那神秘的魅力是從這里出來的了。(89頁)
這里省略了不少話。假如我們嘗試作些補充,比如說,之所以“深刻”,是把不可能的東西揉在一起,表現出了行動與心靈的“矛盾”。林文里有沒有這個意思呢?且不詳說吧。這里有這么一個問題,就是:一個信命或者信上帝的心靈,能否有自由?
按照托克維爾的意見,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換言之,上面所說的“矛盾”并不存在。托氏說:
人要是沒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自由,就必須信奉宗教。(17頁)
設想一下讓托克維爾讀《卡門》,會不會有詫異之感或深刻之感?大概不會。假如會的話,恐怕也是基于為什么信“鉛條、咖啡渣子”也能自由。
總之,要想自由,必須有信仰。
為什么?
許紀霖文中講到過“近代意義上的自由起源于新教改革,路德的‘因信稱義說賦予人的內心信仰以神圣的、獨立于外界的性質,使人具有一種不承認《圣經》以外任何外在權威的自主力量,從而使人的精神在信仰領域內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17頁)不過,許文對自由觀念的歷史淵源語焉不詳,這樣,羅素在《權力論》一書中的議論,頗可引征。
在《權力論》里,自由這一世俗價值觀念與宗教信仰牽上關系,是以另一個世俗價值觀念——人權——為中介的。這也許是《權力論》自然側重探討權力形態的緣故。不過,從邏輯上看,信仰經由人權過渡到自由,也很“合理”。
羅素說到“人權”這個觀念為同時代的人所嘲弄,而且也承認,這種學說在哲學上站不住腳,但是,“它是有益的,我們享有許多它所爭得的自由。”(《權力論》90頁)羅素說:
個人主義與新教顯然有著邏輯上和歷史上的聯系。新教在神學范圍內維護它的學說,雖然當它執政時,往往將這一學說拋棄。通過新教,它與早期基督教,以及基督教對異教國家的仇視發生關系。它與基督教也有一種較為深切的聯系,因為基督教與個人的靈魂有關。按照基督教的道德觀,沒有一種國家的需要可以證明官方強迫人民做壞事是正當的。……康德的原則,即每個人本身就是目的,是源于基督教教義的。(91頁,同上)
與權力有關的最重要的基督教教義是:“我們應當服從上帝而不是人。”……在基督教看來,超自然的真理是至關重要的。他們認為,如果他們對那唯一真實的上帝之外的東西做禮拜,他們將有被罰入地獄的危險,相比之下,他們寧可選擇痛苦較少的殉教。
基督徒對于“我們應當服從上帝而不是人”這一原則有兩種解釋。上帝的旨意可以直接地或通過教會間接地傳至個人的良心。迄今為止,除了亨利八世和黑格爾,從來沒有人認為上帝的旨意可以通過政府傳達。因此,基督教的教義是要削弱國家的權力,以便支持個人判斷的權利或受教會受益。(84—85頁,同上)
在我們的某些教科書里,人權這個概念,正和神權相對。人的解放,個人的解放,是基于對上帝的批判。人權的證明與落實,也以對神權的批判與架空為前提。也許,在歷史的某一階段,比如在人權與自由、理性能自主發展的時期,上述論斷也本錯。不過,至少在羅素所探討的新教革命時期,情形恰好相反。個人主義、人權借助了基督教教義以及教會,從而免遭國家、政府等世俗權力的專制與控制。這里并不過多涉及人權、自由的理論內涵,僅僅著眼權力史的角度:個人主義、人權、自由等等,萌生并成長于對世俗權力抗爭的過程之中。當然,基督教包含著個人主義的觀念、以及人權不從屬于世俗權力的觀念,肯定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
羅素的上述議論,不妨視之為以超驗權力抗衡世俗權力,從而獲得自由。還有一種意見,視信仰(包括教會)為“支援意識”(或權威),從而抗拒流行意見,獲得自由。這一意見,海外學人林毓生在《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一書中,多有闡述。
林毓生認為自由的必要前提之一是權威,這一見解大致相當于創造的必要前提之一是“支援意識”,科學研究的必要前提之一是“范式”,不過三者之間還有一些出入,至少有側重面的不同。林氏說:
以寫中國舊詩為例,你必須承認李白、杜甫寫得好,晚唐的李賀雖然有些問題,但也不失他的權威性。服從了某些權威,根據這些權威才易開始你的寫作。(第7頁)
寫作當然要處在自由狀態才好。但也不能因此一切權威一概不認。你總得承認一些規則,才能證明寫作及寫作品吧?當然,林毓生大談權威,是有所指的:
我們中國的人文世界中就是缺乏真正的權威;我們中國就是發生了權威的危機。(同上)
在關于自由與權威的幾篇專論里,林毓生指明了造成權威危機的一大原因,這便是“五四人物”以為自由與權威不相容,對權威大加攻擊,以至各項權威都幾乎崩潰了。
說一點閑話吧:林氏所論當然是正確的。但魯迅、胡適等知識分子也未必不正確。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即以寫作為例,學習寫作當然不妨對諸多大師頂禮膜拜(承認權威),但臨到實際寫作,則不妨如一句經驗之談所說“老子天下第一”。蓋五四人物當時處在“創作”過程中,而不是“學習創作”過程中。如借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他們處在破壞范式、重建范式的時期,而不是鞏固范式、捍衛范式時期。時過境遷,他們因此有局限,無足驚怪吧。
仍回到權威上。權威又是什么呢?林氏說:
權威即是一種使自己的提議被別人接受的能力。在社會上,有創造力的人的提議常被別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而志愿地服膺,并隨之一起前進。在這種志愿的結合中,我們感到有一股力量促使志愿結合的發生,這個力量就是權威。(78頁)
服膺權威,但并不等于權威即是目的。權威之所以為權威,是因為它象征著普遍和抽象的規則,人們對這些規則的學習、理解、掌握、遵循、利用,都是經過權威的示范才獲成功的。從這個意義上看,權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林毓生關于權威的思想引申一下,就可以用來討論自由與信仰。在西方,信仰是一種傳統,也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無論如何,你首先得承認信仰這一既成事實,而且,必須尊重這一事實。關于這一點,大詩人艾略特說:
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們的整個文化也將消失。接著你便不得不痛苦地從頭開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現成的新文化來。你必須等到青草長高,羊吃了青草長出羊毛,你才能把毛弄來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得經過若干個世紀的野蠻狀態。(《基督教與文化》,第206頁)
林毓生提議尊重傳統權威,用意正與艾略特相當。信仰作為自由的前提,其理論上的可能性之一是,信仰是一種重要的“支援意識”。林毓生對“支援意識”的解釋是:
博蘭霓區分人的意識為明顯自知的“集中意識”(focal awareness)和無法表面明說,在與具體事例接觸以后經由潛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人的創造活動是兩種意識相互激蕩的過程,但在這種過程中,“支援意識”所發生的作用更為重要。博蘭霓說:“在支援意識中可以意會而不能言傳的知的能力是頭腦的基本力量。”(第301頁)
信仰作為“支援意識”,作用之一是不媚俗,或者說,抗拒流行的意見。林語堂認為一個哲學家的標志就是“不愿承認現實的全貌的表面價值”,或者“不愿相信報紙上所刊載的每一句話”。(見《人生的盛宴》第18頁)但一個人憑什么敢于懷疑現實及流行的意見呢?他有什么自信?他有什么底牌?這或者是由于理性,對理性的自信,或是由于信仰,對上帝的相信。一個信上帝的人,當然會把所見所聞拿來與上帝的聲音加以比較。反之,一個心中沒有上帝,也沒任何別的“托付”(哪怕是卡門的“鉛條、咖啡渣子”也好),乃至以趕時髦為榮的人,被流行的意見牽著走,那肯定是免不了的。
對我們而言,信上帝當然不是自由。不過,因信上帝而取得了對流行意見的自由,這一事實倒也不容忽視。
海外學人黃仁宇先生說:
很多美國人沒有想起的他們所表彰的“自由”也是一種歷史產物,也有北美合眾國的特殊性格。英文里面有兩個字可以視作自由,一為freedom,一為liberty,前者帶來濃厚的宗教意義。十七世紀的清教徒,在其旗幟之下,深信他們個人接受了神之啟示(calling),遠渡重洋,來北美洲披荊斬棘把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發揮到極端。后者追溯其根源于歐洲中世紀,起先封建領主將城市特權(municipal franchise)授與市民(burghers),等到經濟發展成熟才普及于全民。(《讀書》一九九一年第三期:《摩天樓下的芻議》)
這里,黃先生又帶出了自由的另一個淵源,也就是非宗教的淵源,不妨概略地追溯一下。
中世紀的城市意義極大。假如把希臘的城邦,中世紀的城市與諸大帝國及帝國的城市作些比較,恐怕對西方文明、東方文明的底蘊就能了解一個梗概。這且不詳說。德國社會學家恩斯特·特羅伊奇(Ernst Troelth)說:
只是當崛起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與殘余之中的城市,把來自所有不同社會階層的各種不同的居民聯合起來之時,封建主義的野蠻與暴力得以清除的更高層次的中世紀社會的基礎,才得以奠定。城市作為一種基本的經濟聯合體存在的條件正是和平、自由與所有市民的共同利益,還有工作的自由以及以個人努力和勞作為基礎的財產積聚。(轉見克里斯托弗·道森著:《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184頁)
封建土地制的瓦解這一點是中世紀城市出現的前提。在十一世紀之后的幾個世紀里,政治運作的軸心是國王與貴族的斗爭,來自城市的力量對雙方既是牽制,又有吸引力,但最后勝利者卻是這第三者。城市政治力量的中堅是商人。商人在地方當權,被認為是十分特殊的,因為,當時“在東方諸帝國中,商人毫無機會上升到當權者的地位。”(見《全球通史——一五○○年以前的世界》,465頁)
以商人為主體的市民取得權力的過程是漸進的。最初的實體是“自由自愿的商人社團”,然后是功能有限的“新型市政機構”,再后成為一種獨立自足的常設機構,“他們最后渴望將從前絕對屬于主教、伯爵或封建國家代理人的政治、司法和軍事職責接管過來。”(參見《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186頁)這一進展的另一方面是:
由于自治市的自由民擁有權力和財政資源,他們通常從國王那里獲得皇家特許狀;特許狀準許他們組成單獨的小自治市,享有自治體的權利,可以用自治市的印章簽定協議,擁有自己的市政廳、法院以及市外屬地。皇家特許狀還準許商人和工匠組織行會,或自愿同盟會,用以自衛和互助,其中包括對產品標準、價格和工作時間的規定。因而,城市逐漸被公認為新的社會成分,市民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約。(《全球通史》464頁)
市民的上述種種進展,雖然是在社會層面上取得的,但值得一說的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作用,始終內在于這一進程。文化史家道森指出早期的“社團”、“行會”具有“宗教保護下的自由結社原則”這一基礎;作為“中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創造之一”的自治聯盟也“與教會改革密切相聯”;“在一位圣徒保護下為著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相互援助而結成的個人自由聯盟即宗教團體或‘慈善機構,在作為中世紀城市社會最為顯著的特征的商人行會和手工業者行會中,成為自治聯盟生活大繁榮的種子”。(以上參見《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185、186、187、193頁)最后,中世紀的城市為社會生活的徹底基督教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照此說來,自由的liberty與freedom并不是沒有干系的。
臺灣南懷瑾先生的《論語別裁》頗有意思。《論語·季氏第十六》有段話: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論語別裁》就這段話演繹出“怕的哲學”,說是“人生無所畏,實在很危險,只有兩種人可以無畏,一種是第一等智慧的人,一種是最笨的人,可以不要畏”;又說“我們只要研究歷史上的成功人物,他們心理上一定有個東西,以普通的哲學來講,就是找一個信仰的東西,一個主義,一個目的為中心,假使沒有這個中心就完了”;且說“一定要自己找一個怕的,誠敬的去做,是一種道德。沒有可怕的就去信一個宗教,再沒有可怕的,回家去裝著怕太太。這真是一個哲學,我發現一個有思想信仰的人,他的成就絕對不同,一個人沒有什么管到自己的時候,很容易就是失敗的開始,不然,還是回家拜觀音菩薩才好。”(781—783頁)
信仰是“畏”或“怕”,這層意思德國詩人席勒講到過。席勒以為,一個自然混沌的人無所畏懼,因為他沒有道德意識。一旦他有了道德意識,首先得到的倒是恐懼(參見《審美書簡》)。有些人無所畏懼也真能成大事。但大事也有好壞之分,好的時候固然是好,壞的時候就不敢領教。不過上智與下愚終屬少數,絕大多數還是應有所怕。進一層的話,應有所信吧。據說,在某次宗教學術討論會上,有人有這樣的妙論:
我走到大街上,不怕基督教徒,不怕回教徒,不怕佛教徒,不怕道教徒,就怕那些什么也不怕的小流氓。
一個全無所怕的人,與一個有所怕的人,誰距自由近一些呢?一個全無所信的人,與一個有所信的人,誰的自由多一些呢?一個甚至信鉛條、咖啡渣子的人,是不是肯定就比一個完全無所信的人,自由要少一些呢?要把這些問題弄清楚,就涉及到信仰或宗教的實質了。
如從理論內涵上分析,宗教或信仰又是什么呢?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第一冊中說:
十八世紀英史家吉朋(Gibbon)嘗謂,眾人(the people)視各教皆真(eqeally true),哲人(the philosopher)視各教皆妄(equally false),官人(the magistrate)視各教皆有用(equally useful),則直湊單微矣。(19頁)
不過,吉朋當年所陳說的“哲人視各教皆妄”,現在看來,是有例外的。至少黑格爾對宗教、信仰的看法,就不那么簡單。
黑格爾把意識形態作為精神現象學的研究對象。他說:
精神自身既然是在這個意識因素里發展著的,它既然把
它的環節展開在意識因素里,那么精神的這些環節就都具有意識的上述兩方面的對立,它們就都顯現為意識的形象。敘述這條發展道路的科學就是關于意識的經驗的科學;實體和實體的運動都是作為意識的經驗對象而被考察的。(《精神現象學》上卷23頁)
精神現象學就是考察精神的歷程,這個歷程在不同的階段,表現為典型的意識形態。宗教是其中的一種意識形態。按照黑格爾的劃分,精神現象學有五個大階段:(一)意識,(二)自我意識,(三)理性(以上三者屬于主觀精神的環節),(四)精神(即客觀精神),(五)絕對精神。(見《精神現象學·譯者導言》)宗教是最后這個階段即絕對精神的兩個環節之一(另一環節是絕對知識。另有三環節的劃分:藝術、宗教、哲學)。從這里可以窺見宗教的地位之尊。黑格爾甚至說:
宗教和哲學是一致的。事實上,哲學本身也就是禮拜、宗教,因為哲學在實質上不是別的,而就是在自己研究上帝時拋棄掉主觀的臆測和意見。因此,哲學和宗教是同一的。(轉引自《國外黑格爾哲學新論》)
宗教和哲學的一致在內容,即它們都體現著絕對本質(或絕對精神)。不同處在于,宗教是以表象的形式去把握絕對精神的。就宗教自身而言,它也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即:自然的宗教、藝術的宗教、天啟的宗教。在自然宗教里,精神在意識中,在藝術的宗教里,精神在自我意識中,在天啟宗教,精神具有了自在和自為存在的形態(見《精神現象學》下卷186頁)。黑格爾下面一段指出宗教與哲學(或絕對知識)的差異:
雖說精神在這里誠然達到了它的真實形態,不過這個形態本身和它的表象形式還是一個沒有被克服的方面,精神還須從這一方面過渡到概念,以便在概念中完全消除對象性的形式,而概念是同樣包含它的對方在它自身內的。
在黑格爾哲學中,絕對精神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具體涵義,這些且不展開說。以上引證黑格爾的話,一是表明黑格爾以“辯證歷史”的形式,把不同的意識現象。集合在一個更高的概念當中,以及揭示諸意識形態的是非短長,是較之那種是就是,非就非的思維方法,要高明許多倍的。另一是表明黑格爾并不以為宗教“皆妄”。
當然,不以宗教為“皆妄”的,還有不少哲人,馬克斯·韋伯,克里斯托弗·道森,T·S·艾略特,不僅不以為妄,而且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宗教之于自由,之于西方文化,之于現代社會的巨大意義——這最后一點,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一書,也是再三申論。所有這些,對宗教情緒并不濃厚的我們來說,是值得去仔細體會的。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湖北省社科院哲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