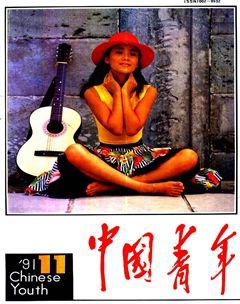里程碑
程棟林 魏群
1991年9月4日,對于中國3億多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來說,是個大吉大利的日子。
這一天,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隨后,國家主席楊尚昆發布第五十號主席令,決定這部中國立法史上前所未有的法規于1992年1月1日起實施。
法律是人類文明進化的產物,用國家的意志來為民族的未來著想,為自己的后代提供全面而系統的法律保護,這無異于一個民族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樹起一座現代文明的里程碑。
立法:共青團功不可沒
中國人民大學力康泰教授感慨萬千:“我,作為《青少年人保護法》的最初起草者之一,10年之后,終于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正式頒布,心情非常激動。”
“十年磨一劍”。一部法規的誕生來得何等漫長,何等不易啊!
在此之前,中國沒有專門的青少年保護法,中國卻有占總人口1/3的未成年人;中國已有的法規中雖然有一些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條款和規定,卻難以發揮總體效應。原則而不具體,零碎而不成系統;重于懲戒,輕于保護;重于防范,輕于教育,這些明顯的缺陷和疏漏引起人們深深的焦慮:在這些未成年人身上,寄托著國家和民族的希望,保護未成年人,就是保護民族的未來;塑造未成年人,就是塑造民族未來的形象。以千秋大業計,為未成年人立法大有必要。
于是,中共中央以其莊嚴的“紅頭文件”明示:“目前,保護青少年的有關法律還不完善,建議立法機關會同有關部門,根據憲法精神,加緊制定保護青少年的有關法律。用法律手段來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權利不受侵犯,防止資本主義、封建主義腐朽思想對青少年的引誘和腐蝕,保護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而以代表和維護青少年利益為根本任務和最高責任的共青團,在其后10年漫長而艱難的立法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團組織雖然不是立法機關,卻為這部法規的誕生殫精竭慮,用“功不可沒”來加以贊譽,并不過分。
地上本沒有路,路是人踩出來的。
1980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指導下,團中央等單位著手調研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青少年保護法(討論稿)》,至1988年1月,團中央牽頭組成了青少年立法顧問組和青少年立法咨詢組,并不定期召開青少年立法工作聯席會議,正式開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草案)》的起草工作。之后,《草案》11易其稿,工作之艱巨是可想而知的。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
在共青團上海市委的積極參與下,1987年6月,上海市率先推出了我國第一部地方性青少年保護法規《上海市青少年保護條例》,這是我國青少年立法史上一次重大突破。
1988年10月20日,《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頒布,《條例》所具有的內在活力以及在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直接法律效力,使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納入了正規化、法制化的軌道。
共青團寧夏自治區委受區人大委托,牽頭起草《寧夏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他們確定了54個調研課題;走訪了全區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學23所、清真寺9座、有關人員500余次;召開各種座談會、討論會34次;寫出了5萬多字的調查報告,征集意見和建議100多條,9易其稿,形成《條例》。
河北省青年聯合會重點抓好維權的組織建設,創造了理事型、議事型、咨詢型三種不同功能的青少年維權組織,使青少年維權組織形成了系統網絡。
遼寧省青聯不斷強化輿論環境的建設,他們和省電視臺聯合攝制《我們的太陽》專題片,以典型事例介紹保護未成年人法規的重要意義,宣傳月、宣傳周、宣傳日活動此起彼伏。
還有廣東,還有福建,還有天津,還有山東,還有四川,還有貴州,還有內蒙古,還有……
一時間,全團上下認準了一個方向:為促進青少年立法工作而努力,這是共青團在變革與發展的社會現實面前頗有作為的一件大事。原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少年立法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劉延東這樣說:“有必要專門討論一下青少年立法與共青團工作體制改革的關系。共青團工作體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完善團組織的職能。在過去的工作中,團組織比較重視‘助手職能和‘突擊隊職能,而在自覺充當青少年權益的社會代表方面就很不夠了,加之團組織作為青少年利益的社會代表還缺少法律的依據和保證,團組織維護青少年合法權益就成了一句空話。因此,青少年立法既是共青團體制改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又是促進共青團體制改革,進而促進青少年工作的一個重要因素。這個觀點不僅團內要搞清楚,還要努力使全社會接受。只有這樣,團組織作為青少年利益的代表,才不僅有理論上的意義,而且有實踐上的意義。”
難能可貴的共識,凝聚起全團上下的熱情、力量與心智。10年來,為青少年立法不斷奔走呼號,積極實踐,共青團始終充當著一個實干者的角色。
雖然“保護神”姍姍來遲,但是,當3億多青少年與“保護神”相擁抱的時候,他們同時向共青團投來深情而敬佩的目光:共青團是為青少年辦實事的!
用法:
讓理性的光芒照耀人的尊嚴
一位專家對《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特點陳述看法:本法從法的名稱到基本原則,從法的內容到法的體系結構,都突出了“保護”這一立法指導思想,而不是著眼于司法制裁和違法犯罪的處理。本法不僅解決了“保護誰”和“保護什么”的問題,而且回答了由“誰來保護”和“如何保護”的問題。這說明《未成年人保護法》既不是單純的刑事法律,也不是單純的民事法律;既不是單純的實體法,也不是單純的程序法,而是為維護未成年人健康向上、民族生存發展、國家長治久安的綜合性法律。
理性是法律的生命。
一部《未成年人保護法》不僅僅使以思考見長的專家學者們產生了這樣邏輯嚴謹的認識,而且更重要的意義還在于,它以不可動搖的意志在不知不覺中向所有的人們滲透著一種理性的力量。在它的面前,感情不能替代判斷是非的標準;約定俗成的規矩不再是行與不行之間的界限,舊有觀念無法抗拒法律的尊嚴。
李霞的母親無論如何也不曾想到,她常常讓上小學的李霞遲到、早退,以至曠課、輟學,到自己家的雜貨鋪子里作幫手、掙錢,這竟是一種侵權行為。艾曉的爸爸也同樣未曾想到,在與妻子辦理離婚手續的過程中,為了爭奪兒子的撫養權,他把兒子藏起來達半年之久,不讓兒子上學,這同樣是侵犯了未成年人應當享有的受教育的權利。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家庭保護一章的第9條明確規定:“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應當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權利,必須使適齡未成年人按照規定接受義務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輟學。”
如今的許多家長,對子女的認識和教育還囿于傳統的觀念之中,許多人認為孩子是自己的血緣延續,因而也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他們或是對子女百般溺愛,嬌慣縱容,其結果是導致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身心健康畸形發展;或是望子成龍,苛刻要求,稍不如意就棒棍相加,使未成年人身心受到摧殘,或是隨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子女婚姻,尤其是在農村,“換親”、“娃娃親”、買賣婚姻、包辦婚姻等屢禁不止。殊不知,這樣做的結果,都是對未成年人應有權益的一種踐踏。父母作為未成年子女的監護人有權利盡監護、撫養、教育、約束的責任,卻沒有權利損害未成年人做人的尊嚴。
“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適應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的特點;教育與保護相結合。”《未成年人保護法》開宗明義,弘揚著人作為人的價值。這是這部法規最根本的意義所在。
貴州省湄潭縣義泉鎮第一小學五(一)班班主任李英蓮,為了懲罰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習,將班上4位差生集中起來,組織全班50多位學生,令每人依次狠揍這4名差生10個耳光,學習成績好的同學還可多打10個耳光。有些同學不忍心打,反遭李的訓斥。這4個被打的學生有的被打多達7000多個耳光,致使耳朵被打聾。而在李英蓮看來,對學生體罰是一種教育手段,雖然過分一點,但老師管學生也無可非議。他無論如何也不相信這會與犯法相提并論。然而,他錯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在學校保護一章中規定:“學校、幼兒園的教職員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李英蓮不得不為自己的無知去承擔法律責任。
中學生早戀現象,是老師和家長都十分頭疼的社會問題。對此,他們可謂驚恐不安,深惡痛絕,于是想盡一切辦法防患于未然。因此,吳明明的媽媽對明明宣布一條規定,凡是有給明明的信,必得先有大人過目。而且趁明明不在家時,父母還常偷翻看明明的抽屜和日記。14歲的明明惱火透了,以離家出走表示抗議。而初中生秦勉的班主任覺得秦勉學習不夠勤勉是因為和外校的一位女同學談戀愛造成的,班主任便私自截留和拆開秦勉的信,想找到根據來教育秦勉,結果,信中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班主任又自作主張將信毀掉。秦勉知道了這件事,深感自尊心受到極大侮辱,他要控告他的班主任。其實,吳明明的媽媽也好,秦勉的班主任也好,無論他們出于什么樣良好的動機,他們的行為都是為《未成年人保護法》所不容的:“對未成年人的信件,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隱匿、毀棄;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查院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進行檢查,或者對無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代為開拆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開拆。”
無須再舉更多的事例,正是這樣,法律的莊嚴與冷峻,使一些人們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事情變得那么嚴肅,那么鄭重,那么不講情面,那么令人想不到,人們不得不刮目相視這變化著的生活,不得不為自己的大腦平添些法律意識,用理性的眼光去重新審視自己的言行和生活角色。
當然,保護決不是“袒護”,更不是“放縱”。保護是一種教育,教育是十分有效的保護。這同樣應該被理解為《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魅力之所在。
一位記者在反復地閱讀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之后,這樣感慨道:“《保護法》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提供了一片沃土,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就好比四個保護神,在精心地培育和看管著一株株幼苗破土而出,沐浴著理性的光芒,這一片沃土必然成長起一個個健康茁壯而富有尊嚴的大寫的人。”
尊嚴,它屬于整個民族。
執法:任重而道遠
保護未成年人是一項崇高的事業。
我們從無法可依發展到今天有法可依,這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但是,我們又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法律只有不折不扣地執行,才能產生應有的效力。立法的目的在于執行,否則,法律便是一紙空文。法貴必行。
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現實生活中,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不是“立法如林,執法無人”,這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法律意識還很薄弱、法制建設還不夠健全的社會來說,絕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困難來自于方方面面。
請看:在北京市一所小學的家長會上,當老師向家長們問起未成年人是否享有公民權這樣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問題時,所有的家長竟異口同聲地回答:“沒有!”他們當中,既有普通工人,也有國家干部和學者。
還有這樣的事例:當自己的未成年女兒遭到強奸后,作父母的首先想到的不是報警和尋求法律保護,而是背著大出血的女兒找強奸犯去“私了”。
面對這樣的愚昧和法盲,至高無上的法律也不得不悲鳴:英雄無用武之地。
“有了保護法并不意味著未成年人就萬事大吉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語重心長地說:“立法、執法和監督是一個有機體,缺一個環節,都難以發揮應有的整體效益,而后兩者在我國目前的法制建設中,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認為:“《未成年人保護法》雖然已經頒布,但法律的一些規定還比較原則,需要制定相應的配套法規,逐步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體系。”
一位記者比喻得更形象:“《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制定和通過,無疑是獻給近4億孩子們的一只大蛋糕。然而,誰來切分呢?換言之,誰來執行又怎么執行此法呢?”
是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實施將任重而道遠。
全社會繼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