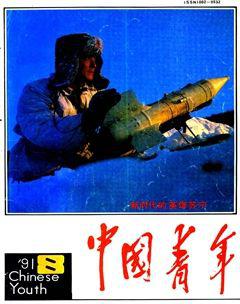歷史性的感慨與回答
莊建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鄧小平
有人說,高新技術是下個世紀的“上帝”。
歷史性的感慨與發問
20世紀70年代末期,當中國再次打開她緊閉的大門看世界的時候,面對的已不是她關閉國門時的那一個世界。
雖然,過去的時間在人類社會的進程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這是一寸光陰一寸金的瞬間。高新技術的發展,使世界在這一瞬之中發生了以往數百年不曾有過的進步和飛躍。在不長的時間里,電子技術及一些其它高新技術使美國加州一條30英里長、10英里寬的狹小得連名字也不曾有過的水果產地,一下子名噪全國乃至世界。這里每年新增4萬個就業機會,迅速躍居為美國九大制造業中心之一,這里生產的半導體集成線路、導彈和宇航設備、電子計算機分別占全美產量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八分之一,年銷售額達400億美元。眾目睽睽之下,這里的居民家庭購買力一下躍居全美305個都市地區之首。這里是袖珍計算器、影像游藝機、家用計算機、無線電話、激光技術、微處理機和數字顯示手表的誕生地。幾乎,電子工業方面的每一件新產品都是最先從這里推出。于是,在某種意義上說,這里成了電子工業以及整個高新技術產業的代名詞。這就是硅谷。
應當說,高新技術給予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機會是均等的。但是,當中國決定參與這競爭的時候,她已喪失了部分機會,使自己處在了不平等競爭的地位上。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聽到硅谷天方夜譚般的傳說是在80年代初期,硅谷已實實在在存在了10多年之后。它的身后,美國及世界許多地方已相繼出現了和它一樣神奇的“硅山”、“硅沙漠”、“硅草原”、“碳谷”、“生物工程谷”、“硅島”……
高新技術的蓬勃發展,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巨大飛躍,進而對世界的經濟、技術、社會、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開戰以前,美國派出幾十架飛機進行軟殺傷,使伊拉克雷達迷盲、通訊失靈、指揮中斷。由于智能炸彈、激光炸彈的出現,加上精確制導轟炸的精確度大大提高,轟炸伊總統府而使周圍的四星級旅館并不受損。海灣戰爭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科學技術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也使人們意識到,國際競爭已轉入以高技術為“制高點”的綜合國力的競賽。
一批批中國的領導者、專家、學者走出國門去看世界,在將中國與她生存的世界進行了比較之后,帶回了信息和思考。“二十一世紀將是高技術的世紀,誰掌握了先進的高技術,誰將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主動地位。”這成為一個民族的共識。
主管全國科技工作的宋健同志在參觀北京市80年代重大科技成果展時頗有感慨,他說,原始勞動、低檔的手工業勞動,人均產值不過千把元。傳統工業的人均產值也只不過一到二萬元,而高技術、新技術產業的人均產值是幾十萬元。中國人勤勞、勇敢,比外國人辛苦,但我們的人均勞動生產率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幾十分之一。因此,發展高新技術是歷史賦予我們的重任。中國如果不能實現用高新技術產業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標,就永遠也富不起來。
一位記者則這樣表述了自己的思想:“公元11、12世紀,開啟世界新技術之門的鑰匙握在中國人的手里。當中國人的造紙、印刷術使文化得以廣泛傳播時,歐洲人還在用羊皮抄寫《圣經》。當中國人用火藥制造出‘火炮時,歐洲的騎士們還像唐·吉訶德一樣揮舞著盾牌和長矛。當中國人已經很熟練地掌握鑄鐵冶煉技術時,馬可·波羅卻還在他的游記里向國人驚嘆:‘中國人在用一種不知叫什么東西的黑石頭燒飯和取暖……初始于13世紀的西歐近代科學,是從學習中國開始的,他們整整花了三四百年。英國人學習西歐花了200年;德國學習英國花了差不多70年;后來,美國學西歐不過四五十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戰敗國日本、西德躋身世界先進行列,只用了15年左右的時間。看來,學習的過程,也是總結經驗,創造奇跡和超越他人的過程。”最后,他發問:“今天,中國人是否能用更短的時間自立于世界高新技術發展潮流的潮頭?”這歷史性的發問,叩擊著每一個中國人的心。
用行動來回答
猶如在田徑場上角逐,起步晚了,但只要你還在奮進,就尚存趕上去奪魁的希望。如果你就此棄權,失敗無疑就屬于你。在研究了世界和自身之后,中國人用行動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于是,1986年3月,一個以在幾個最重要的高技術領域跟蹤國際先進水平,縮小同國外的差距,并力爭在可能的領域有所突破,將成果用于國民經濟建設的計劃——“863”計劃提出,1987年初進入實施。于是,1988年,旨在推動高新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實現商品化、產業化、國際化的“火炬計劃”,經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作為這一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建設,發展迅速,令人矚目。分布在全國的38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目前已擁有高新技術企業2500多家。1990年的總收入額達70多億元。位于中關村地區的北京高新技術產業試驗區,到1990年底,已有新技術企業930家,經認定的高新技術及其產品已達2027項,其中107項獲國際和國家級獎。一大批代表了我國高科技水平的產品相繼涌現:“三環”的釹鐵硼新材料,“科海”的激光打印機,“四通”的MS系列中外文字處理機,“京海”的VPS不間斷電源,“信通”的英文翻譯說話機,“華*”的替代氟里昂的新一代制冷劑,“長城機電”的無極交流調速電機……拳頭產品的出現,標志著試驗區內新技術產業已經開始形成規模。目前這里年創收超過500萬元的企業已達50家,出現了聯想、四通、科海等大型的全國性集團公司。決策者將新技術開發試驗區建成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生長點和輻射源的初衷,正在神州大地變為現實。
在中國的高新技術領城,中國人重新樹起自己的標高:1987年,我國和美國科學家各自獨立地發現了液氮溫區的氧化物超導材料,從此,一場國際范圍的超導材料研究、開發應用的激烈競爭揭開了帷幕。我國有關科研單位聯合攻關,3年來,在高溫超導研究的主要領域處于世界前列。在另一個領域,我國成功地完成了“亞洲一號”通訊衛星的發射,在世界航天商業市場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在電子對撞機、重離子加速器、激光照排技術、尿激酶、人工晶體制造技術、乙肝疫苗的商業化生產等相當一部分領域,中國獲得了世界水平的成功。
我們不必妄自菲薄!
有了人的集成才有財力、物力的集成
1989年,當從美國留學歸來的28歲的博士陳章良被北京大學破格晉升為教授的時候,一個中國當代史的記錄打破了。多少年了?中國何曾有過這樣年輕的教授。此舉不僅使被年齡的封蓋壓在最下層的青年知識分子看到了曙光,而且也給各級人才管理部門提供了思維的新支點。
國家科委副主任朱麗蘭不久前面對新、老兩代科學家講了這樣的話:“面對90年代高新技術的競爭,每個中國人都要有緊迫感。2000年誰上去?關鍵是人的集成。有了人的集成,才有財力、物力的集成。目前,年輕人中帥才不多,年輕人要有站出來挑大梁的氣派。當然,社會也要為中青年創造條件,使他們在高技術研究領域脫穎而出。”
這樣的認識或許比某一個事實意義更為深遠,更為重要。
當代青年是幸運的。改革開放使當代青年得到了幾代人不曾有過的機會。因為,在這個時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已不再只是一種政治象征意義的口號,它一步步地成為這個社會進步發展的迫切需要和現實。
在國家尚不包分配的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高技術企業中從事技、工、貿實際工作的青年人幾乎占了從業人員的80%。只有30多人的“海威電子開發部”,清一色的都是青年人。北京光通信公司,從總經理到項目經理的位置,也都讓年輕人占著。這個姍姍來遲的小企業,去年工程產值已達500萬,人均創產值30萬元,創利稅3.7萬元。
并不僅僅是在高新技術開發區,在整個高新技術領域,青年人正在形成自己威武的梯隊。
但是,在采訪中,我們也發現這樣一種現象:一些人較多地看到了在高新技術領域創業的青年人的成功,更多地關注了在開發區工作的青年人的收入,卻很少去探究一下他們的內心,關心一下他們在這一領域奮斗的艱辛。于是,說他們“出風頭”者有之,說他們為了“賺大錢而來”者亦有之。
這是不公平的。
在和他們交談之后,我們更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對祖國、對事業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他們中有的人舍棄了國家科研單位優越的條件,扔掉了鐵飯碗,走到開發區,興辦高技術企業;有的謝絕了發達國家的高薪聘請,回到祖國,尋找的是報效祖國的崗位,發揮自己才能的環境。
上海復旦大學青年教授楊玉良,婉謝了13萬馬克年薪的聘請,回到祖國,是因為他“丟不下生他養他的這塊土地,舍不下他從事的科研工作和輔導的學生”。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周其鳳向我們敞開的心扉,令人聽來感動。1978年,他出國留學前夕,和同批赴美的留學生一起受到當時的教育部長蔣南翔的接見。周其鳳向部長表示:“爭取學好了,向領導匯報。”蔣南翔同志糾正他:“不是向領導匯報,是向祖國、向人民匯報。”蔣部長的話,他一直牢牢記在心里。在麻省理工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系,他用兩年零七個月的時間完成了碩士、博士的學業,成為該系至今以最短時間完成此學業的人。隨后,他提前歸國。目前,他主持的液晶高分子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進展:他在世界上最先發現了重要的液晶高分子的分子量效應;他發明的新型液晶高分子引起國際高分子化學界的關注,已為法國兩位科學家證明。談到回國的動機,他坦白地說:“在國外,做得再多,是給別人做,而在這里,我做的每一點工作都是屬于自己的祖國的。”
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里,有許多年輕人是把檔案放在街道或人才交流中心,拿著求職書來謀職的。他們中有的是剛走出校門,有的則是已有多年工齡的國家干部、職工。他們來到這里,雖然每個人的想法千差萬別,但“用祖國和人民給予的知識,為發展祖國的高科技事業做點工作”,是他們共同的愿望。
應當說,他們需要理解,需要支持,需要關心。他們中的許多人,尚缺少最起碼的工作條件,有的壯志未酬,已疾病在身;有的因沒有一筆上機費,遂使滿腹抱負無法施展;有的尚被按資排輩的舊習重重地壓抑著……高科技領域的少壯派們,要真正成長起來,尚需要外部的條件和自身的鍛煉。
陳章良曾口出“狂言”:“斷層?只要把機會給年輕人,我就不相信我們接不了班!”此話道出了一代青年人的膽量與氣派。
“我同意陳章良的看法!”國家科委副主任朱麗蘭說,此話有遠見,這也是一代人的胸懷與期望。
可以相信,只要我們沖破自身思想上的束縛,解決人才斷層的辦法就會無窮盡地涌現;只要兩代人攜手并肩,更自覺地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世界高科技之林中中國之樹必將常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