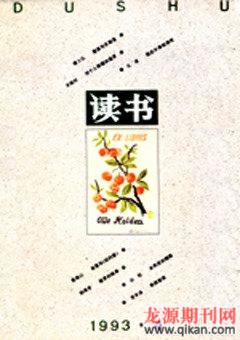對個人幸福的追求
李銀河
在西方,宗教規范是社會規范得以實行的工具,人們的行為只是間接地受到社會規范的約束(迪爾凱姆曾說,人們還給宗教的實際上是他們欠社會的債),而在中國,由于宗教不發達,社會是直接通過倫理道德來規范人們的行為的。中國人不敢作出某種行為(如離婚),往往并不是出于對法律的畏懼,也并不是由于受到宗教教條的約束,而是迫于社會上一種無形的壓力,這實際上就是社會的倫理道德的規范力量。寡婦守寡不愿再嫁往往不是由于法律禁止或她信仰的宗教的有形的約束,而是迫于倫理的無形壓力或受誘惑于貞節牌坊所標志的社會贊許。
由于倫理道德的規范力量十分強大,所以中國雖然沒有西方那樣的宗教,僅僅憑著倫理道德的力量也使社會達到了相當程度的整合。這種高度的社會整合是以對個人欲望的壓抑為條件的。媳婦壓抑自己為了婆婆,妻子壓抑自己為了丈夫,兒子壓抑自己為了父親,氏族中每一成員壓抑自己為了全族的利益,臣民壓抑自己為了君主。所以如此,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在西方,人們很早就在農耕之外謀求其他生路,或經商,或掠奪,等等,人的欲望因此往往能找到“正向”發展的渠道,而在中國,人們密集地居住在小片的可耕地上,它剛剛能夠養活所有的人,農耕以外的生路并不發達也不成功(成吉斯汗的遠征是向外發展,但嚴格地說,它不屬于漢民族或漢文化),所以人的欲望只能向“負向”發展——對個人欲望的壓抑:既然向外擴張是不成功的,只有大家繼續擁擠地生活在一起,于是彌合每個人個人欲望正向發展帶來的人際矛盾與沖突就顯得十分重要了。久而久之,這種強大的社會規范力量滲入了民族意識的深處,人們已經忘記這一規范的起因在于把個人欲望壓抑到一種使集體生活得以維持的程度,只是一味覺得對個人的壓抑是天經地義的。
近幾十年的道德思想教育與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有其吻合之處。這種教育的基調是提倡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反對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這當然無可厚非。但是,為此進行的一些批判活動,往往竭力壓抑個人欲望,不但要壓抑人“消費的欲望”,如想吃好、穿好、住好,以及各種形式的物質享受的欲望,而且壓抑人“創造的欲望”——至少想出名是一種創造的欲望,如果想得利不算創造的欲望的話。在這里,無論消費的欲望還是創造的欲望統統由于不是為了集體和他人的而是利己主義或個人主義的而受到壓抑。
五十年代,曾有過關于反面典型王鼎臣的討論。他是一個小職員,平常工作不錯,唯一的嗜好是讀點閑書。他之所以引起爭論是因為一個觀點: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一個人是僅僅為他人活著的,“一個人就不應該考慮他個人和他的家庭嗎?”王鼎臣問。他還對人的思想能夠被改造表示懷疑,因為“人的思想不象一張床或一張椅子可以隨意改變模樣。人的思想從腦子來,除非將人腦本身加以改造是不可能改造思想的”(大意)。他的說法未必都正確。但說他是“反面典型”,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
在五七——五八年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中,受到批判的思想范圍之廣令人驚詫,從名利思想、享樂主義到厭世思想、看破紅塵,幾乎無所不包。
在“文革”中,“思想改造”運動登峰造極,如“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等等,而且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幾乎每星期都有一位無私的英雄見報。歐陽海、麥賢得、劉英俊、李文忠、金訓華等等,長期思想教育改造運動的不懈耕耘終于結下了累累的果實。這些人的個人品質之高尚是無疑的(也有人說金訓華為在激流中攔住木頭而死不是很值得,木頭重要還是人重要?但他的行動無疑是符合道德思想教育的邏輯的:木頭雖然不如人重要,但是木頭如果是集體的,它就比個人的生命都重要了),但是如果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必須絕對地適用于每一個人,那么這一原則徹底實現后的社會情景應當是每個人消費水平的完全等同。而如果一社會中人的消費水平完全相等,人們將會喪失動力。提高消費水平一向是人類發展的動力。如果每個人通過自己勞動比別人多創造出來的消費品都被拿去給創造消費品較少的人以達到消費水平的一致,則前者多創造的動力就會越來越小,整個社會也將會保持在最懶惰最無能力的人所能創造出來的消費水平之上。改革前的中國就是這種“共同貧困”的生動圖解。
實際上,消費水平的完全相等自原始社會解體以來還從未有過,也沒有證據表明將來會出現這種局面。即使共產主義實現了,物質極大豐富了,每人都可以按需分配到私人汽車,甚至私人飛機,但是只要人類還在發明新的消費品,就不可能使每個人都同時得到,因為任何新型消費品都不可能一出世就生產得很多。如果一百個人平均可得一件,根據什么原則來分配呢?與其象有一個時期中國耐用消費品分配中所實行的隨機原則(抓鬮),還不如象現在這樣根據購買力分配。因為后者至少能刺激生產掙錢的積極性,前者什么積極性也刺激不了。
如果說在戰爭時期為個人利益還是為他人集體利益的行為是可以明確區分開來的,在和平時期二者卻往往很難區分開來。一個為掙錢養家的工人的行為與一個為他人集體而勞動的工人的行為在生產線上很難區別開來。后者可能會更努力一些,但是前者也有很努力很認真的。如果兩個人的行為完全一樣,只是其中一人與另一人的想法不同,那么這種想法除了對思想者本人有意義之外,對別人并沒有什么意義。
除了工作努力程度之外,思想可能造成的行為差異包括:(1)一個為他人為集體而生活的人可能將個人收入在滿足了自己最低生活標準之后的節余送給比自己生活水平低的人。這種作法之不可能也不應當普及于每一個人的原因前文已闡述過了;(2)使人自愿放棄較高的生活水平選擇較低的生活水平,如支援落后地區。這種作法比起其他一些國家用較優厚的待遇(利)或事業上的成功(名)吸引人去落后地區的作法略輸一籌。因為后一種作法畢竟可以肯定是人自己的選擇,前種作法往往使人為一時沖動付出多年的代價。如上山、下鄉、支邊等,多數人不但又千方百計回到生活水平較高的原居住地,而且往往還覺得受了騙。如果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的利益選擇的去向就不至于如此。
一個社會不論是希望人努力工作還是希望人去沒有人愿去的地方,如果能使人由于追求個人幸福而如此作,必定比使人由于壓抑個人幸福而如此作會收到更好的效果。正為此,許多個體戶的勞動積極性簡直比勞模一點不差,甚至更強一些。
一個合理的、有生氣的、有效率的社會是一個使每個人都能在對個人幸福的追求中找到生活歸宿而不僅僅在利他和對集體的奉獻中才能找到歸宿的社會。因為社會畢竟是由一個個的個人組成的,社會如果是以個人幸福為目的的,要求每個人都僅以利他為歸宿則每一個人的個人幸福都將是他人的歸宿而不是自己的歸宿。換言之,如果在一個社會中,我的生活目的是使你幸福,你的目的是使我幸福(其結果如果是兩個人都幸福),如此這般,則與每個人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其結果也是兩個人都幸福)沒有什么區別。既然如此何必要去顛倒呢?
如果有的人愿意僅僅以他人和集體的幸福為其生活目的,那也很好,甚至很高尚。本文絕不是要攻擊這些人,只是說要求所有的人都做到這一點,要是做不到(而不是反對)就強迫他去做,那是很荒唐的。當年轟動一時的“蛇口風波”中,蛇口青年與道德家們的爭論在我看來蓋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