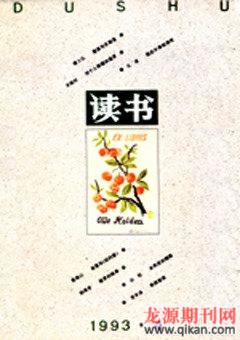“打”出一個“文化場”
齊煥文
早些年有所謂“名角兒靠捧”之說,也就是說,明星之“明”常要靠有聲望的名人、輿論的鼓吹,以及小報俗刊的哄抬。這也是要人為地構建起一個能消納此明星的“文化場”而激起“場效應”。日聞名人為書題序,多有扶掖嘆賞之意,也難免會有增其價值以廣招徠之圖。所以,我們在考察某一“文化品”的“文化價值”之先,就不能不考察其“文化場”的建構了。如果說,當今的假冒偽劣商品之所以猖獗一時,端賴其擁有一條綠燈暢行的流通渠道的話;那么,由于種種社會歷史原因而人為虛假構筑的“文化場”,則能滋生樹立起“偽文化品”的虛假的“文化價值”。其價值的增減,則視此“文化場”的興衰漲落而定。反過來說,某一具有真價值、高價值的“文化品”或稀世珍品,由于未被識別而不容于世,則只得藏諸深山、湮沒于煙塵,或待來世如此“文化場”成熟以后乃被確認、而或名震百世。這樣的例子,在中外歷史上俯拾即是。和氏之被刖雙足,仲尼之厄于陳蔡;一部《石頭記》之
作為特殊的“文化品”之“文化人”,即:含有一定質量的“文化因子”的所謂的知識分子或所謂的“人才”,其“價值”則不僅包含有由一定必要勞動量和供求關系所決定的商品價值,尤其包含有獨特的“文化價值”。此等“人”的“文化價值”,殊又不同于一部書、一件出土的文物的“物”的文化價值,而常又被人所自覺而視為自我之“人格價值”。此等“人格”之“文化價值”或由一定的“文化價值”所融鑄的“人格”,則非一般“物價”或商品價格所能標定,其價值之被確認與否,則常被其自我意識為“尊卑,榮辱”。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理中,又常有“知遇”或“不遇”之論。“遇”,則肝腦涂地;“不遇”,則桀驁不馴或退隱山林。然而,像范仲淹先生所說的那種“居廟堂之高”和“處江湖之遠”都一樣地憂國憂民,則是中國知識分子迂腐的光榮傳統。由于“人”是能動的,是活的,當其“人格價值”不被確認時,他就必須會流走,由楚而秦、而鄭、而齊,其所尋覓的無非是一個能適應其存在并確認其“價值”的“文化場”。有所謂“墻外開花墻內香”之說,原也是要到“墻外”去找得一個“文化場”來確認其價值,而“墻內”的“文化場”則相形見絀而已。
更為復雜的還是,所謂的“文化價值”雖固有其內在恒常的方面,其浮面則常隨時代歷史的遷移而變動不居;同時,所謂的“文化場”也不是什么絕對孤立的系統,它必然地要受整個社會大文化的運動機制所規約。因之,一定的“文化價值”,則又取決于一時代社會總體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觀。當社會處于急劇震蕩變動之時,其“價值”觀難免顛倒混亂,此時一定的“文化價值”令人懷疑,也是情理中事。即若“文化場”本身,也還有一個極為復雜的構成,其社會組織的健全合理與否,也必然影響到其“文化場”的構成健全與否。當代文化所普遍面對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區分這“文化價值”與“商品價值”的問題。當我們的“文化場”尚未健全成熟的時候,硬要將一切“文化品”都置入“市場”而任憑“市場調節”,則“文化”就只有隨著流俗跑了。目前電影、電視乃至出版業所面對的“不知所云”的局面,概由于在“文化價值”與“商品價值”之間徘徊而無所適從。而“文化”的最基礎的層面則是教育。先驅們早就見出“教育”的重要,當年魯迅之所以棄醫就文,就在于他痛識到我民族之自救乃在于拔除愚昧。
當然,“文化”并不是什么世間可有可無的、全然消極被動的東西。只要人類存在,“文化”總要作為人類自我的表達,和對自我與世間的關注而站出來說話。“文化”也要就自身的狀況加以反思和探問。最終,一時代社會總體的“價值”觀,也還要靠“文化”的建設與調節。所謂“仁者愛人”,所謂“唯我”還是“利他”,以及所謂“人、物”關系,“人、人”關系,乃至“人”與“天”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世代都懸在人們的腦門心上。人們對“天意”和自我“命運”的敬畏和猜疑,也終歸要詢問個究竟。高的則有哲學、宗教以及藝術來解說和表述;低的則在街談巷尾來議論和到馬路邊上去求卜。
一個開明進步的社會或國家,當其傾全力來推進經濟解決民生問題的時候,就不能不顧及“文化”,就不能不花大氣力來樹立其社會總體的理性的“價值”觀。所以,我們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也還要發展“精神文明”。而確立合理的“文化價值”體系和構筑健全的“文化場”就是關鍵。如同發展經濟,要有合理的商品價格系統和健全成熟的“商品市場”一樣。“商品價值”聯系著“商品市場”;“文化價值”聯系著“文化場”。當“文化品”進入到供求關系的時候,事實上是受著這兩個“場”的同時制約的,不知社會學家們是否注意到這一點。近日讀費孝通先生《孔林片思》一文(見《讀書》今年第九期),意大思深,堪為博通之論,然筆者不揣卑陋也還有所進言。竊以為:一社會的發展,不但要關注于自然的、物質化的“生態”和精神化的“心態”,也還要關注于社會化、人文化的“文化態”。當世不但要呼喚和培育“孔子”式的人物的產生,更要依靠理性科學的力量,依靠開明的政治,調動全社會組織來培育合理的“文化價值”系統和建構相應的“文化場”。(它涉及“文化”本體的發育和內外部聯系;“文化”的物質載體和機構的設置;出版和媒體的傳播;評賞鑒識和理論、評論;以及觀者、讀者群的培養發展等等。)當然,政治對于“文化”的褒揚和貶抑的作用則尤為顯著,其實政治又何嘗不是一種文化的體現而受到文化的強大的制約和影響。“社會學”在首先著眼于社會經濟運動和民生狀態的同時,是否還應該關注“社會文化”的布局和構筑。我想,“文化社會學”則理當是“社會學”的一大支系。孔子的偉大建樹即在于他通過教育發展了我國“文化”,確立了系統的“仁禮”價值概念,其所以得到倡揚實在于漢、唐“文化場”的隆推,這怕是我們應該深以為鑒的史實。
我想,知識分子們也完全不必為其“市場價格”之低而喪氣,當其“文化價值”尚未得到應有的確認之時,任憑“價格系統”如何調節,其價值也是不會得到相應的體現的。知識分子們不應該在低首于“市場價格”之時,而忘卻了如何不斷增進自身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