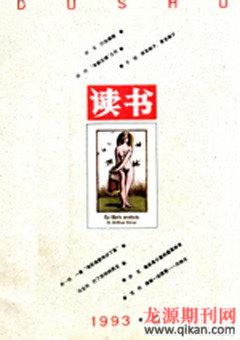“藏書家的心事”
董橋說:“把書當工具的人,家里雖有幾架子書,卻不算‘藏書家。”這話說得好。讀書的人未必是愛書人。讀書是一種境界,愛書又是另一般境界,正像結婚的是多數人,但欲求永遠保存一份初戀般的愛情,卻是少數人的奢侈了。舊時中國的讀書人中,不乏愛書人,即被稱作藏書家的一類。于是便有鐫刻印章,鈐于所愛之上的一番風雅。諸如某某藏書,某某經眼,某某讀過,皆屬常見;亦有唯恐后人不知不識,而不憚縷述的,如“楊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號冬樵行二”之類;又有諄諄切切留言子孫的,如“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等等,此以一個癡字,便可道盡其中情懷。卻更有鐫了愛妾的名號,鈐于珍愛的書冊之上,以志佳人才子的一回人生艷遇,如平湖陸子章,歸安嚴元照,都是。倒真是“弄得愛書和愛女人都混起來了”。不過,比起西人的藏書票,這“偷運”愛情的方式,未免過于含蓄,仍是董橋說——西方仕女圖藏書票上畫的女人,漂亮不必說,大半還帶幾分媚蕩或者幽怨的神情,仕女身邊偶有幾本書,流露出藏書家心里要的是什么。這當然又是后花園幽會的心態在作祟!倫敦舊書商威爾遜的藏書票藏品又多又精,自己還印制好幾款仕女圖藏書票,有一次問他為什么一款又一款盡是仕女圖?他低聲反問:“你不覺得她們迷人嗎?”——不待他人作“誅心之論”,藏書家早和盤托出心事。“愛”之為“情”,必也如斯乎?
今年《讀書》第一期封面的藏書票,選用了波蘭T.Szumarski的作品(雕刻銅版),封底則為日本的關根壽雄(套色木刻版);第二期的兩枚,作者一為日本大內香峰(封面;木刻版,木口木刻套色版),一為捷克K.Ondreicka(線畫凸版);第三期則是“美而艷”的“西方美人”(封面為日本小林鈍所作,封底為日本巖佐直所作,均為蝕刻、干刻版)——方寸之地,“愛”與“情”存焉。不過封面上的這一位,專藏eroticis,不免“左道”。但對此也不必多加非議,因其只是自娛,本與他人無涉。就此圖看來,也很平常,且不乏幽默,并無eroticis之可言。何況此間的“百爾所思”,又何煩“鄭箋”,若得愛書人與讀書人俱“以同懷視之”,不也就是藏書票的無限意趣了么?
讀書短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