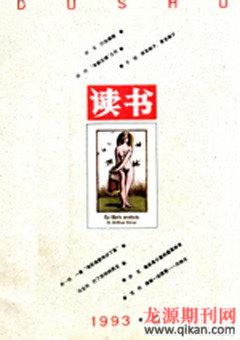推薦一位西圣——貝特生
雪 熱
前幾日在德國讀到費孝通先生《孔林片思》一文,深為老先生憂民憂國憂世界的情思而感動。正巧在書堆里碰上一位有些圣賢之氣的人物,推薦來作為對費老呼喚的回應。此人是美國人,不知妥否?
格里高利·貝特生(GregoryBateson)是個雜家,研究過文化人類學、生物學、生態學、心理學及精神病學,均有建樹。在這專家太多、雜家太少的時代,奠定他泰斗地位的,正是其在這些具體學科之上大手筆的綜合。照“總體多于部分之和”的說法,這一綜合使其成就蔭及各學術領域,成為超時代、跨文化的思想家。但也許他的思想離我們太遠,在中國的知名度遠不如其前妻米德(Mead,有多種文化人類學著作問世)。有一本研究生用《自然辯證法》教材在“三論”章節中提過他對信息下的定義——信息是造成差異的差異。然多數同學堅信哲學虛玄,此話怎樣講也是不了了之。在重教導不重教育,重技術不重科學,重科學不重文化的氛圍里,大概也只能如此。
貝特生之不平常,可用心理學家羅洛·梅的幾句話來概括:“貝特生讓我想起那些古典哲學家。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個由古典的廣闊與非凡的深刻結合成的例子。他站在由美國科學闡明的真理與源自于東方智慧的真理之間的中點上。”如果將美國科學喻為征服自然的利刃,將東方文化比做規范人生的經緯,那么與此相應的當代人類“生態”與“心態”(費老提法)兩大問題都是被他琢磨過的。當然,他站的那個中點是否就是人類危機的平衡點,還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說來有趣,他的思想正好有一部分關涉到何以有仁者智者之分的問題,也即認識論
貝特生是“不正統”的,“古典”之譽有些勉強。最重要的著作有兩本:《邁向精神的生態學》(Steps to theEco1ogy of Mind,一九七二)和《精神與自然》(Mind and Nature,一九七九)。前者是幾十年間論文集,書名中的“精神生態”似與“心態”有契合之處;后者則是晚年的系統沉思。兩書內涵極豐富,涉及哲學、宗教、社會、人文、行為及自然科學。二書的重點在于指出,我們認識到的世界并非如我們以為的那樣真實;它實際上是符合我們信念及認識論前提的社會構成物。作為科學家,他沒有幼稚到要否定那個外在的,供我們大腦“模寫”(列寧說法)的世界。(插一句:讀他的書若不心平氣和,就會給他的“唯心主義”論點增加依據。不信試試看。)以此為出發點,他的著眼點放在了人類關系、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上。天真的唯我論和天真的現實主義都是他所反對的。或者準確一點說,他反對的是從笛卡爾、牛頓以降主宰了科學思維的二元論。唯我論和現實主義作為被構成的價值體系,本身是無可非議的。但天真的唯我論或現實主義所遵循的二元論是只看見矛盾的一個方面的認識論。它總是“構成”半幅世界:非黑即白。好—壞、穩—亂、公—私、理論—實踐、美學—實用主義等等,都是只取其一,認定為真的、正確的或有用的。且不說這種半瓶醋的認識因為忽略了另一半世界會有什么害處,光是爭奪這一邊與那一邊的定義權就常常變成權力斗爭。“什么對什么錯”遠不如“誰對誰錯”重要。困擾人類的重大問題常常是在這兩個層次上發生的——內容和關系:對自然的掠奪性開發基于對人類能力的自大妄想(內容)和對大自然實施報復(關系)的麻木不仁;強權政治以“別人不對”為理論根據(內容)而以武力作后盾(關系)。回到中國人這里來,“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馴服與殘忍周期性的表達,也可視為“非此即彼”邏輯占了“既……又……”邏輯的上風:終究還是人而不是物的問題。
貝特生試圖用控制論認識論來克服二元論缺陷。簡而言之,控制論是一種研究模式、關系和組織的一般科學。要接受它,就得進入一個境地,完全不同地對世界進行描述,里里外外改變思想、行為方式。認識論的改變大概是在人類所能發生的最高層次因而也是最難的變化,它意味著要轉換體驗世界的方式。(一位印第安巫師稱此為“中止內在對話”。頗似修禪、練氣功)新的體驗世界的方式是空前寬容、平和、色彩絢麗的,以致我得再次準確一點地說,貝特生甚至并不反對二元論,只是對其不滿意而已。因為他超越了二元論與控制論之間的二分法,在更高層次上觀照二者間互補性、交互性、循環性的辯證關系。
從描述具體的現象、形成理論,到探討指導產生理論的認識論方法,再到研究認識論之間的辯證關系,正是其貫徹于各學科研究中的“過程(內容)與形式的辯證法”。他總是站在比被觀察對象高一級的認識層次上,所以對人類的觀察便有了從行為到背景,從小背景再到大背景的提升與擴展。每一層次里他都“構造”一套概念,動態地描述這一層次里的模式與組織,但不把“營養學理論、烹調處方、菜譜與菜”相混淆。相比之下,不少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研究卻顯得資料詳實而無可升華,頂多是為幾個婦孺皆知的抽象概念在一個層次里完成一次“自我參照”,如同下例:有人問,何以某藥能催人入眠。答曰:“因為它是一種安眠藥。”這是貝特生所謂的“安眠藥原則”:一種對于對象的描述,被抽象了一次,進行了再包裝(命名),然后這個抽象概念——從被觀察對象而來——被當成對象的原因。安眠藥本身有睡眠的藥理作用,非藥理學家的貝特生卻更重視,此類形式的對安眠藥作用的解釋是否也有利于睡眠。我們的教育、學術中,頗多這類令人心安理得的解釋,疑是圣人太多的緣故。教條及教條發明者的名字成了解釋研究對象的原因;而經驗主義者不相信別人發明的抽象概念,而只以自己在抽象過程中形成的概念解釋對象,使這些概念成為對象的原因。就菜譜被當作菜這一點看,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竟是同胞兄弟。貝特生從內容和形式兩個層次看待對象和自己,體現了“控制論的控制論”(亦稱第二控制論)的精神:既把握被觀察對象,又把握觀察者的觀察即認識論基礎。他認為,如果滿足于一種解釋,我們便沒有了好奇心,向深度廣度的理性擴展因此而窒息。如果從捍衛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你死我活斗爭中抽出身來,超然于二者之上,在若干個認識論層次上多來幾個“反饋回合”,放棄一條道走到黑的直線性因果思維模式,豈不就是百花齊放?反饋是控制論的最核心概念,世界因為反饋、循環而普遍聯系著。
我們需要這位“圣賢”嗎?大凡圣賢,都不是修修補補之才(或材?),應該有新意,引起些積極而深刻的變化。如果貝特生引起的變化主要是認識論的,這種變化關乎痛癢嗎?
欲回答此問題,僅僅理解了前面提及的認識論與人類困境的關系還不夠,這只涉及必要性的問題。重要的還有可能性的問題。我們得搞清楚目前主導的認識論在不同人群、不同文化里的空間分布,還得搞清楚認識論的歷史走向。有人認為,貝特生的工作之所以意義重大,乃是因為他是一個站在“后現代化科學”角度上的預言家。他口里出來的預言,對于正在追求現代化的“前現代化”民族是否適用,就是有考究的了。預言家與空想家是有區別的。空想家提供畫餅,提供符合“安眠藥原則”的簡單解釋,讓人覺得受用,效果是阻斷創造性想象,抑制探究行為。貝特生這樣的預言家則提供信息——造成差異的差異。他沒有現成答案,只是提示世界的多樣性(既白又黑,余類推),也即呈現給我們差異,然后這種差異連同這種呈現本身(不教導,不灌輸),在我們頭腦中引起形式和內容的雙重差異,于是便讓我們心緒不寧,幸運的話就會在比較、推敲、探究中產生新的思想、新的行為方式。這樣一種預言方式,可以說是既仁又智的。既有對禮崩樂壞的深切關注,又有對人類自我組織、自我矯正的信心;所用的方式是富于啟迪、有生產性的。就這一點來看,他與我們之間“后現代”與“前現代”的巨大差異,恰恰在我們造成了大差異,也即給了“大信息”。按照他的注重模式、關系的“精神生態學”觀點,人與自然相通,低等動物與高等動物相通。既然如此,更何況“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兩種文化?
貝特生已于一九八○年去世。但他的思想仍回聲不絕,四處擴散。最具代表性的實用例子是在歐美日漸興盛的“家庭治療”。心理治療家放棄了說教者、判官及社會控制者的角色,超然于誰是誰非之二元分離,著力于誘導家庭系統認識論的改變,以此處理個人、家庭的危機與病態,頗有成效。另有一位名叫卡普拉(Capra)的物理學家,亦是深得其道,十數年來頻頻奔走于歐美之間,為實現所謂“范式的轉變”四處吶喊。他的著作(如《物理學之道》,譯作《東方神秘主義與現代物理學》;《轉變時刻》,《新思維》等)為傳播、發展貝特生思想起到了不小作用。一九九一年在德國的一次大會上他應邀作報告,趨者甚眾。內容是痛陳唯理性主義、歐美中心主義危害,推崇不尚爭的混沌東方智慧。強調尊卑有序、社會控制的孔孟之道是不受歡迎的,老莊、禪宗卻倍受稱道。作為聽者,我自喜之余又不禁迷惑:“這真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啊!”可不是嗎,沒有秩序、沒有穩定,只有阿Q,只有清談騷客,哪來雞蛋、導彈?中國人不又要被您的同胞們生吞了么?
看來范式的改變不容易。在這個世界上,如果仁義道德只管君子,不束小人,真不如沒有圣人的好,大家回到相忘于仁義的蠻荒時代去。但這種道家式的“減法”是不可能的。得考慮“加法”:仁義道德十法制十民主十科學理性十……。但如前所述,加一把油或加一把勁常常把事情弄得更糟,有如軍備競賽。兩年來生活于洋人中間,常覺這道運算老是出錯,民主法制自由仍有缺憾。不過感覺最深的還是,二元論思維占盡天下,使西人常說合邏輯之胡話,編織嚴密之謬誤與偏見,做理直氣壯之壞事。貝特生所以吸引我,就是因為他的思想似更接近問題本質,提示了一種超越東西方文化各自缺陷的可能性,是一種“乘法”——激發人們構筑一個既有個人自律、自由、創造,又有社會、生態整合性的世界。這樣的世界需要有許多的新孔子。但要培養他們,這個社會應是寬容、和平、對世界及人本身充滿好奇心的。這也正是要求于這些構成新世界的新圣人的。他們不應該是褊狹、強暴、對世界對人充滿占有欲的。孔子的教誨被人發揚光大以滅人欲,尤其是新圣們要避免的。這是個悖論——控制論恰好不是用來控制擺布人的。
謹以貝特生的一段話作為結尾:
我們這些社會科學家應該好好收斂一下我們控制這個了解得十分不全面的世界的欲望;我們的研究可以用一種更為古老的,但今天卻較少被尊重的動機來激勵:一種對于世界的好奇。在那個世界里,我們只是其成分。對這份工作的報答,不是權力而是美。
寫完此話,我擔心他一時做不了圣人。大概他也從未想過要當圣人。封他個“弼馬溫”足矣。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寫于冬天的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