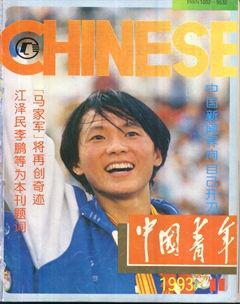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
□中學生和家長擰了一個扣
□家長說:孩子,我這是為你好!
□中學生自己怎樣說呢?
我在一個偶然的場合聽到一位中學生如此這般地向成人反駁,我有些疑惑,為什么孩子們把他們和父母共同的世界分為你們的和我們的?
初夏的一個傍晚,我找到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青年教師靳忠良,想和他共同探討這件事,也想寫一篇通訊。然而,當我讀完他借給我的許多信和一紙袋“海淀區小作家協會”學生的隨感后,我改變了主意:不如把學生們的話原原本本擺出來,也許,原汁原味更耐人尋味。
——編者
晚上,要開家長會,下午,學生們就蔫兒了,原來是怕爹媽會后“加壓”。我不解,靳老師說,你讀讀那些信就明白了,我摘出如下幾段:
●我媽媽總是說她有多愛我,比如因為要撫養我她不能安心工作等等。她總是說自己如何為我犧牲一切,卻不知我也為他們犧牲了很多。我已上了中學,有了自己的想法,但在父母面前卻要裝出乖樣子,不敢暴露任何“不妥的”思想,連看國際新聞也不敢“挺狂的”說三道四,不然爸媽就會輪番“作報告”或者訓斥,“小孩子懂什么!”,每到這時,我都不再吭氣。我沒有一個真正理解我的朋友,心愛的日記早已不屬于我個人。為了對付爸媽。我準備了兩個日記本,一本專寫豪言壯語,是給他們看的,另一本才是我的心聲。
——李素15歲
●你們大人不是每天都看天氣預報嗎?我也看,但不是電視,而是爸爸媽媽的臉。他們一下班回家,我就得琢磨他們,臉色好,說明心情好,是晴天,臉色不好,說明心情不好,是陰天;天晴的時候,我就提那些特想做、又很難被家長答應的事,準行,例如玩游戲機什么的;天陰的時候,干脆乖乖地躲在屋里寫作業,一聲別響,如果那時提要求,等于自投羅網,自討沒趣兒。不過,我的天氣預報經常不準——跟電視一樣。
——姚南13歲
●我在家里不起任何作用,放學回家吃飯,吃完飯到自己房子里做作業,然后洗漱,上床睡覺。起床靠鬧鐘,很少和爸媽交流,好像我們隔得很遠,沒有交流的習慣。我作過一個統計,如果我一天想和爸爸說300句話,只能挑100句說,如果我把這100句都說了,爸爸大約只能回答3句,如果其中有一句是認真回答的,我就感到很萬幸了。
——王錚13歲
●我初三了,馬上就要參加中考,可我現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睡覺,自從本學期一開學,我就成了籠中鳥。父母都是教師,那些亂七八糟的練習題、試卷自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這下可苦了我。
“小菊還不快做?都1點了。”我心想:“天哪!媽媽現在還知道幾點嗎?她就不心疼我?”,我嘆口氣,勉強挺直疲倦的身體,耳邊不斷地傳來媽媽的聲音,“這都是為你好”“上個好學校一輩子都有好處”之類,聽得我煩煩膩膩的。我重重地甩了下頭,像是要把所有的睡意、疲倦和對父母的不滿都甩掉。我費力地睜了睜眼,費力地寫著,但筆不聽我的,胳膊不聽我的,腿也跟我找別扭,腦子里一個勁地說,睡覺,睡覺!媽媽好像正在背后嚴厲地看著我,而且還說著什么,這時我只希望發生兩件事,要么地震,要么停電,只有這樣,我才能踏實,媽媽也踏實了。
——王秀菊16歲
●今天,媽媽打了我,好狠啊!我就坐著不動,張著大嘴哇哇哭,淚如雨下。媽媽太不講理,不允許說她有錯,否則就是不孝。父母太可憐,他們愛孩子,卻不懂得怎么愛。有時他們打我,我真想死可又缺乏勇氣,現在我才明白,自殺并不是脆弱,死也得要勇氣,像我這樣,想死不敢死的人才是可悲!
——吳翠16歲
●父母對孩子的管束我可以理解,但他們太過分了!我越來越討厭他們。比如,我喜歡聽歌,也喜歡某個明星,父母就使勁在我面前糟改他們,什么“奶油味”之類,企圖把他們從我心里轟出去;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們發現我有兩盤新加坡男歌星的磁帶,發現我在同學錄上“最想去的國家”一欄填的是新加坡,竟罵我是“賤骨頭”,我又生氣,又委屈,一個人跑到公園里哭了一場。一想起這些,我就難過極了。
——江曉洋13歲
孩子們所抱怨的,恰恰是家長們所夢想的。孩子們所苦腦的,不是物質的匱乏,而是精神的控制。
每個家長都想在孩子身上實現自己的夢想,但他們卻忽略了孩子自己的夢想;每個家長都認為自己有責任向孩子灌輸各種社會的理想和道德,有責任把孩子培養成自己所希望的人,但他們卻忽略了,曾經懷著崇敬接受過十幾年教育的孩子,需要一個自我消化的過程,他們已經到了人生這樣一個階段——是孩子又不是孩子,是大人又不是大人,他們在印證小時候父母向自己傳授的一切的同時,竭力想走一條自己的路。這是不可抵御的誘惑,其愿望越強烈,對父母精神控制的反抗也越強烈。我開始懷疑,在孩子們的抱怨中,除了青春期特有的生理心理沖突外,是否也包含了父母們愚蠢的責任心?
——編者
靳老師對我說,中學生感受家長的愛和體貼就像感受對立情緒一樣強烈。
●我知道爸媽很愛我,尤其是媽媽,舉一個例子,平時我最愛吃雞腿,媽媽總給我做來吃。可我發現,每次媽媽只吃我剩下的雞皮。我問媽媽為什么,她說,她就愛吃雞皮。暑期,我在一家餐館打工,我用自己第一次掙的錢給媽媽買了一大兜雞皮,媽媽見到后,迷惑地問:這是干什麼?我興沖沖地對她說:“你不是愛吃雞皮嗎?這是我孝敬你的。”媽媽看了看我,一句話也沒說,然后趴在桌上哭了。現在我可能還不能理解媽媽當時的感情,但我懂得,媽媽為我付出的是她自己的一切。
——呂靜14歲
●我從小就在愛的包圍下長大,媽媽、爸爸、姥姥、姥爺都寵愛我,我要什么,他們就給我買什么。每天看電視我都要看廣告,從那里尋找我想要的東西,然后告訴大人,他們就會想盡辦法給我買來。有時爸爸想教育我,我就擺擺手,“行了,別說了,我煩著吶!”爸爸老說,他在我心里的地位不如電視高,其實,他說錯了,我挺愛爸爸,只是不喜歡聽他嘮叨。
——郭宏祥15歲
●我在小學,到底上過多少課外活動班,已經數不清了,我一說學煩了,爸媽就給我換一個,除了手風琴,我一門也沒學出名堂來。記憶最深的,倒是爸爸媽媽為我受了很多罪,搞得家不像家,人不像人,他們每天接我送我時就像接力賽跑,看到他們疲勞的樣子,我就想:當父母太累了,我要是長大了,一定不要孩子,不受這種罪。
——曲強16歲
●我們家有很多人,他們對我照顧得太周到了,周到得我直想離開他們,一個人好好呆一天。那天,我終于被同意一個人呆在家里。臨出門時家人囑咐了很多話,關門啦、關燈啦、帶鑰匙啦……好羅嗦,我又不是小孩子,連這些都不懂?
送走家人,我躺在沙發上邊聽歌,邊看閑書,邊吃泡泡糖,美極了!后來不知什么時候竟睡著了,醒來后已經1點多了,我坐起來重重地打了幾個噴涕,鼻涕一個勁地流,原來我忘記蓋被了。“唉,要是奶奶在多好,我決不會感冒。”因為每天睡覺都是她給我蓋被子。
起來后,我覺得有點餓,打開冰箱一看,肉,蔬菜應有盡有,我一會想吃這,一會想吃那,可一樣都不會做,只好泡方便面了。“唉,要是媽媽在家多好,我想吃什么她就給我做什么。”天晚了,我做完了作業,突然覺得害怕起來,我把所有的燈都打開,電視也打開,把所有的門和窗子又鎖了一遍,可還是不踏實,坐在床上望著鐘表發呆。我想,如果現在家里人都回來了,我一定撲上去擁抱他們。老師,我想告訴你,這是我最自由的一天,也是最想念家人的一天,還是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是個笨蛋的一天。
——董國宇14歲
在父母和孩子之間,愛與被愛所產生的效果并非全是積極的。有時愛也能導至隔膜,發生誤解。這誤解往往會使雙方的感情因為愛而沉重起來。記得一位歷史學家說過,保障給人心理的壓力,常常大于人在惡劣環境中所能承受的壓力。我們是否該共同作一種努力,在愛中感受美好而不是枷鎖。
——編者
靳老師告訴我,現在孩子們正試著在“溺愛”和“緊張的生活”中尋找縫隙,尋找一個適當的位置。
●我是一顆星,是家庭的中心;我是一只小鳥,給家庭帶來歡樂;同時我又是一顆炸彈,每每爆炸都引起暴風驟雨般的爭吵。我只希望有一片自己的天地。
——馮津京13歲
●我在家是皇帝,但不是真皇帝,爸爸媽媽高興的時候,我的確像皇帝,受到百般照顧;可爸爸媽媽不高興時,皇帝就“駕崩”了,到那個時候我就是家里最慘的,像馬踏草坪,被踩得一蹋糊涂。所以我要利用當皇帝的時候,多多享受。
——南錚13歲
●在家里,我的位置是不固定的。有時爸媽很關心我,有時就把我撇在一邊,每到這時,我都挺知趣的,就躲了。您問如果躲不了怎么辦?別忘了,我們的門上有插銷呀!
——佟慶13歲
●如果說我的父母是套在一起的兩個圓圈,我就是中間交叉的那部分,有時我是個圓的,是個中心,有時我就被擠成橢圓,還有時被他們擠得殘缺不全,總之,我這個圓經常隨著代表父母的兩個大圓的變化而變化。
——姚南13歲
●我是家庭幸福的粘合劑,爸媽吵架,我讓他們別吵了,他們就不吵了。
——陳興13歲
●我能用王朔小說的書名形容我和家庭的關系:我在家里是《天使與魔鬼》又加《頑主》。因為我的父母都很正經,所以我就顯得挺玩世不恭的,父母說我有時像天使,有時像魔鬼,十足一個“頑主”。
我爸媽對我《愛你沒商量》。
當我和爸爸辯論,爸說不過我時,就說《我是你爸爸》。當爸媽強迫我同意他們的意見時,我總愛說《各抒己見》。當我鬧著要干什么事時,媽就說我《一點正經沒有》。我對家庭最美好的回憶是《浮出海面》、《長長的魚線》、《大喘氣》。我和父母一起去海邊玩,一起釣魚,一起聊天,一邊侃,一邊開玩笑,先說半句,來個大喘氣,再說后半句開心極了。
——趙雷13歲
●您問我為什么不試著把心里話告訴家長,向他們那邊邁一步。我試過,但又退回去了。我的心里話成了他們教育的靶子。所以不如把那些話放在心里,聽聽流行樂,那些歌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趙雷13歲
●您問我怎樣看待和家長的沖突、矛盾。這還用問?沒啥了不起,不吵架怎么能叫家?上班、上學都得繃住一股勁,回家當然得輕松自然,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吵就吵,我怕的是回家也跟上班、上學一樣緊張。
——姚南13歲
●有時我挺想叫父母吵架,只要別太傷感情,這樣一來我在家里的位置就顯出來了,給他們勸架的時候,我感到自己不再是孩子,而是大人。
——劉溢13歲
……
孩子們想到的,遠遠超過了家長給他們指出的,甚或是家長為他們付出的。在生活的觀念上,孩子們已經改革開放了,可家長呢?
如果說,80年代,關于“小皇帝”的警鐘打破了家長對孩子過分的物質保障,那么今天是否還要進一步打破精神的保障?如果說90年代,人們在觀念上已經認可了孩子作為個人的權利和尊嚴,那么為什么輪到行動的時候卻又不自覺地回到舊有的范式中呢?
有位學生問得好:“爸爸老說他們是新中國的建設者,好像我們就是享受者,難道我們就不是建設者嗎?”
記得有位詩人對一位懷抱孩子的婦女說:
你們的孩子不是你們的,
他們是由生活召喚而來的,生活的兒女。
他們雖然經過你們而出世,但不是你們的。
你們可以給他們愛,卻不能給他們思想。
你們可以照顧他們的身體,
卻不能照顧他們的靈魂。
他們的靈魂住在明天的房子里,
你們可以盡量同他們一樣,
但不要讓他們同你一樣。
因為生活不能倒退,
也不能同昨天停留在一起。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