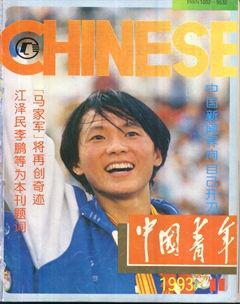修正上帝的筆誤
萬潤龍等
北京消息:1993年2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wù)院秘書長羅干會見了克萊特夫婦,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授予他們最高貴的禮物——“友誼獎”。
我們都自稱為正常人。但是,如果我們不能為精神病患者提供一個正常的生活氛圍,那么,我們又正常在什么地方呢?
——海因茨·克萊特
圣誕節(jié),武漢市江岸區(qū)解放南路356號二樓,一個近百平方米的娛樂室,60多名男女穿著節(jié)日的服裝圍成一個大圓圈,收錄機(jī)播放著貝多芬的《命運(yùn)交響曲》。屋頂斜拉著的彩花紙球,以及四周漂亮的裝飾,讓人感到節(jié)日的歡樂。
吹蠟燭,說故事,演小品……每個人都那樣開心,那樣生氣勃勃。會唱的,獻(xiàn)上一曲《讓世界充滿愛》;不會唱的,請大家猜一個謎;既不會唱,又羞于說的,便沿著圈子給大家鞠上幾個躬。掌聲,笑聲,贊嘆聲,更有一些控制不住自己情緒的,眼淚順著雙頰淌了下來。
我坐不住了。我實在不敢相信,在這些圣誕節(jié)聯(lián)歡的參與者中,竟會有16位精神病患者。我離開擊鼓傳花的圈子,來到了海因茨·克萊特先生的身旁,他身旁正好有一個空位子,那是他的夫人的座位,此時,他的夫人羅莎·克萊特正舉著照相機(jī),頻頻地攝下她的病人那歡欣愉悅的鏡頭……
克萊特夫婦的中國之行是一本書,一本充滿傳奇色彩而又給人以無數(shù)啟迪的書。
7年前,剛退休不久的克萊特先生與他的夫人羅莎告別了自己的4個女兒,踏上了中國這塊向世界開放不久的土地。他們應(yīng)聘擔(dān)任了武漢水運(yùn)學(xué)院的外語教授。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那么友好,克萊特夫婦領(lǐng)略了中華大地這塊古老國土的風(fēng)情文化,漸漸地對這里的一切產(chǎn)生了感情。上課的任務(wù)并不重,閑暇時,這對德國夫婦時常到街上散散步。有一天,他倆被眼前的一個情景拉住了腳步:大街上,一個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姑娘不停地向路人舞手蹈足,她的身邊已經(jīng)圍了好大一圈看熱鬧的人。
克萊特夫婦的心被刺痛了。多少年來,他們最不愿意見到的,就是眼前這種場景。他們開始反省自己中國之行的初衷。
他倆都是精神病學(xué)的專家。
克萊特是德語國家的知名人士。這位出生于德國歷史名城德累斯頓的男子漢,在青年時代就以其仁慈之心和專業(yè)特長投身于精神病者的康復(fù)工作。60年代末期,他升任一所衛(wèi)生院校的副校長,而后又擔(dān)任了德國《教育論壇》“慈善”專欄主持人。70年代,他憑卓越的才華和在德語國家的聲望出任德國聯(lián)邦政府“改善精神病人狀況”規(guī)劃委員會委員。此后不久,德國開始籌建“德國社會精神病學(xué)聯(lián)合會”,他積極參與了這一團(tuán)體的組建工作,并出任首任主席。卓越的成就是與難以想像的艱辛困苦為伴的,從事精神病康復(fù)的職業(yè)工作者更是如此。克萊特夫婦為治療精神病患者度過了人生最美好的年華;為了為精神病患者爭取一份應(yīng)有的社會權(quán)利,他們又歷經(jīng)了人間的艱辛。跨上中國的國土后,這對夫婦曾決定:不再從事與精神病康復(fù)有關(guān)的工作。
可是,自從見到武漢街頭那些精神病患者之后,他們的“決定”動搖了,職業(yè)的沖動和仁慈的本性使他們再也無法平靜。他們開始走訪武漢的精神病醫(yī)院,并參加有關(guān)部門組織的街頭心理咨詢活動。
1988年,克萊特夫婦為武漢江岸區(qū)精神康復(fù)中心捐款1000美元、1000馬克。同年,他們接受了該中心“名譽(yù)院長”的聘書。與此同時,他們在水運(yùn)學(xué)院的工作合同到期,鑒于他們的出色工作,學(xué)院要求他們續(xù)聘兩年,但他們已經(jīng)有了新的使命。他們?yōu)閷W(xué)院介紹了兩位接自己班的德籍教師,之后,這對夫婦立即返回了德國,他們要為中國的精神康復(fù)事業(yè)募捐。
美國著名社會活動家、國際殘疾人運(yùn)動的先驅(qū)海倫·凱勒曾經(jīng)說過:“殘疾人事業(yè)是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這是超越國境的愛心。”返回德國后的克萊特夫婦輾轉(zhuǎn)數(shù)千公里,自費(fèi)上萬元,跑遍了各個大中城市,找到了幾乎所有有名望的慈善機(jī)構(gòu)。他們的誠心感動了異國他鄉(xiāng)的慈善人員,從1989年至1992年,武漢市的精神康復(fù)機(jī)構(gòu)不斷收到來自德國、香港、德國駐華使館以及克萊特夫婦個人捐助的款項和物資設(shè)備。1993年2月27日,新華社報道:克萊特夫婦為武漢市精神康復(fù)事業(yè)募集的資金達(dá)240萬元。
早在70年代中葉,克萊特在擔(dān)任德國社會精神病學(xué)聯(lián)合會主席時,就與夫人羅莎創(chuàng)辦了數(shù)家為失業(yè)的精神病患者提供就業(yè)機(jī)會和“工療”的工廠。這種“克萊特式”的精神病社區(qū)康復(fù)模式很快在德國許多城市推廣。
如今,克萊特夫婦要在武漢來繼續(xù)他們未竟的事業(yè)了。
“我們要致力于消除導(dǎo)致精神病發(fā)病的諸多因素……”克萊特夫婦在武漢逢人就說。不論是聊天、授課,還是演講甚至包括為政府官員在內(nèi)的聽眾作報告,他們總要說到這同一個主題。
——貧困、失業(yè)、失學(xué)、愚昧、迷信、吸毒、人際關(guān)系緊張,還有歧視和偏見,都是導(dǎo)致精神病發(fā)病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們自稱是正常人,就應(yīng)該為精神病患者提供一個正常的生活氛圍。否則,我們又正常在什么地方呢?
——為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份工作吧!如果他們沒有工作——即使是一半患者沒有工作,他們的衣食住行及治療等開銷,也足以成為家庭和社會的巨大負(fù)擔(dān);無事則生非,無所作為的患者難以抵御心頭的空虛,便會滋事擾亂,這種損失就更加難以估量……
克萊特夫婦身體力行。他們用募集的捐款購機(jī)器、添設(shè)備,讓精神病患者在康復(fù)中心像健全人一樣地參加工作,參與游戲,樹立起生活的信心和勇氣,重新塑造新的靈魂。
僅有20張病床的康復(fù)中心的工作已難以使克萊特夫婦滿足;眾多的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病類型的多發(fā)性也使江岸區(qū)精神康復(fù)中心顯得難以適應(yīng)。克萊特夫婦決定創(chuàng)建一所全新的醫(yī)院,這所醫(yī)院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的精神病專科醫(yī)院的格局,它設(shè)有門診部、心理治療部、職業(yè)治療部、醫(yī)務(wù)社會工作部、社會康復(fù)護(hù)理部以及關(guān)懷精神病人聯(lián)合會。
克萊特夫婦將這所醫(yī)院命名為“中德心理健康白天醫(yī)院”。
1992年6月6日,“白天醫(yī)院”正式宣告成立。面對100多位來客,名譽(yù)院長羅莎·克萊特夫人激動萬分。她顫聲說道:“這家醫(yī)院是中德友誼的結(jié)晶。我們的責(zé)任,是要讓精神病患者充分感受到人間的溫情,并最終回歸于社會。”克萊特先生也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意味深長地向全體與會者呼吁:“讓我們一起來做修正上帝筆誤的人!六根弦既然斷了一根弦,那就用余下的五根弦來彈奏,只要認(rèn)真彈,一樣能奏出美妙的生命之歌!”
克萊特夫婦并不是崇尚空談的“傳教士”。他們以自己的行動給武漢市的民眾樹立了最佳的榜樣,書寫了一個個活生生的動人故事。
這一天,羅莎夫人下班回家,突然聽到樓旁水塘中有響聲,走近一看,是一位婦女在水中掙扎。羅莎不顧一切地將她拉上岸。這位婦女衣衫破爛不堪,表情呆滯。羅莎憑直覺判斷出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急忙將她帶回自己的房間,幫她脫下濕衣服,親自燒好熱水讓她在自己的浴缸里洗了澡,最后又取出自己的衣服給她換上。這位患者姓肖,果然是個發(fā)作期的精神病人。她的丈夫?qū)⑵浣踊丶也痪茫职阉突亓_莎身邊,請求羅莎再救一次他妻子的命。他說:“有您這樣的好心人給我的妻子治療,我絕對放心!”
那一天,克萊特先生大發(fā)其火,他騎著自行車經(jīng)過張公堤時,發(fā)現(xiàn)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衣不遮體,渾身是泥,左眼還有大面積的化膿傷口。他急忙將小伙子用車推回醫(yī)院,并給他洗澡換上干凈的衣服。護(hù)士為小伙子作了傷口消毒處理后,克萊特問值班醫(yī)師:“您準(zhǔn)備對他如何安排?”醫(yī)師根據(jù)小伙子的癥狀和當(dāng)?shù)氐挠嘘P(guān)規(guī)定,如實回答說:“先作治療,而后將他送收容所,由遣送站將他送回原籍。”克萊特問為什么要這樣做,醫(yī)師答道:“醫(yī)院無權(quán)收留來歷不明的患者,再說治療費(fèi)用也無處著落。”克萊特一下子就來了氣,大聲說:“不行,我要讓他住到恢復(fù)正常為止!”言畢,從口袋里掏出300元錢交給會計,說:“這些錢是他的醫(yī)治費(fèi),不夠再向我算!”緊接著,克萊特掛通了區(qū)民政局分管局長的電話,高聲說:“如果沒有我這個名譽(yù)院長的同意,你們讓這個患者離開了醫(yī)院,我就跟你沒完!”
誰還敢拒絕他的決定呢?患者住下了。事后,他高興地對那位醫(yī)師說:“你注意到他(患者)的笑沒有?這種笑是心靈純潔的人、毫無敵意的人才會出現(xiàn)的。”
武漢市江岸區(qū)精神康復(fù)中心發(fā)展了,壯大了,康復(fù)治療的網(wǎng)絡(luò)從小到大,從郊區(qū)到市區(qū),形成了一種院內(nèi)院外相結(jié)合的全新醫(yī)療體制。“白天醫(yī)院”的建立,又使這種社區(qū)康復(fù)網(wǎng)絡(luò)上了臺階。
盡管克萊特夫婦從不提起自己的功績,然而,他們的奉獻(xiàn)精神和全新的康復(fù)治療手段還是得到了海內(nèi)外同行的贊譽(yù)。民政部、中國民政康復(fù)醫(yī)學(xué)研究會分別介紹過這家中心的經(jīng)驗。香港、德國精神康復(fù)學(xué)界稱克萊特夫婦在武漢開創(chuàng)的事業(yè)是“偉大而又成功的創(chuàng)舉”;法蘭克福電視臺將這對夫婦在中國的無私奉獻(xiàn)當(dāng)作日爾曼民族博大情懷的典型事例加以介紹;德國駐京人員專門為克萊特夫婦和他們的患者組織了幾次盛大的聚會,讓他們介紹在武漢開創(chuàng)的人道主義事業(yè),家庭主婦們在聚會上高價義買患者們精心制作的糕點(diǎn),并為克萊特夫婦的事業(yè)慷慨捐款……
克萊特夫婦的奉獻(xiàn)精神和行善之舉在德國政府中也產(chǎn)生了反響。政府官員們將這對夫婦的高尚行為視作中德友誼的結(jié)晶。1992年5月,德國總統(tǒng)魏茨德克將聯(lián)邦德國十字勛章授予克萊特夫婦,這是無數(shù)德國人視為至高無上的榮譽(yù)。
克萊特夫婦最感到滿足的是病人們對他們的報答。有一段時間,克萊特夫婦清早開門,總能見到門口放著新鮮的魚肉和蔬菜。經(jīng)過多次查詢,終于“逮”住了送菜人。原來,這位送菜人曾求助于克萊特夫婦,她痊愈后無以相報,便采用了這種獨(dú)特的報答方式。在以后的每次演講中,克萊特都用上了這個例子:精神病患者完全懂得接受別人的關(guān)懷和愛,并且懂得如何予以回報。
1992年12月20日,是克萊特夫婦終身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們最大的愿望實現(xiàn)了——武漢市副市長和市公安局負(fù)責(zé)人親自將兩份“永久居住證”頒發(fā)給他們。這意味著克萊特夫婦將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走完自己的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