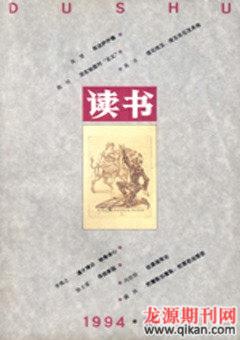懺悔的缺欠
1994-07-15 05:30:04陳立群
讀書 1994年10期
陳立群
從雷頤《自將磨洗認前朝》(《讀書》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一文我們讀到了陳凱歌關于懺悔與控訴錯位的精辟之論。然而我認為當前中國知識界的關鍵仍是懺悔的缺欠。在災難中的所謂“懺悔”大多是“臣罪當誅兮天子圣明”式的套話,何曾發自內心。沒有發自內心的懺悔,所謂控訴也只能是基于利害得失的委屈抱怨,而不會是出于公理良知的申訴抗爭。
懺悔的缺欠主要是由于沒有誠實思考的勇氣和習慣。“先在下意識中欺騙自己,然后又想象自己既誠實又有德。”(羅素《論教育》)于是有了一批衛道模樣的正人君子,頌王罵賊黨同伐異。對這些人說來,他們永遠不能從自己的皮袍下榨出個不字,也沒有勇氣喝盡自己釀成的酸酒。
其實,樂于回味過五關、斬六將的榮耀,而不愿回想失荊州、走麥城的狼狽,似乎也是人的本性。正視一切事實,尤其是令自己不愉快的事實,卻是需要刻意培養才能形成的品質。這本應成為品德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從小開始,可惜事實并非如此,雖然正心誠意之說古已有之。
懺悔的缺欠不僅導致歷史的遺忘,也導致歷史的誤解。相當多“文革”中的成年人對這場災難的理解仍屬于波普爾所說“原始的迷信”,認為十年浩劫是“某些有權勢的個人或集團直接設計的結果。”(《猜測與反駁》)過來人尚且不明不白,后生晚輩更是糊里糊涂。
由于缺少直面歷史的勇氣,便有了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只好想象一切從頭開始。“文革”十年的往事已差不多忘卻,幾年前的往事也要淡化。記性壞的人有福了,他們已得安慰;記性好的人有福了,他們永無安寧。
猜你喜歡
科普童話·學霸日記(2021年4期)2021-09-05 04:28:51
小學生作文(低年級適用)(2019年12期)2020-01-18 07:50:36
學與玩(2018年5期)2019-01-21 02:13:06
中國化妝品(2018年6期)2018-07-09 03:12:42
小學生優秀作文(低年級)(2018年5期)2018-04-24 02:05:29
讀者(2017年15期)2017-07-14 19:59:34
全體育(2016年4期)2016-11-02 18:57:28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6期)2015-10-13 07:21:18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9期)2015-09-22 07:36:52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8期)2015-08-14 07: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