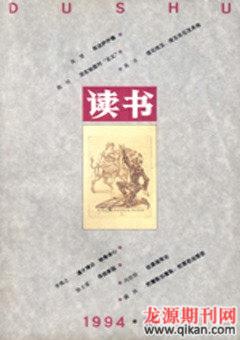大浪淘沙
孫達人
魏特夫及其《東方專制主義》具有相當典型的意義。盡管中國讀者看到這部書比初版晚了三十多年,現在我們評論這部書又比中譯本的出版晚了五六年,這也許反而為適當評價本書創造了較好的條件。當本書中譯本剛出版時,人們對許多充滿火藥味的詞語——諸如“赤手空拳不能進行戰斗”、“西方對待官僚極權主義必須抱一種既了解情況又敢于有所作為的態度”云云,也許相當敏感;而今,我想我們已能夠充裕地看待問題,把那些過于情緒化的東西放到一邊。歷史不僅比任何人,也比我們的總和都要有力量得多。大浪淘沙。作為歷史學家更應該有深邃的眼光和豁達的氣度來審視一切學術成果,也允許別人以同樣的態度來審視自己的學術成果。
魏特夫的經歷很特殊,以至可以說具有戲劇性。他是一個西方人,可是以畢生精力研究東方社會;他曾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后來與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他曾當過共產黨員和德共中央委員,后來與共產主義運動決裂,全身心地為西方世界填補“理論上的真空”。一言以蔽之,魏特夫是一個在生活、思想、工作和信仰上經歷跨度都很大的人。正是這種經歷和跳躍,使他積累了關于東方社會歷史和現實的豐富知識,也使他的著作具有特別意義上的典型性。
從廣義上講,東西方關系至少是全部成文史的關鍵問題之一,長期以來一直是歷史學家關注的焦點。從狹義上講,東方社會究竟向何處去,對于東方人自然早已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問題。對魏特夫的跳躍不論喜歡還是不喜歡,這種經歷是一種溝通認知的橋梁;他畢生研究所得,不論是正確還是謬誤,都是東方社會研究中的一種積淀,并從正面或負面給予人們以啟迪。對于象我這樣的人,因為歷史和個人的原因過去對西方的認識太少,自己在閱讀《東方專制主義》中的突出感受是收獲比讀許多觀點與自己類似的著作還要多些。
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的學說不是無源之水。毫無疑問,不僅黑格爾、亞當·斯密,而且還有孟德斯鳩、赫德爾、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理查德·瓊斯等人的意見都給予馬克思的觀點以一定的影響;同樣毫無疑問,馬克思關于東方社會的觀點打開了魏特夫整個研究生涯的大門。不過,假如有人想要就吸取前輩遺產方面對他倆作一比較,那末,可以發現一個重大區別:前者把前輩的遺產進行了消化,化為了自己學術體系的血肉;在后者,前輩的遺產象是兩股洪流激蕩,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陷阱。這是曾經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魏特夫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不同之處。
《東方專制主義》引證的文獻達八百五十六種。這對于擴大視野是很有好處的。即以我們比較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而論,他的熟悉程度也值得稱道。本書十分重視自然環境的作用,認為歷史條件相同時,重大的自然差別可能導致決定性的制度差別。他說:“正是水源不穩的情況所產生的任務促使人類去發展由社會進行控制的治水方法。”這個意見顯然是正確的,值得引起重視。盡管本來馬克思早已指出過大體相同的意見,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國學術界卻長期相當漠視。同時,魏特夫對灌溉農業的許多分析也有獨到之處。例如,他認為,這種農業與雨水農業、澆灌農業不同,為進行農業耕作首先必需有與耕作本身分開的大型灌溉和防護工程,在工業化時代之前,這種大型工程既造成特殊類型的勞動分工和大規模的社會合作,也為集權政治的產生、天文學和數學的發展和其它大型建設奠定了基礎。此外在一些往往易于忽略的地方,例如東西方建筑風格上的差別,本書也說出了不無啟發的意見。當然,魏特夫至少在他自己非常自負的中國史領域也講了不少外行話和錯話。這里舉其至關重要的一個:由于誤把被許多山脈分割的中國視為是一個地理上統一的國家,而且看來也根本不知道近一萬年以來我國北方的氣候經歷了一個由原先比較暖濕,到距今三千年以來變得日益干涼的過程,以致誤認為“在機器以前的時代是如此;今天基本上仍然如此”。因此,他既不了解一萬年以來中國的原始農業,也不了解近二千多年新生的精耕細作農業。直截了當地說吧,他對中國農業史的知識還是三、四十年代的,早已大大落后于現代科學水平了。順便說一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國農學和農業史的研究,在一大批老中青專家鍥而不舍的努力下,成果斐然。這對于理解中國歷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亞洲的歷史自然有很多的共同性。如果說非洲是我們人類的搖籃,曾經長期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獨占鰲頭,那末,在此后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亞洲的貢獻特別巨大。這里是農業的發源地,也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圣地。現代歷史學已經在這一點上形成了共識:截止中世紀后期之前,亞洲的文明仍具有相當先進的水平。到了中世紀后期開始,這個曾經領先的大洲無可挽回地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西歐北美的大西洋文明,亦即現代資本主義文明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這就是說,從世界歷史的全局著眼,亞洲的文明盛衰過程存在著共同的趨勢。如果從制度上著眼,亞洲的政制長期以來確實都是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社會體制方面,私有制長期發展不充分。上述這些共性在研究亞洲史時都必須重視,而決不可以忽略。但是,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和喜馬拉雅山脈把亞洲一分為二,東西亞在地質、地貌和氣候條件諸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就相互交通而言,西亞與歐洲比之它與東亞反而要方便得多。中國本身就占東亞很大的一部分;如果算上中華文化輻射圈,幅員更加遼闊,人種獨具特色而且眾多,文化自成體系。因此,在注意到亞洲的共性同時,也決不可忽略亞洲內部東西兩大塊之間存在著的重要區別。這恰恰是《東方專制主義》為構筑自己的理論體系時完全忽略了的。
魏特夫從用水的角度把農業區分為治水、澆灌和雨水三種類型是有學術價值的。布羅代爾在其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從作物的角度把農業區分為小麥、稻米和玉米三種類型,捉住了農業更本質的特性,因而更具有啟發性。不過,看來他們都忽略了還有另一種類型的農業——以粟為主要作物、以精耕細作為主要手段的旱作農業,以及這種農業在我國所經歷的特殊發展過程。簡要地說,這種精耕細作的旱作農業于戰國時代產生在我國北方的黃土地上,后來不僅在作物上越來越增大了小麥生產的分量,而且又進一步在南方的水稻生產中發揚光大了它的精耕細作技術。正因為如此,學術界把我國在原始農業之后發展起來農業稱之為精耕細作農業。關于這個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南京農學院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著的《中國農學史》對此作出了系統闡述,我也曾著文從理論上有所剖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這里我想著重強調的是中國的精耕細作農業在兩個基本方面具有與其它地區傳統農業的重要區別:從技術方面看,它是把氣候條件即所謂天、自然條件即所謂地和農民的能動作用即所謂人三者結合為一個有機系統,因而既不是適應一種氣候條件的灌溉農業,也不是適應特定土壤和氣候條件的小麥農業或雨水農業,而是根據我國幅員遼闊、氣候類型多樣的客觀實際,把旱作和灌溉,粟、小麥、稻米、玉米等多種作物綜合地加以利用,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農業體系。它的實質,大學者王充早在公元初已正確地概括為“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從經營管理方面看,它與集體主義形態不相容,農業的經營單位始終是個體的,因而也就決定了我國社會的基本生活和生產單位,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合二為一,并使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長期成為社會的獨立細胞,而在觀念上則具有十分強烈的家庭和家族色彩。上述兩方面的特點互相要求并互相促進,其結果既使中國農業創造了高于古代其他地區,甚至足以與現代農業相比的單位面積產量,而且,這種結構極為簡單的家庭農業極易水平位移,無孔不入地普及到能適于它生存的一切地方。正是這種從結構上看幾乎是一模一樣而且越來越分散的小農,就是產生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基礎。也正是由于同一原因,中華文化具有極其強大的輻射力,使中國本身形成為一個具有悠久而且連綿不斷歷史的特大型社會實體,形成了獨特的東亞文化圈。當然,還是出于同一原因,這種曾經在戰國至唐宋之際使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創造高度和博大豐富的內涵方面都確曾具有世界先進性的中華文明,在明清以后長期地停滯而落后了。魏特夫無視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特殊的發展過程本來未可厚非。因為一個文化淵源上不同的西方人在了解完全陌生的文明時容易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可惜,他是出于民族偏見,為構筑理論體系的需要而蓄意抹殺了這些區別。最明顯的證據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日本的社會從來也不是治水社會”,在亞洲唯獨把這個分明的東方國家硬扯入西方社會的范疇。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邁出了東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步,并且取得了越來越大的成就,使發源于西方的現代化過程出現了東亞色彩。這個事實是這樣明顯而無法否定,迫使魏特夫只能采取“肢解”法。他原以為日本無非是一個不大的島國,割去之后便可自圓其說。但是,客觀歷史進程是這樣的無情和有力,為時不過二三十年,繼“亞洲四小龍”興起,東亞的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又在崛起。現在,被魏特夫定為“治水社會”的“核心地區”,也就是據說靠“內部力量”絕對不能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在實現獨立之后,雖然經歷了坎坷不平、艱難曲折的道路,終于也開始了大規模的現代化過程。當然,這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更有別于日本之與歐美。在本文開頭,我說該書中文版的晚出幾十年更有利讀者理解,就是指現今才具備可以對這部著作進行真正學術討論的條件。
歷史的內涵無比豐富。且不說三百萬年來的人類全部歷史,即以近幾千年文明史而言,事關多少國家,發展過程又是何等漫長和復雜,史學家要想了解它,除逐一研究它之外,別無他途。但是當他們在這樣做并做出了某些成績之時,千萬要有自知之明,決不可被自己歸根結底說還是一孔之見所陶醉,飄飄然起來,落到一葉障目的程度。坦率地說,當魏特夫在書中對馬克思主義的若干原理進行攻擊時,隨處都有這類令人不愉快的表現。
然而,即使在這些處所,也要進行具體分析,未可一概而論。魏特夫在書中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進行了攻擊。其實,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只是說:“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僅此而已。但自《聯共(布)黨史》開始,馬克思所說的“社會”被擴大到幾乎每一個民族和國家,“大體說來”的“幾個時代”被升格為“客觀規律”,簡言之,由此而弄得婦孺皆知的五種社會形態說比馬克思痛斥過的“萬能鑰匙”還教條化,然而卻長期被奉為金科玉律。誰若對此稍有異議,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其實世界上從來也沒有一個國家曾經依次經歷過五種社會形態;現代的社會主義運動恰恰都發生在非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很不發展的國家和地區。毋庸諱言,從《聯共(布)黨史》以來把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學說教條化的普遍而惡劣影響,已使理論和事實嚴重脫節。許多很有水平的西方和中國學者都拒絕它,這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魏特夫對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學說的攻擊其所以還有一定的市場,與這種學說長期被嚴重歪曲是有關的。當前,為恢復馬克思的社會形態學說的本來面貌,就必需清理其嚴重歪曲。
魏特夫重復講了許多上一世紀西方非常流行的昏話,這種充滿殖民主義的論調很傷害東方人的感情。但是,我們反省自問,過去曾經充斥一時的“世界革命”云云恐怕也稱不得理智。更重要的是,他博學多識;我們決不可因人廢言,也不能用片面來解釋和對待魏特夫的片面。該書批判專制主義,指出東方的私有制發展不充分等等,盡管缺乏歷史態度,卻仍值得特別重視,需要我們在實踐中逐步邁出符合國情的轉型步驟。世界極其復雜,客觀事物并不以人們的好惡而改變其存在和性質。簡單地按別人反對的我們就贊成的邏輯辦事,其實是不成的。千萬別忘記,我們面前的路還很長很艱難,已取得的進展還只是開始,而歷史造成的差距仍然很大。
世界是一個整體,它始終向前發展著。但作為它的一個部分,無論是種族、民族、國家和地區,還是某種文明,都是有限的,都既有上升也有下降的興衰存亡過程。世上從來沒有永遠興盛的民族和文明。落后變先進,先進轉落后,概莫能外。我們決不可把興和衰凝固起來變成驕傲的資本或悲觀的根據。讀了《東方專制主義》應使我們更聰明和更開放一點。偉大的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末曾周游中國,據親身經歷寫出的著名游記盛贊了中華文明。當時西歐還處在由落后變先進的前夕。馬可波羅看不到中國和西歐即將更換落后和先進的位置,這可以用歷史條件來解釋。六七百年的進步應該允許今人能更方便得多地了解和利用現代文明,并看得更深遠一些。問題全在于必須善于學習,敢于創新,不懈地為中國和東亞的復興作出應該的貢獻。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九日
(《東方專制主義》,〔美〕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9.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