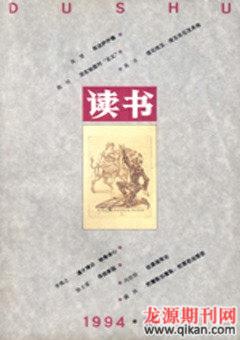尋找家園
張士甫
六十年代以后,臺灣詩歌放棄自身而為某種社會意識充當奴仆的角色在歷史的格局中已成為過去。——與西方文化的密切聯(lián)系使得詩向西方詩西方哲學發(fā)生了很大傾斜。產(chǎn)生了諸如商禽等超現(xiàn)實主義“點火人”,較早地進入了(或企圖進入)非理性領域。亦產(chǎn)生了鄭愁予之類代表性詩人。那確是傳統(tǒng)詩藝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二道相因”的產(chǎn)物,是唯有中國這塊土地上方可結(jié)出的豐腴果實。
臺灣詩的一個很大長處在于確有詩的“理法”——標準是不容含混的。冒牌詩人及詩的贗品較少。原因可能在于即便總編輯有意兜攬,尚有社長、發(fā)行人、董事會在。刊物是不愿——也不敢砸自己的鍋的。
另一方面它的已達國際水平的評審團八十年間漸趨成形。其背后是遍布西方世界的教授、科學家、學者、詩人。均頗負“良心”。使小魚很難過關,大魚很難漏網(wǎng)。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臺灣詩大有放棄東方詩及東方哲學優(yōu)勢的趨勢。詩人們大多對西方詩之“醉境”趨之若鶩,對東方詩之“禪境”則少有問津。
臺灣詩人在人群中的比例比大陸密集,學歷及文化層次相對為優(yōu),詩在文學藝術(shù)領域之比重亦大,科學家詩人尤多。——不以寫詩出身似不以科舉出身,則難為文學界之“朝官”矣。我每有這種印象。
但是教養(yǎng)本身也可能帶來很大弊病。使詩人、詩極易陰盛陽衰。一旦缺乏惡的杠桿,缺乏憂患、大不幸及深沉的內(nèi)心悲苦,詩的份量便可能輕飄飄的。
這當然不是指天才,天才屬于例外。
紀弦為臺灣詩壇之大宗師,現(xiàn)代派及現(xiàn)代詩社的創(chuàng)始人。
紀弦決非識時務之俊杰,卻極具霸氣才情。
他似乎不是以詩確立了他在臺灣詩壇絕無僅有的地位,卻是憑借人的本身——氣質(zhì)、風度、非凡的性格、魅力。
想象不出有比紀弦更象詩人的詩人。
紀弦在三十年代即與《現(xiàn)代》雜志頗多過從,并與編輯之一的杜衡和主筆之一的戴望舒相友好。其他詩友還包括徐遲、歐外鷗、番草等。與卞之琳、馮至、孫大雨、梁宗岱亦有交往。其文學創(chuàng)作及文學活動的豐富閱歷使紀弦及早便成為影響中國詩壇的人物。
除了與生俱來的孱弱、敏銳、孤獨、憂郁外,與外界的不協(xié)調(diào)、經(jīng)常的生錯及不合常情的舉動是詩人種種不對勁的緣由。此外,真正的詩確乎是毫不實用的,決非任何階級、集團、思想觀念所可利用,因而是不能贏利的。
但并不因此詩便降低了對詩人的要求。它甚至愈發(fā)需要詩人的智慧獨立于意志之外。乃至對歷史以及重大變革的獨到理解,對其背后動因的時代性把握(以至與社會兩相抵忤),對未來的預想,即前知等等。
紀弦以他的近于政治家的氣度、行動的孤傲及種種失敗——習慣性的失敗,造就了他的大成就。
白話詩運動以來,很少有人比紀弦走得更遠。請看寫于一九四二年的《吠月的犬》:
載著吠月的犬的列車滑過去消失了。
鐵道嘆一口氣。
于是騎在多刺的巨型仙人掌上的全裸的少女們的有個性的歌聲四起了……
不一致的意義。
非協(xié)和之音。……
紀弦早年在美術(shù)學院攻讀繪畫,擅用畫家的眼光感應事物,有不同常人的靈異之處。
意象凄美、神秘。確不比布勒東艾呂雅差多少。——可說一點不差。
詩寫于紀弦從淪陷的香港搬到上海之后,在百般磨難中其創(chuàng)作的熱情可想而知。
——更無人比紀弦鬧的動靜更大。
他竟僅憑匹馬單槍在中國詩史上創(chuàng)立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流派。
《九葉集》的問世是在一九八一年,人們從塵封中發(fā)掘出九位詩人四十年代的創(chuàng)作,發(fā)現(xiàn)了一個一脈相承的體系及其在新時期的拓展,隨后引發(fā)了一場“膝隴詩”的爭論,隱隱約約名為“九葉”的一個現(xiàn)代詩派方結(jié)胎而成形。
在此之前,紀弦領導的現(xiàn)代派幾乎是中國現(xiàn)代詩史上的唯一流派。(相較而言,《新月》《七月》等均時間過短,影響較小。)
他的情緒是哀怨憤怒的,他的生命和創(chuàng)作是真和狂放的。他領導的社團及運動一度如火如茶,幾近揭竿而起的暴動,對傳統(tǒng)和秩序構(gòu)成極大威脅。
詩本性如此,他又僅僅忠于詩,詩是他的宗教。
紀弦現(xiàn)居住美國。即便為“現(xiàn)代詩四十年”慶典也拒絕命駕,過著隱士般的生活。——比梵高的遭際稍好。
從詩的角度說,商禽詩是臺灣詩一個方面的代表,這方面是一個主要的方面,具普遍性。
商禽幼年棄學,出身士官。曾在美游學二年。其詩“有形而上之玄思,有悲天憫人之情懷”,角度與思維均極詭異。
他的傳誦一時的名篇《鴿子》《長頸鹿》《阿蓮》《狗》《無言的衣裳》總有一股悲涼感傷的氣息,如忍冬花香紛組而迷人。
商禽詩的思維始終訴諸于“自性”。有“即心即佛”之意。宛如“中夜宿田里,睹星月燦然,有省。”主觀心靈的作用顯而易見,每每統(tǒng)率全篇。
而其語言若明漪絕底奇花初胎。——簡練精當而又優(yōu)美。
月已西沉親愛的
不要去搬動
盆栽當心
你薄薄的影子
被突來的晚風吹落陽臺
——《露臺》
確有些許禪意。詩人在與造化對話。
不足處在于:此公之詩屢屢落入窠臼。——始終囿于局部的微觀的范疇。心力筆力自非雄渾之品。直截點說吧,欠大才力大學問大風范,也就征服不了大題材。
“點火人”的稱號也許是名實相符的吧。
“中士”是許多人對商禽的親昵稱呼。而“中士”在詩品中畢竟難為上上之品。果然詩如其人耶?
詩之品位固然難求一律,然詩之生命——尤如禪之底蘊必為生生不息。詩之理法——有如禪之理法,說到底是不斷地破除理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斯而已。
更何況不超以象外何可至大不可限制?又焉有“道”在?不能返虛入渾,如何積健為雄?以得“環(huán)中”?——詩之真諦也?
綜觀商禽兩部詩集《夢或者黎明及其他》與《用腳思想》覺商詩之非理性因素亦非如臺灣評論家所以為的多。——似尚在非理性邊緣徜徉,唯其入門意識強烈而了然。
我以為,若果欲進入非理性領域,非極其渾厚的禪學及至玄學功底不可。公允的說,嚴格意義上的超現(xiàn)實主義詩人,其文字游戲、夢囈、下意識書寫等等并非真詩。——其挖掘潛意識的動機很有必要,途徑顯然不甚對頭。比如布勒東,一生都在寫不是詩的詩,而那的確不是詩。——與東方的詩性智慧相比只是鬧著玩罷了。(并非某種文化非要排斥某種文化)就詩來說,超現(xiàn)實主義理論是有啟示意義的,作品卻是十分幼稚的。——決非“眾妙之門”。
當然詩的含義多種多樣。以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者——諸如商禽——已為好詩,而好詩已靠近神明之觀,距虛無之宅或抑有期乎?
商禽詩不是臺灣詩的一個側(cè)面,大抵包涵了全部靈秀及不足。
而我閱讀最多,也最敬畏的詩人是鄭愁予。
其《窗外的女奴》《夢土上》《衣缽》坊間早已無存。好在多數(shù)精品膾炙人口神交以久。
從大陸至臺灣至美國,經(jīng)歷了戰(zhàn)亂(一度處政治軍事漩渦中心)、治學及專心述造種種生涯,鄭氏之心路歷程,囊括了整個民族半個世紀的興衰。行近靡靡,中心搖搖,無怪總有黍離之音。
他的詩時而直接干預治國安邦(詩人于政治顯然決不外行)——而其政治詩一如情詩,亦是給自己、知己看的,非受命也。(雖如此,此類詩仍為鄭詩之
而這些都不是
禪與處子談到詞窮處
竟又進入余蔭后的微雨
這種只適可散步七分鐘的雨
少了不夠潤
多了便是漉
所謂禪微雨行到六分鐘的時候
也許就咝咝……咝咝地悟到了……
——《談禪與微雨》
這首詩竟寫在鄭愁予湖南求學的日子。當在十六歲以前。
其思維及語言令人嘆為觀止。
“俱胝斷指”說的是同樣豎起一指示法,其含義則不可同年而語。
從詩的形式看——才力豐美、工于語言——鄭愁予其時似已有資格談禪。
編入《刺繡的歌謠》中屬“歌謠風”的鄭氏之早期詩作,毫不遜色于較晚期的詩作。這興許由于“早熟”,抑或他本屬“正常的兒童”,在其一生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中一出手便達可望不可即之境。——有似希臘藝術(shù)。這當然亦在情理之中。
《錯誤》是一首名篇,由此曾引起種種揣測、誤解乃至非難。我嘗聽詩人當面論及原委,蒙冤屈之狀可掬。其實讀詩是一種補充的創(chuàng)造。詩所蘊含的信息量非關象內(nèi)。“得意忘象”從而達到超言絕象之“本體”,恰為詩之神髓。詩何必達詁。倒是愈不留形跡愈好。
《錯誤》的感應力十分巨大,具有令人莫名其妙的藝術(shù)效果。
鄭愁予詩集尚包括《雪的可能》《燕人行》以及諸種選集,篇幅頗巨。而其涵養(yǎng)既深,天機自合。——日甚一日,如惠風然,如篁音然。其愛情、友情、公情及域外之情,以情真意切堪稱極品。
臺灣詩至鄭愁予已至顛峰狀態(tài)。鄭詩是一個時代圓滿的終結(jié),但詩之本義卻在嘗試和實驗中以健行周流,永不衰竭。在不斷地聚變或裂變。一旦有了詩式詩格即已落入理性思維模式,便阻斷了頓悟思維之途徑。(為此倒是每每需要突然割斷理性思維)那么,新的時期如何開始?
契機是無盡藏的,現(xiàn)代詩這一概念僅在于抓住新的契機,以達到“物我渾契”、“天人合一”。
鄭愁予是熟諳禪宗的,但顯然尚未“即心是佛”。鄭詩是追求詩之現(xiàn)代的,卻遠遠未及神秘之境。
神秘是似即似離的、混混沌沌的、惟恍惟惚的、模模糊糊的。心賞其美神與之契,鄭詩似可得也。出神入化,須莫之求而自致也,鄭詩似未及也。
臺灣中青年詩人中——卓犖不群者甚眾。——鴻鴻以其“見素抱樸”的弱道哲學而純?nèi)惶鞕C。其詩可謂“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在一九九四年《中外文學》一期讀到鴻鴻以墻取象作譬之《紅墻》,有“明道若昧”之感,留下極不尋常印象。
他描述的墻決非現(xiàn)世的,只是意識的現(xiàn)實。而其諸般意象來自多種邏輯,煞是“模糊”。——類屬差異大,從而留出的想象空間大,呈多方位、諸形態(tài)。最終一種駕御一切的力量在驚恐、憾惜、悔恨、哀愁中顯現(xiàn)。——由人的意旨組成了解放的合力,自由精神隨著永恒精神之流一同流動,支柱是柔韌而剛強的。那是對一個時代反芻性的深思,通體透出禪機。
冥冥中似有一主宰一切的力量,詩的含義正在于揭示這一力量,向所有心靈顯現(xiàn)它的“朋從爾思”的境界。
以期交感,找到得失。
臺灣現(xiàn)代詩繼承了中國詩歌的道統(tǒng),其發(fā)展歷程及方向具有極大意義。然而相較于如此紛繁擾攘的時代,如此多變而凝重的歷史以及無盡的人生苦難,其堪稱力作的作品卻也陳陳相因。更重要的是,真正進入非理性領域的詩作尚嫌太少。更由于地域的限制,其視野、才力、氣宇畢竟不盡如人意。
作為東方詩人,對東方詩及東方哲學的理解亦難說充份。
這筆財富的挖掘大約有待時日。
詩確實有賴于時代及家國的氛圍。
在長期的東方理性主義時期,儒家的“詩教說”始終不兼容東方神秘主義。——這一純粹精神的建構(gòu)與佛老之學有極深緣法。而在此之前從河洛到八卦到易,它由來已久。原始的巫學智慧潛隱著稚憨又靈動的美學智慧。及至文心雕龍以來,滄浪、漁洋、隨園無不強調(diào)對對象的直覺把握。這一思維方式是不可或缺的,是不宜偏廢的。
不然詩就太乏味了。
思來想去,我們最終——也只能寄希望于人民的海洋。詩必須是自由而自在的。在其深深的海底,不會沒有指示著未來的擁有無限能量的潛流。
在分離了近半個世紀之后,兩岸詩壇已各自成為對方的一面鏡子。這一比照或許具有方法論的意義。——若再伴隨以哲學的、道德的、倫理的、觀念與技術(shù)的(包括文化市場及刊物運作機制)相應變革,相互借鑒、雜糅,并因此集合各方面之新表現(xiàn)而劃為另一時代,當為中國現(xiàn)代詩的希望。
本體為無限、為一、為和、為沖淡、為元氣;而萬形則為有限、為多、為各有所偏。——我以為,沿著禪心、玄心而接近“自性”,接近“本體”,接近“道”,那得意而忘言忘象的空間,便是現(xiàn)代詩的“家園”。
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