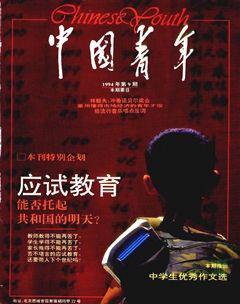家長:為了孩子可以犧牲一切
楊曉升
這里沒有愿意不愿意的問題。只要你有孩子,命里注定你就必須同他(她)一道去“爬雪山”“過草地”——
有一股風,無形卻難以抗拒的風,裹挾著當今中國眾多望子成龍的家長,魚貫般往前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你的子女到了上學年齡,你都會被這股無形的風裹著拖著,跟在子女的身后艱難地往前走。
上“重點”不惜血本
遠在子女上學之前,許許多多的父母便千方百計地琢磨著如何將自己的寶貝子女送上一所“重點”學校。在當今的大都市,“重點”還有“區重點”“市重點”之分。“重點”學校就那么多,僧多粥少,怎么辦呢?找關系,送禮,或者,高價“贊助”學校。眼下的贊助數目是數千、上萬乃至數萬不等。如此大的金額,雖難為了眾多的父母,但只要能達到目的,都不惜自己克勤克儉、節衣縮食,不惜陪著笑臉四處籌借。
“重點”首先意味著較高水平的師資和高升學率。一般來說,重點學校的老師對本校的“重點”榮譽又是極其珍惜的。維護或保住榮譽靠什么呢?當然是升學率。升學率越高,學校的地位就越高、名聲也越大。這在學校與學校之間也已形成一種競爭。而這種競爭,多數是用增加學生作業、給學生補課的方式進行。你給學生10道題,我布置20個;你補習1小時課,我再加一倍……
3年前,借助朋友的幫助,姜將女兒送進了北京市一所名聲顯赫的學校。欣喜之余,姜又不免發愁。從家里到學校,騎車馱女兒需花1小時,每天來回2小時,行程20公里。她本是搞業務的,三天兩頭要出差,可為了每天能準時接送女兒,她不得不放棄業務,到本單位的辦公室當打字員。
學校對學生的要求極其嚴格。比方評“三好學生”,北京市一般要求學生每科不低于90分,而該校則要求95分。好在姜的女兒很爭氣,從一年級到現在的四年級,她每科考試成績應試教育,能否托起共和國的明天?”都保持在95分以上,總成績也一直處于班里前10名。即使如此,姜還是千叮嚀萬囑咐,竭力為女兒鼓勁。有時女兒某科考試已得了95分,姜也心急火燎大不滿足。她對女兒說,少了一兩分,就掉下好幾名,別人都憋著勁,你怎么能放松下來?那不等于退出競爭嗎?姜還說,這輩子自己一事無成,就指望著女兒能有出息,給爭口氣。
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失落
姜的這番話,實際上反映了當今中國年輕父母們的普遍心態。一方面,獨生子女的出現使中國人“光宗耀祖”的傳統心理更加突現;另一方面,曾經被動亂年代剝奪了上大學機會的這一代年輕父母,大都把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期望著以此彌補自己的人生遺憾。為了使孩子在未來的競爭中多幾分成功的把握,善良的父母們不惜忍著那份“十指連心”的痛楚,自小便逼迫孩子擠上競爭之路。前些年,孩子們的業余學習主要是“琴棋書畫”,在這方面有特長的孩子,升入高一級學校時能夠于考試成績之外加若干分數。于是,就有成千上萬的孩子從幼兒園起就被家長“逼”到了鋼琴前、畫架前……有一個男孩,3歲起母親就逼迫他學鋼琴。一次,鄰居聽到他一邊哭一邊傷心地訴說(當時他大約5歲):“我說了我不想彈,你們非逼著我彈,彈不好你們就打,還盡揀我的手指骨打。你們是哪兒疼打哪兒,哪兒肉少打哪……嗚嗚……”母親心里痛著哭著,理智卻依舊執著于“棍棒底下出人才”的信念。
家長最怕開“家長會”
14歲的田煒,原來在光明樓小學讀書。光明樓小學也是“重點”,但實行的是“快樂教育”。可上了本區的一所重點中學之后,田煒的“快樂”一去不返,沒完沒了的作業總是壓得他抬不起頭來。每天,自打父親將他送進校門,到黃昏父親下班來接他,小田煒的唯一任務就是端坐在課堂里,一節課接一節課地聽老師滿堂灌。而每天所有的作業幾乎都通通背回家里,然后在除了吃飯和睡覺以外的時間里一道一道地做,而父親還得坐在一旁輔導。每天晚上及節假日,做父親的把原本看書及休息的時間全搭進去了。然而,由于作業過多、過于勞累,小田煒時常在晚上九點作業還沒有做完便打瞌睡了。如此疲于應戰,從“快樂”教育到“不快樂”,小田煒一直沒能適應,于是他的成績只屬中游。眼看著被學業所累的兒子,做父母的時常疼愛不已。小田煒的父親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眼下是中央某部司局級干部。他同我淡起孩子的教育時,不無沉重地搖頭嘆氣。他說現在養個孩子比過去的父母養幾個孩子還累。過去自己的學習完全靠自己、靠自覺,照樣能考上大學;可現在不知怎么,孩子每天的作業、試卷都要家長簽字。此外,還幾乎三天兩頭要開家長會,洗耳恭聽教師們的各種要求甚至訓話。
一位高中學生的家長就說過,現在簡直是家長在上學!孩子學不好,學校不找學生找家長。家長會上,點到哪個學習不好的孩子,哪個孩子的家長就得當著其他家長的面站起來聽老師訓話。另一名家長則訴苦說,他的孩子在一次模擬考試中,政治考得不理想,學校竟把家長叫去辦學習班,學習怎樣輔導孩子復習功課。不少家長埋怨:“今天的家長真不敢去開家長會!”
兩難境地如何是好
張是一家報社的記者,按說,單位不坐班,她可以安排足夠的時間輔導兒子。可眼下,兒子的學業已實實在在地成了她一種巨大的精神負擔。在兒子學校召開的一次家長會上,她曾被兒子的老師當著眾多其他家長的面點名站了起來,老師不留情面地訓她:“你兒子數學老學不好,你是不是該帶他去看心理醫生啊?”張剎那間感覺到像被撕下了臉皮,又羞又惱。
張的兒子生性活潑好動,上小學時他就招老師煩,一次兒子因未按老師限定的時間做完數學習題,遭到了老師的嚴厲訓斥,從此,兒子便對數學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懼。張發現這樣下去對兒子的學業不利,于是讓兒子轉到了離家近的一所小學就讀。沒料情況并沒有好轉,兒子常遭到老師的批評訓斥,加倍罰做作業,還被當眾踩壞了鉛筆盒,原因還是由于數學。兒子的數學果真那么不可救藥嗎?為了驗證兒子的數學水平,張找來幾道習題,鼓動兒子一同比賽,結果,張敗給了兒子。張恍然大悟,兒子并非真的數學不行,而是因對數學老師的潛在恐懼導致在演算時經常出錯。數學老師的教學方法苛刻而且機械,動不動要求學生背多少多少遍,抄多少多少遍,可張的兒子不喜歡死記硬背,與老師的矛盾緣此而起。于是,張苦惱不已,她不可能去糾正教師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態度(生怕那樣會給兒子招麻煩),又不愿強迫兒子按照老師的要求一招一式去完成作業。這種兩難境地深深地困擾著她,她不知道如何是好。
1994年7月7日上午8時。北京大學附中考場門前擁擠的人群中,一位母親目送女兒走進考場,之后稍微舒了口氣,她說:“女兒不讓我來送,但我怎么能放心呢,只好跟在她后面,還不能讓她瞧見。”
在北京八中考場,一位父親提著幾袋包裝的飲料,正在焦急地尋找女兒。僅是女兒早餐后沒喝水,這位父親就騎了兩個鐘頭的車從郊區趕來了。汗水和雨水已經濕透了全身,那幾袋飲料卻被他嚴嚴實實地裹在懷里。在場的兒位家長感慨起來:“為了孩子,該做的不該做的我們都做了。就是不能替他們考試,要是能的話,我們肯定比他們還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