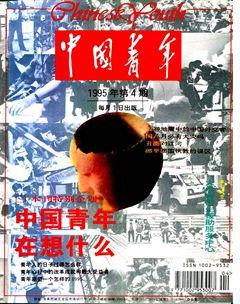共青團(tuán),走俏大上海
陸康勤
當(dāng)我決定用這一題目作文章名時(shí),團(tuán)上海市委書記鐘燕群對(duì)此提出異議,她說團(tuán)干部不管什么時(shí)候都應(yīng)謙虛謹(jǐn)慎,要珍惜好形勢(shì),好自為之。我理解鐘燕群的深意,但仍堅(jiān)持。理由是共表團(tuán)干部走俏,不是哪個(gè)團(tuán)干部個(gè)人的事,也不是哪個(gè)團(tuán)組織的事,而是全團(tuán)的欣慰,也是黨的事業(yè)發(fā)達(dá)興旺的標(biāo)志之一。于是我便寫了下面兩段文字。
行情走悄的團(tuán)校畢業(yè)生
偌大的上海,天天有新聞。下面的這條消息或許就被眾多的新聞所淹沒,被人忽視了。近年來,團(tuán)上海市委所轄的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xué)院(以下簡(jiǎn)稱“上海青干院”,原為上海團(tuán)校),報(bào)考者熱火。五六年前該學(xué)院所招收的選送生在全市高中會(huì)考的數(shù)學(xué)、語文、外語成績(jī)僅為BBC級(jí),1993年由于選送生候選者增多,入選者會(huì)考成績(jī)升至BBB級(jí),1994年又躍至ABB級(jí),且該年錄取的選送生一半以上是重點(diǎn)高中的班干部。1994年應(yīng)考生的報(bào)考與錄取比例達(dá)到7.5∶1,大大超出當(dāng)年全國高考平均錄取率(3∶1)。一些應(yīng)考生第一志愿填寫“上海青干院”,而其他本科院校被放在第二志愿中填寫。
有人把上海青干院崛起走紅的現(xiàn)象稱為“團(tuán)校現(xiàn)象”,并對(duì)這一奇異的現(xiàn)象表示困惑。上海青干院何以如此招人喜歡?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下,為什么有那么多的青年把自已的專長(zhǎng)和職業(yè)選擇定在這一院校上呢?
這樣,就有了我和上海青干院黨委書記、常務(wù)副院長(zhǎng)金國華的下述對(duì)話。
——能先介紹一下上海青干院的一般情況嗎?
好的。上海青干院復(fù)校于1978年,1980年開辦了共青團(tuán)和少先隊(duì)干部的大專班,可以說是全團(tuán)全日制大專班的始作俑者。現(xiàn)在我院每年招收400多名學(xué)生,全院有31個(gè)班,學(xué)制2~3年。十多年來,從這所院校走出的數(shù)千名團(tuán)隊(duì)干部工作在上海的各級(jí)團(tuán)的崗位上。現(xiàn)在,上海全日制中學(xué)的團(tuán)委書記十有八九是我院的畢業(yè)生,上海14個(gè)區(qū)中有15位團(tuán)區(qū)委正副書記是我院的畢業(yè)生。
——你好像很得意。是不是因?yàn)槟阍旱拿恳粋€(gè)畢業(yè)生就是一個(gè)活的廣告,這些畢業(yè)生在社會(huì)上構(gòu)成了你院的整體社會(huì)形象?
確實(shí)。作為教育者,其作品就是學(xué)生,沒有比看到學(xué)生成才,學(xué)生在社會(huì)上受歡迎更使我們高興的。這里我還可舉幾個(gè)具體的例子。我院的選送生畢業(yè)分配去向遵循“哪送回哪”的原則。可這幾年我院的畢業(yè)生求大于供,一次市屬某局向我院要一畢業(yè)生,我們把原來由黃浦區(qū)選送的一學(xué)生分到該局。黃浦區(qū)聞?dòng)嵄闾岢鲆蠓颠€該畢業(yè)生,還將此事告到市人大常委會(huì)。兩個(gè)區(qū)局級(jí)單位,為爭(zhēng)一個(gè)畢業(yè)生而將官司打到市人大,也可見我院畢業(yè)生在社會(huì)上走俏、搶手。還有前年我院分配給上海外國語大學(xué)兩名畢業(yè)生,其中一名留在該校團(tuán)委,一名現(xiàn)在上海外國語大學(xué)附中作團(tuán)委書記。我對(duì)上海外國語大學(xué)黨委書記說:“我們的畢業(yè)生年輕,應(yīng)該多鍛煉學(xué)習(xí),緩緩再提拔使用。”那位黨委書記打斷我的話說:“不,他們很出色,你今年還得給我分一個(gè)來。”再有我院有一個(gè)畢業(yè)生徐麟,21歲分到南匯縣作團(tuán)委書記,23歲任某鄉(xiāng)黨委書記,28歲作副縣長(zhǎng),現(xiàn)在是該縣常務(wù)副縣長(zhǎng)。這樣的學(xué)生在社會(huì)上能不搶手嗎?
——人們對(duì)所謂“團(tuán)校現(xiàn)象”感到困惑,大概是因?yàn)檫@幾年在市場(chǎng)意識(shí)和經(jīng)濟(jì)觀念不斷強(qiáng)化的背景下,人們對(duì)政治工作不甚感興趣了;居然會(huì)有越來越多的人對(duì)報(bào)考你們?cè)盒S信d趣。
我想先要說明的是,我院不是政治學(xué)院。我院由上海團(tuán)校改名為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xué)院,不僅是一個(gè)名字的變化。從專業(yè)設(shè)置來說,我院現(xiàn)設(shè)有青年思想教育、經(jīng)濟(jì)管理、公共關(guān)系、行政管理、文化宣傳藝術(shù)等專業(yè),今年還將增設(shè)財(cái)務(wù)會(huì)計(jì)、外貿(mào)等專業(yè)。我們?cè)O(shè)置這些專業(yè)是因?yàn)樯虾0l(fā)展戰(zhàn)略是要把上海建設(shè)成國際經(jīng)濟(jì)、金融、貿(mào)易中心,我們要為這一戰(zhàn)略發(fā)展培養(yǎng)青年管理干部人才。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培養(yǎng)單一的政治型人才,只能把辦學(xué)引入窄胡同。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我們培養(yǎng)人才的目標(biāo)、手段的確定,以及這幾年工作的成果,得益于團(tuán)上海市委提出的培養(yǎng)復(fù)合型團(tuán)干部的思路。
高進(jìn)優(yōu)出的“復(fù)合型團(tuán)干部”
團(tuán)上海市委是第一個(gè)提出“復(fù)合型團(tuán)干部”這一概念的,時(shí)間是1993年4月上海第10屆團(tuán)代會(huì)上。1993年11月全團(tuán)組織工作會(huì)議上,團(tuán)上海市委副書記薛潮對(duì)“復(fù)合型團(tuán)干部”詮釋:復(fù)合是指政治素質(zhì)與經(jīng)濟(jì)素質(zhì)的復(fù)合,基層工作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與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的管理能力的復(fù)合,不同崗位和不同經(jīng)歷的復(fù)合;培養(yǎng)復(fù)合型團(tuán)干部的目標(biāo)與要求是,政治素質(zhì)的全面性、工作能力的適應(yīng)性、知識(shí)結(jié)構(gòu)的合理性、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的豐富性。“復(fù)合型團(tuán)干部”理論的提出與闡述,令全團(tuán)耳目一新。
事隔一年多,團(tuán)上海市委在培養(yǎng)復(fù)合型團(tuán)干部上已形成并推出了“高進(jìn)優(yōu)出”的團(tuán)干部選拔、培養(yǎng)、輸送的機(jī)制。在選進(jìn)團(tuán)干部時(shí),堅(jiān)持“高學(xué)位、高素質(zhì)、高水平”的考核、錄用標(biāo)準(zhǔn);在團(tuán)干部的培養(yǎng)上保證其一定的在校學(xué)習(xí)、掛職鍛煉、本崗培養(yǎng)的機(jī)會(huì)和條件;在輸送上,由于對(duì)團(tuán)干部選進(jìn)時(shí)的高素質(zhì)和培養(yǎng)的高要求,也就能保證向黨和社會(huì)輸送優(yōu)秀的人才。團(tuán)上海市委組織部負(fù)責(zé)人介紹:近年來,團(tuán)上海市委已先后選送4批40名處以上團(tuán)干部到市委黨校“中青班”脫產(chǎn)培訓(xùn),安排了200名團(tuán)干部掛職鍛煉,委托同濟(jì)大學(xué)、上海青干院聯(lián)合開設(shè)了工商管理碩士研究生班(MBA)和管理工程研究生班,有數(shù)十名團(tuán)干部在這兩個(gè)班中學(xué)習(xí)。
自1990年以來,從上海團(tuán)干部行列中走出了這么一批干部:
上海虹口區(qū)區(qū)長(zhǎng)黃躍金,
上海盧灣區(qū)區(qū)長(zhǎng)韓正,
上海靜安區(qū)區(qū)委書記許德明,
上海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zhǎng)吳漢民,
上海浦東社會(huì)發(fā)展局局長(zhǎng)張學(xué)兵,
上海靜安區(qū)副區(qū)長(zhǎng)范希平,
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qū)開發(fā)公司總經(jīng)理高國富,
上海海洋石油服務(wù)公司副總經(jīng)理金建華,
上海新聞出版局副局長(zhǎng)王仲偉。
當(dāng)然,他們是上海許許多多團(tuán)干部中的一部分。
上海的團(tuán)干部或許是幸運(yùn)的,上海團(tuán)的工作有一個(gè)良好的社會(huì)環(huán)境。1994年,上海市委推出“三個(gè)一工程”,認(rèn)為培養(yǎng)跨世紀(jì)人才要有一個(gè)定量,這個(gè)量具體地表現(xiàn)是:要培養(yǎng)100個(gè)既懂政治、又懂經(jīng)濟(jì)的高層次的領(lǐng)導(dǎo)干部;培養(yǎng)1000個(gè)能夠在世界高科技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有發(fā)言權(quán)的學(xué)科帶頭人;培養(yǎng)10000個(gè)通曉國際經(jīng)濟(jì)、金融的管理人才。團(tuán)上海市委隨即把培養(yǎng)復(fù)合型團(tuán)干部的的工作定位在作為市委“三個(gè)一工程”的基礎(chǔ)工程,向市委輸送青年人才。因此,團(tuán)上海市委爭(zhēng)取到了每年兩次向市委推薦優(yōu)秀干部的機(jī)會(huì),并且使這一機(jī)會(huì)作為一種規(guī)定進(jìn)入機(jī)制和程序。我還了解到,在原團(tuán)上海市委副書記許德明任區(qū)委書記的上海靜安區(qū)團(tuán)委換屆時(shí),區(qū)委結(jié)合該區(qū)的“三個(gè)一工程”,從全區(qū)初選的1000名35歲以下的優(yōu)秀青年中復(fù)選了100人送入?yún)^(qū)委黨校學(xué)習(xí),之后從這100人中選了數(shù)人至區(qū)委組織部掛職考察,然后選定一位23歲的青年女黨員孫明麗作團(tuán)區(qū)委副書記的候選人。為配備一名區(qū)團(tuán)委副書記,區(qū)黨委如此下力氣,確實(shí)是團(tuán)組織的幸運(yùn)。
但同上海團(tuán)干部接觸,感受的卻不僅僅是幸運(yùn)。我曾采訪過團(tuán)上海市委前兩任書記黃躍金、韓正。他們都對(duì)我這樣表示:個(gè)人榮辱進(jìn)退是小事,現(xiàn)在舉手投足間常想到自己是從團(tuán)的崗位上走來的,因?yàn)槿藗冊(cè)u(píng)價(jià)我們時(shí)總會(huì)把我們和共青團(tuán)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的心中永遠(yuǎn)有一面團(tuán)旗。此話令我感動(dòng),不僅因?yàn)槲液退麄兌荚奂谀敲鎴F(tuán)旗下。
從團(tuán)干部入手帶動(dòng)整個(gè)團(tuán)的工作,不能不說團(tuán)上海市委的遠(yuǎn)見。團(tuán)上海市委書記鐘燕群在接受我的采訪時(shí)說:作為一次性生產(chǎn)資源(如原料、燃料等),上海是沒有優(yōu)勢(shì)的,但上海在人才資源上有歷史的優(yōu)勢(shì),上海今后的發(fā)展仍然需要依靠這個(gè)優(yōu)勢(shì)。因此,上海市委推出“三個(gè)一工程”,是抓住了上海發(fā)展之根本。共青團(tuán)抓好復(fù)合型干部的培養(yǎng),也可以說是順勢(shì)而上,抓住了機(jī)遇。
確實(shí),建國以來,上海的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的發(fā)展一直在全國處于領(lǐng)先地位。但在改革之初,上海卻落后了,上海的人才不斷地往廣州、深圳以及附近的江浙等地流動(dòng)。80年代還發(fā)生過兩件令上海人尷尬的事,一是上海甲肝大流行,那一陣沒人敢往上海出差,國人對(duì)上海避之唯恐不及。再一個(gè)是一次上海降大霧,因霧鎖黃浦江,輪渡停駛,輪渡口候渡者發(fā)生擁擠竟然傷亡上百人。那陣子上海多么期盼、希冀著騰飛。今天,歷史又一次把騰飛的機(jī)遇交給了上海人民。歷史也公平地把機(jī)遇又一次交給了上海和全國的共青團(tu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