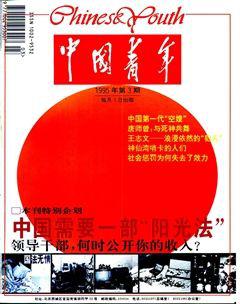南方情結
黃敏堅
人們總喜歡歸類,萬物都被歸入各自的類別,人本身也不例外。于是很自然的,中大學生被劃入了南方大學生之列,盡管我們也是來自天南地北。
南方(更確切地說應該是五嶺之南)似乎是個光怪陸離的復合體,因為它的開放,它的包容,造就了它的魅力,也造就了人們對它的毀譽。有人說喧囂、浮躁是它的情緒,媚俗、時尚是它的偏好;也有人說求實、進取是它的精神,靈活是它的個性。但隨你怎么說,南方還是照樣存在與發展。
可是嶺南最高學府里的學子們卻不在乎別人評說他們的功利與淺薄,更不滿足于別人所稱道的務實與獨立。曾幾何時,提起中山大學,人們首先聯想到南方,然后聯想到逃課打工賺錢的學生,再聯想到雖實用但缺乏理論功底的學術水平,最后得出結論:中大畢竟是南方大學。一個“南方”便把中大學生的不足給輕描淡寫地原諒了。
然而我們無法原諒自己。曾經瀟瀟灑灑、風風光光的行為真那么值得自豪嗎?我們不想再說南方的世界實在太精彩,象牙塔外的誘惑實在難以抗拒;我們也厭倦了去說,打工賺錢既為了獨立,也為了獲取實踐經驗;我們甚至羞于說,南方經濟的繁榮還有我們的一份貢獻呢。
因為,南方經濟浪潮并未使我們建立起獨樹一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嶺南文化的倡導也沒能讓我們南方文學突破風花雪月、通俗娛樂的層面;而當化學系研究生去做期貨經紀,生物系學生去做推銷,數學系學生兼職做秘書時,我們感到了一種委屈,一種困惑,還有一種壓力。
于是,我們陷入思考。即使思考還不多,還不深,但至少我們已經開始,開始用理性去批駁平庸,用吶喊去沖破麻木,用實際行動去表白自己。看看圖書館內求索的身影,看看教學樓里爆滿的講座,看看學生宿舍熱烈的文化沙龍,看看惺亭月色下擁擠的英語角,還有寫在各類學生刊物上的那一張張誠懇的面孔和一顆顆火熱的心。走出校門的依舊源源不斷,但更多的同學又從外面的世界回到了象牙塔里,考研之風甚盛。我們不想為自己的轉變而歡呼,因為路還很長,只有中山先生留下的校訓在始終鞭策著我們——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據說中大有90%的學生和成果輻射在廣東地區,校長曾漢民也說過,中大首先要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作出貢獻。看來我們注定是要屬于南方的,只為了不辜負這一段南方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