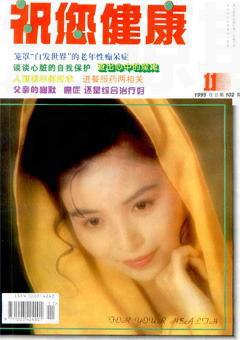結(jié)緣在西麗
李克因
我的書架上插著一本600頁的厚書,是長(zhǎng)篇小說《三舍本傳》;案頭有一本也是600頁的厚書,是文學(xué)理論集《藝術(shù)·人·真誠(chéng)》。得到這兩部大書,應(yīng)該講點(diǎn)緣法和雅趣。而我撫著它們,就立刻找回半年前那難得的歡樂。
深圳西麗湖是個(gè)初具規(guī)模的旅游區(qū)。中華文學(xué)基金會(huì)在這里設(shè)了個(gè)休養(yǎng)所,分批安排中國(guó)作協(xié)會(huì)員前來度假。我有幸獲得一個(gè)機(jī)會(huì),半個(gè)月中,觀覽了這個(gè)特區(qū)的“特”處。這對(duì)初來的人自然具有吸引力;而我之得趣更在游樂之外。
這批安排了24人,正好三桌之?dāng)?shù)。入所第一餐,我與陳登科同桌鄰座。他來得早,已開始展示他那閑適的風(fēng)貌。他抓著一只大約盛著三兩酒的玻璃杯,隨飲隨侃,海闊天空。我與他在1982年有過一次晤會(huì),提起往事,格外親切。他把杯子遞給我,說:“老壘(李),干杯!”豪爽灑脫之氣不減當(dāng)年。
陳登科的豪飲在文學(xué)界是出了名的,鬧起酒來大有“拚命三郎”氣概,動(dòng)輒“干杯”。此時(shí)的所謂“干”不過是“意思意思”,并非要?jiǎng)诱娓瘛N业牧侩m然有限,卻也是個(gè)喜歡“弄一點(diǎn)”的好酒之徒。有他開例在先,我也放肆起來,到小賣部買了幾瓶酒,每餐帶上2兩,和他對(duì)飲對(duì)侃。瀟灑一回。大概人都有個(gè)“趨熟性”,第一次坐定,此后十之八九還要奔這個(gè)地方,座次就此形成。
第三天下午,我去餐廳稍早一些,正坐等人齊,忽然一陣橐橐皮鞋聲,一男一女徑奔我桌而來,老先生隨即在我旁邊坐下,“占”了陳登科的位子。請(qǐng)問大名,原來是上海錢谷融教授夫婦,他邊揩汗邊說:“挨宰了。從飛機(jī)場(chǎng)打的到這里,竟然要我一百五。”話剛落音,陳登科抓著杯子來到,一看桌上已經(jīng)滿員,便笑呵呵轉(zhuǎn)到另外一桌。座席最后確定,再無改變。
一條道上的朋友。很容易熟悉。從此,我稱陳登科為“登老”,錢谷融為“谷老”。因?yàn)樗麄兌急任夷觊L(zhǎng)。而也從此,谷老極可能受到我的影響,每餐也帶酒來,淺淺一杯底。他說:“我平素也喜歡喝一點(diǎn),為的是休息,也可以多吃點(diǎn)菜,多說點(diǎn)話。”論年齡,我排行第三。文人不拘形跡。三個(gè)老頭兒頻頻喝酒,并無人稱怪。而登老一人獨(dú)酌,未免寂寞。常常踱過來,舉杯向我:“老壘,干杯!”
這二老都是四十年代初就開筆的文學(xué)界耆宿。都是中國(guó)作協(xié)理事。大同之中也有大異。谷老是文學(xué)院畢業(yè)的理論家,長(zhǎng)期在大學(xué)執(zhí)教;登老是“社會(huì)大學(xué)”出身,中國(guó)文講所首期學(xué)員,小說作家,長(zhǎng)期主持省作協(xié)工作。谷老身著三件頭西裝,斜戴法蘭西扁帽,十分修整。一派精干的教授風(fēng)范;登老則是著一件肥大的休閑衫,趿一雙松松的懶漢鞋,大似閑云野鶴。谷老每天都修得面兒光光,精神抖擻;登老則蓄著一部其長(zhǎng)及胸的大胡子,南極仙翁般超凡脫俗。
我不知道他倆過去有無交往,想來未必。大學(xué)、作協(xié)畢竟隔了個(gè)行。現(xiàn)在機(jī)遇把他們扯到了一起。那天,登老踱過來,舉杯向谷老致意。杯子叮的一響,兩位都笑得臉上開了花。過了兩天,登老又踅過來,正要和我“干杯”,谷老已站起來:“陳老,今天該我敬你了。”登老忙說:“不,錢老,還是我敬你。”互相一敬。便序起齒來。登老說出生于1919年農(nóng)歷3月,谷老馬上說:“你長(zhǎng)我8個(gè)月,是老大哥。”
一天正逢節(jié)日,晚上加菜備酒,大家興致都很高。登老自然不會(huì)放過這個(gè)機(jī)會(huì),逐桌逐人碰杯。“碰”到谷老處,兩人互相問起“貴處”。登老說;“我是蘇北漣水人,在安徽干了45年。”谷老樂了:“巧啦,我原籍蘇南武進(jìn),在上海干了45年。”
這一敘,真敘出了一個(gè)具有戲劇性的巧合。兩位都是一直在外地工作的江蘇人,而我這個(gè)太行山人卻在異鄉(xiāng)江蘇干了45年。如今在嶺南西麗相會(huì),又是全所僅有的餐餐飲酒的三個(gè)人。豈非天緣湊巧?我借著酒意,口發(fā)狂言,說如有可能,定要寫一篇“二老三碰杯”以志盛,全場(chǎng)鼓掌贊成。
當(dāng)然這都是閑話閑筆。文人相聚。“論道”更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我們論得很投契,感情日深。那天晚飯后我在園中散步回來,陳登科先生已在門口廊下等著,隨即把一本厚書雙手遞給我,我連忙恭謹(jǐn)接過。這就是他新近全部殺青的百萬字長(zhǎng)篇的第一卷:《三舍本傳》,扉頁已經(jīng)題字:克因兄,敬請(qǐng)教正。
錢谷融先生則是以1957年初發(fā)表《論“文學(xué)是人學(xué)”》名于世,為此他受過長(zhǎng)期的嚴(yán)酷批判。嗣后他一直不改初衷,以嚴(yán)肅、科學(xué)的治學(xué)態(tài)度,繼續(xù)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diǎn)。而經(jīng)受了時(shí)間檢驗(yàn)。此論已廣為人們接受。文學(xué)不以人為考察、研究對(duì)象,能算什么文學(xué)呢?他說,自己寫的東西其實(shí)不算多,已編了個(gè)自選集,交給出版社。他提到這些,只是“輕描淡寫”,若無其事。不意4個(gè)月后,這部50萬字、集其大半生理論研究精粹的《藝術(shù)·人·真誠(chéng)》的大書,竟翩然飛到我的案頭,扉頁上用剛勁的筆觸寫著:克因大兄正。
我非常慚愧。倒不完全因?yàn)槭艿剿麄兇蟠筮^份的尊重;更由于我到西麗湖去只是為了“瀟灑走一回”,而他們卻是在這個(gè)富于情趣的環(huán)境中,享受生活賜予的同時(shí)。還在以嚴(yán)肅的態(tài)度思考和著述,為社會(huì)做著貢獻(xiàn)。我分明記得,在他們的居室里,桌上都展放著書籍和稿紙。真是老而彌壯!
情趣本來寄寓著真誠(chéng);他們更在真誠(chéng)中充分展示著對(duì)生活的情趣。僅從這一點(diǎn)來說,就足獲我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