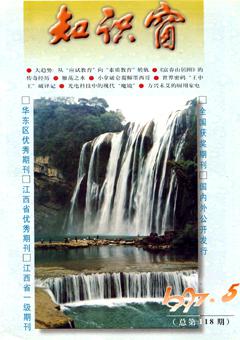柳公權“筆諫”唐穆宗等
陸茂清等
“柳骨”,是人們對唐代書法家柳公權獨特書法藝術的高度評價。據史書記載,柳公權常全神貫注看屠戶剔骨,又用心觀察驚馬、奔鹿、斗牛,將動物的骨骼結構及強勁姿態融注于筆劃之間,其字勁緊嚴正,骨力遒健,故謂之“柳骨”。
人如其字,這位書法大家秉性耿直,剛直不阿,頗如其峻峭諍骨的書風,故人們愛“柳骨”,既是愛他的字,又是愛他的高尚人品。
柳公權得中進士后,初在地方上任小官。一次,唐穆宗出京游覽,至一廟宇,見到了寺壁上柳公權的題詞,對他的筆法贊不絕口,連稱“妙哉好字!”嗣后不久,柳公權進京朝見皇帝,穆宗高興地說:“朕曾在寺中見過卿的墨跡,堪稱一流,就留在京中任職便了。”于是封為右拾遺侍書學士,后又提升為翰林學士。
封建帝王中,穆宗當排在昏君之列,生活放縱,癡迷聲色。一日早朝,穆宗心血來潮,對柳公權說:“朕近時正在練字,卻總感不得要領。卿對此造詣較深,可否作經驗之談?告知聯如何運筆。”
柳公權想了想說:“以小臣的體會,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心不正則筆也難正。”他講的聽上去是運筆之法,實則乃規勸穆宗端正品行心術,做一個明君。
穆宗并不是呆子,自然聽出柳公權的弦外之音,臉色由晴轉陰。群臣見狀,暗暗擔心,無不為柳公權捏了一把汗。柳公權卻神態如常,毫無惶恐之色。
出乎意料,唐穆宗揮揮手:“朕知道如何運筆了,卿且下去吧。”他原本是要懲柳公權“訕諷主上”之罪的,只是考慮到,柳公權講的是運筆的方法,又是答自己所問,罪名難加,更出于愛柳公權的才華,終于使柳得以幸免。
這就是流傳千余年的柳公權“筆諫”的一段佳話。
其實,柳公權犯顏直諫不止一次。
唐敬宗也是個胸無大志的平庸之君,無所作為卻喜歡臣下頌揚。一日與群臣談論漢文帝如何躬行節儉時,高舉雙袖說:“朕這件衣衫,已漿洗過三次了。”
眾臣立即趨聲附臺,七嘴八舌,大加逢迎,一片贊美之聲。內中唯獨柳公權一言不發,敬宗瞥見了,問道:“卿以為朕此舉如何呀?”
柳公權不假思索地說:“臣以為,攬賢才,摒不肖,明賞罰,開言路,為天下萬民興利除弊,乃英明之主日思夜慮之安邦定國大計,至于穿舊衣,雖也不失為好事,只不過小事一樁,終難上國史。”
敬宗聞言,頓時臉紅耳赤,卻又不便發作。
(責任編輯/楊劍鳴)
謝疊山的“卜卦硯”
徐弋生
南宋愛國詩人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弋陽人,寶祏四年與文天祥同科中進士。自抗元失敗后,便隱姓埋名,從江西到福建建陽,以寫字賣卜教書為生,棲身于城南朝天橋的橋亭之中。后元朝迫其出仕,地方官把他強行送往大都(今北京),遂絕食而死。
謝疊山生前有一方石硯,名為“卜卦硯”系有名的覦硯,又稱龍尾硯。此硯長九寸七分,寬五寸元分,厚九分,硯額篆有“橋亭卜卦硯”五字,正面左右還有草書“此吾石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似當年采薇不食,宋義賢也。”硯背右有“宋謝待郎硯,明程文海題”;左有“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為先生祠,揭地得之,閩后學趙元。”
謝疊山當年所居的朝天橋,系宋紹興年間所建,石址木梁,上砌以磚,覆屋七十三間,橫跨雙溪之上,首亭有橋房四間。后來他被逼北上,行前將此卜卦硯埋于地下。明永樂丙申年七月,建陽遭受特大洪水,朝天橋橋亭、驛舍均遭洪水沖毀,洪水退去之后,建陽縣知縣邵某出于對謝疊山的崇敬,于橋頭驛站前建起了疊山祠,以事祭祀。“卜卦硯”就是當時掘地建祠期間被出土的。
據《瞭望》雜志前些年介紹說,建國初期,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初梨同志在北京市偶然購得了謝疊山卜卦硯。消息傳開之后,有一日本人曾想出一萬美元將此硯購去,但遭到李初梨的拒絕。八十年代,李初梨同志離休轉回四川定居后,將此硯以及其他文物一起捐獻給了重慶市博物館,得到了國家的良好保護。
(責任編輯/楊劍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