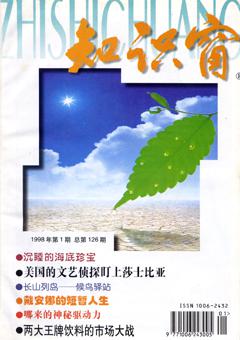美國的文藝偵探盯上莎士比亞
林一民
挖墓找鐵證
1997年3月1日,在英國斯加倍里教堂墓園內的一座墳墓前,十幾個人神色嚴肅地站立著,教堂鐘樓的大鐘鳴響十下后,三名石工拿起鍬鎬,開始動土挖掘。墓園外擁擠著三百多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六名警官站在他們的前面,防備他們在最關鍵的時刻沖向這座即將開掘出來的數百年前的古墓。主持挖墓的并不是墓主的后代,也不是英國人,而是一個美國人,一位頗有名氣的美國戲劇評論家卡爾溫·霍夫曼。不過此時,他不是在評論戲劇,而是在做一項文藝偵探工作。這座古墓的發掘,將要證明他的偵探成果。一旦如愿,那么有一段人人皆知的歷史就要重寫,他就會成為世界最著名的人物。那三百多名記者正瞪大的眼睛,足以說明這一點。
美國是一個無奇不有的國家,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事情層出不窮,專門從事文藝偵探職業的也不乏其人。霍夫曼就干上了這一行,他的第一項業務就是盯上了數百年來倍受人們頂禮膜拜的英國大戲劇家莎士比亞。他發現,莎士比亞有欺世盜名之嫌,深受人們喜愛的著名悲劇《哈姆雷特》等一批作品,并非莎氏所作,而是同時代別的人的作品,或者是當時的人借他的名字發表的。
偵探的證據
霍夫曼自認為找到了有力的證據:
莎士比亞出身低微,父親是一個不善經營的農場主,他本人文化程度不高,只進過幾年當地的文法學校,13歲便輟學在家。失學后,可能是在一家屠宰場殺豬,也可能是在當地一所小學當老師。20多歲后,到倫敦一家戲院打工,先是給紳士們看看馬匹,后來才當上一位跑龍套的演員。總之,莎士比亞的一生在仕途上從沒有輝煌騰達過,也從沒有出入過宮廷。他既沒有叱咤風云的經歷,也沒有與皇親國戚深厚交往,只不過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戲子、伶人而已。然而,莎士比亞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歷史劇和悲劇,寫的大都是帝王將相的悲歡離臺,以及英國歷史上最輝煌、豪華的場面。而他不可能有那么豐富的學識,不可能了解到那么多豪華宮廷與貴族之間的事情,也不可能描寫出那么生動、細致、深刻的生活和心理。
更可疑的是,莎士比亞那么多的作品為什么找不到原稿?霍夫曼曾耗時近20年,找遍英國各地,翻查、搜集古籍,只要是莎士比亞作品的片紙只字,都在他的偵探之列。20年的辛苦,只找到了很難辨認得清的所謂莎士比亞的三個簽字和合作劇《湯瑪士·摩爾》一劇中的三頁原稿。那么莎士比亞37部戲劇的原稿都到哪里去了呢?有兩種流行的說法:一是說,1613年格洛伯戲院發生火災,莎劇原稿在那次大火中化為灰燼。霍夫曼認為這是無稽之談,那時的莎士比亞已經告老還鄉隱居,不可能不把原稿帶走。二是說,原稿僅是腳本,經過多人修改過,已經改得面目全非了,可能莎士比亞認為沒有保存的價值,故未加保留。霍夫曼當然不會同意這種說法。
霍夫曼猜想
那么,莎士比亞的那些杰出戲劇作品的作者是誰呢?霍夫曼認為作品大都是莎士比亞的同時代人馬婁所作。馬婁是英國“大學才子派”中的杰出代表,也是英國著名的劇作家。他的傳世之作有《福斯塔斯》、《馬爾泰的猶太人》等。霍夫曼發現:馬婁出生于1564年,和莎士比亞同齡,劍橋大學出身,在校時做過伊麗莎白女王情報局長福蘭西斯·華興漢的私人秘書,后來成為了無神論者,并埋頭寫作戲劇,成為了劇作家。1593年,馬婁因宮廷政治陰謀,在倫敦郊外的一家酒館被刺客殺害。但霍夫曼卻從一批新的史料中認為被刺客殺害的并不是馬婁,而是充當馬婁替身的一個乞丐。馬婁因此亡命西班牙,并繼續寫劇本。后來,他潛回英國,住在情報局長華興漢爵士的莊園里,仍然埋頭于劇作。霍夫曼還偵探到,馬婁將一部分作品交給了情報局長的堂弟托瑪斯·華興漢,請他交給與他有交情的莎士比亞,并用莎士比亞的名義上演。
霍夫曼認為還有一件證據是很有意義的。1953年首次發現了馬婁的肖像畫,這幀肖像畫被發現在他1618年出版的劇本《福斯塔斯》封面畫上。令人驚訝的是,這幅肖像與1623年刊行的莎士比亞全集的封面肖像,以及莎士比亞在家鄉斯特拉脫弗鎮受洗禮的那座教堂保存的莎氏肖像,都十分相像。因此,霍夫曼認為,莎士比亞劇本的作者就是馬婁。霍夫曼甚至勾勒出馬婁寫作劇本的次序:他在完成《福斯塔斯》、《馬爾泰的猶太人》之后,于流亡時期寫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仲夏夜之夢>、《亨利四世》、《哈姆雷特》、《奧賽羅》、《麥克白》、《李爾王》,潛回英國后又改寫了《暴風雨》等。照此說法,莎士比亞的劇作,幾乎盡屬于馬婁。
英國人態度
霍夫曼的這些偵查探究,令人誠服的證據不多,多的是推測,并拿不出鐵證。為了讓世人信服,霍夫曼決定進行挖掘,要挖出原稿來。他猜想:馬婁所作的莎士比亞戲劇原稿,一定裝在一只鉛箱內作為陪葬的。這只箱子一定在馬婁的監護人華興漢爵士的墳墓之中。掘開華興漢的墳墓,鐵證就可以出現。但是,人家的墳墓不是任何人可以隨便挖的,必須有合法的身份,并辦理必要的手續。為此,霍夫曼千方百計找到并說服了華興漢爵士的后裔唐生德少校,請他出面申請教會許可挖掘他的祖墳。還好,唐生德少校終于同意了他的要求,教會法庭也終于批準了唐生德的請求。一座安靜了三百多年的墳墓被挖開了。
美國的文藝偵探刨開華興漢的墳墓,動機在于找出莎士比亞的“假冒”證據,這無疑是要埋葬英國人傳世的榮譽。“英國人寧可丟掉東印度群島,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亞。”這便是莎士比亞在英國人心中的地位,莎士比亞已經成為英國人文化素養中的一部分。他們的做法,與美國人背道而馳,總是孜孜不倦地證明:某個劇本是莎士比亞在世時就已經上演;某個劇本的底稿上有莎士比亞的親筆簽字,或親筆修改過的筆跡,等等。如果霍夫曼跑到莎士比亞的故鄉斯特拉脫弗鎮去說莎士比亞是假的,他準會遭到圍攻,甚至碰上為莎士比亞而拼命的人。這個鎮在每年的4月26日莎士比亞的紀念只,都要舉行大型的紀念活動,接連幾天,熱鬧非凡。他們邀請世界各地的著名學者參加莎士比亞學術討論會,舉行莎士比亞戲劇匯演,組織盛大慶典游行和展覽。他們是靠啃莎士比亞的老骨頭而發達起來的。莎士比亞已經成了他們的無煙工業、旅游資源。
霍夫曼的偵探行為終于引起了世人的關注,三百多位記者和攝影師正是為此而來的。挖墓工人挖出來的每一鍬土,都令他們增七分好奇和三分喜悅或三分憂愁。
古墓掘開了
古墓被掘開了,但是除了墓中的磚地上有一大堆沙土外,既無遺骸,也無他物,更不要說有什么裝原稿的鉛箱子。站在一旁的唐生德少校先是大失所望,想不到自己的祖墳竟是一堆沙上,然后是無可奈何和憤怒。霍夫曼則先是尷尬,繼而堅持說道:“我不認為這次沒有找到就是我的說法不對。”
看來,這位文藝偵探真的是要盯住莎士比亞不放了,是不服輸,還是拉不下面子?那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但真能盯出個什么合乎霍夫曼猜想的結果來,恐怕并不那么容易。其實,就霍夫曼所占有的證據和他自己的推論來看,要懷疑莎士比亞對那些戲劇作品的著作權,從而推倒莎翁,顯然是不夠慎重的。有不少作家雖然沒有某一方面的親身經歷,但也能根據一些傳說或歷史資料寫出偉大的作品。荷馬瞎老頭,沒有親身經歷過特洛亞戰爭,但他搜集流傳于小亞細亞地區的傳說,創作出了不朽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埃斯庫斯沒有登上奧林匹斯神山,但他寫出了《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彌爾頓更不可能親身經歷《圣經》的境地,但創作了《失樂園》、《復樂園》;至于列夫·托爾斯泰,沒有見過拿破侖和亞歷山大皇帝,然而他在《戰爭與和平》中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這兩位歷史人物相會的歷史場面。由此可見,以莎士比亞的出身和經歷為由,否定他寫過那些杰出的戲劇,證據顯然不充分。
美國的偵探至今也沒能損去莎士比亞的一分一毫光輝,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人們欣賞莎士比亞,主要是欣賞他的作品,而不是他這個人。道理很簡單,莎士比亞的偉大,主要是因為他的那些戲劇作品具有真善美的價值,具有震撼人心的審美效果。
(責任編輯/陳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