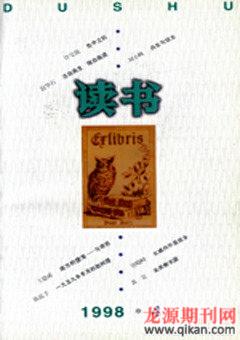“別”意“新”詞各勝場(chǎng)
虞友謙
當(dāng)我們閱讀歷史傳記來(lái)晤對(duì)古人時(shí),固然可以獲取知識(shí),求其對(duì)當(dāng)時(shí)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軍事等情況的了解,也可以用觀劇的立場(chǎng)滿足自身對(duì)審美心境的需求;但我們更高的期望則是達(dá)到一種真切的體驗(yàn),與古人作“神游冥會(huì)”的交往,在豐富深沉的歷史感受中,實(shí)現(xiàn)高層次的人文關(guān)懷,最終充實(shí)提升我們自己的人生境界。我想,能夠滿足這種要求的歷史傳記,應(yīng)屬于上乘之作了。
《柳如是新傳》正是如此。關(guān)于柳如是的傳記,近年來(lái)在出版界十分醒目,但就近年已出版數(shù)種而言,總的感覺(jué)是眼界較窄,大多未能認(rèn)真研讀史料,故缺乏對(duì)傳主人格精神的深刻理解,甚至有個(gè)別作品渲染低級(jí)趣味,不負(fù)責(zé)任地厚誣古人,這與《新傳》實(shí)不可同日而語(yǔ)。不過(guò)我個(gè)人認(rèn)為《新傳》的真正價(jià)值并不體現(xiàn)在與這些作品的比較上,而是表現(xiàn)在它對(duì)三十余年前一代宗師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的把握、認(rèn)同、繼承、演繹與延伸上。而正是在這一點(diǎn)上,可以使卞敏先生這一作品超越一般通俗文史傳記的局限而躋身于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術(shù)著作之林。
首先,堅(jiān)持了陳先生作為學(xué)者的文化價(jià)值觀念與人生理想。陳先生一生都推崇“獨(dú)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時(shí)他又自認(rèn)是一個(gè)“被舊文化所化”的文化人,這兩者決定了他在文化轉(zhuǎn)折的關(guān)頭所表現(xiàn)的文化傳承的歷史使命感。中國(guó)歷史上王朝遞嬗,動(dòng)亂頻仍,但中國(guó)文化經(jīng)歷五千年而延續(xù)不墜,正有賴于一批批“不合時(shí)宜”的文化人在轉(zhuǎn)折時(shí)期所表現(xiàn)的文化擔(dān)當(dāng)?shù)挠職狻O啾戎拢恍┡垠丝N紳、達(dá)官顯貴則顯得十分渺小。陳先生在這方面特別看重柳如是“巾帽不讓須眉”的見(jiàn)識(shí)與氣質(zhì),對(duì)之大加贊賞。《新傳》緊緊把握了這一精神,對(duì)此有極深的體會(huì)。我們除在字里行間有所領(lǐng)略之外,作者在后記中也直接作了說(shuō)明。
第二,繼承運(yùn)用了陳先生史學(xué)研究的方法。陳先生于歷史學(xué)術(shù)之求真實(shí),有其獨(dú)到之處。首先是小中見(jiàn)大,從極細(xì)微處發(fā)現(xiàn)極有價(jià)值的史料,經(jīng)細(xì)密推衍,得出至確不易之結(jié)論,猶如醫(yī)學(xué)上之顯微外科與電子診斷。先生最拿手的“以詩(shī)證史”即是如此。另外,陳先生還提倡對(duì)古人要作“神游冥想”之“真了解”。這實(shí)在是一個(gè)偉大的見(jiàn)解。我們承認(rèn)歷史的動(dòng)因在于物質(zhì)經(jīng)濟(jì)層面,但這僅是從根本上而言,而任何具體的歷史過(guò)程卻無(wú)不有人的“心”與“意”主宰于其間,盡管這心與意也是由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存在的種種因素所決定的。離開(kāi)了對(duì)古人心意的了解,必不能求得真實(shí)。而按照規(guī)律去編纂史料,所得的只是沒(méi)有真實(shí)內(nèi)容的空軀殼,最終只能是糊涂賬而已。陳先生的這種見(jiàn)解對(duì)當(dāng)時(shí)“以論帶史”所造成的空疏缺漏,雖有極大的警醒作用,但卻沒(méi)有多少人理睬。《新傳》可謂是忠實(shí)地繼承了陳先生的史學(xué)方法,這對(duì)倡導(dǎo)弘揚(yáng)先生的研究方法與治學(xué)風(fēng)格是有益的。
第三,基本使用了陳先生《別傳》的研究成果而又有所延伸進(jìn)展。《新傳》行文,通篇以詩(shī)作貫穿其間,猶如一串珍珠項(xiàng)練,頗具光彩。對(duì)許多細(xì)微情節(jié),均能娓娓道來(lái),顯得游刃有余,略無(wú)疑滯,毫不使人產(chǎn)生夸誕之感。這是充分使用了陳先生的研究成果的原因。可以說(shuō)有了陳先生十年艱苦考證發(fā)覆之功,才有《新傳》今日輕松流暢之效。但中國(guó)歷史資料之“汗牛充棟”近乎殘酷,以陳先生這樣一位不世出的史學(xué)大師,窮十年之功,運(yùn)用了一千余種資料以治一個(gè)專題,應(yīng)該是十分完備了。但后人站在巨人的肩上,總是能看到更多更遠(yuǎn)。《新傳》所引柳如是《湖上草》、《尺牘》兩種史料的刻本均為陳先生所“未得親見(jiàn)”,這樣《新傳》在這一方面自然是有所延伸與進(jìn)展。
我想,讀者在閱讀《新傳》的基礎(chǔ)上,如有機(jī)會(huì)再讀《別傳》,或?qū)烧邔?duì)照閱讀,《別傳》與《新傳》,各擅勝場(chǎng),一定會(huì)更有興味的。
(《柳如是新傳》,卞敏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1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