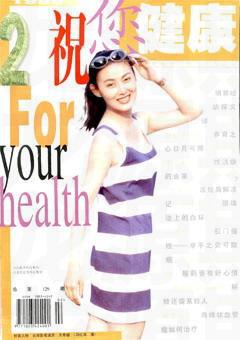長壽之方
長壽是世世代代人的追求;我平生見到的第一位長壽者,要算我的外公。他是清朝末年的秀才,比魯迅先生還年長3歲,也曾進過洋學堂和負笈東瀛的。老人子女雖多,但云散四方,有的遠在臺灣和美國,身邊只有一個患病的老小隨他生活,晚景凄涼可想而知。我與外公接觸,是在60年代初,已經八旬掛零的他,銀髯拂胸,精神矍鑠。那時我剛從揚州來南京讀書不久,常代表母親來看望老人,臨走時他總是叮囑我:你母親也是六十開外的人了,出門該有人陪伴,走路要小心些呀!
老人說這話是不包括他自己的。因為年近90時他還獨自走過建康路去三星池浴室洗澡,他走路很慢,不大用拐杖,腰板卻挺得很直。他是一位飽讀詩書者,家中有很多藏書,晚年寂寞中亦以吟詩聯句為消遣。我常從他口中聽到“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八個字,似乎是他始終遵循的人生信條;他性格平和,達觀知命,在逆境中不消沉,并能自尋樂趣。寧靜致遠,成了他一直堅持到漫長生命盡頭的一種“生活方式”。這在他留下的一部詩稿中能夠得到證明。六朝古都的四時景物,對家鄉和親人的回憶與懷念,常常縈繞在他的心頭,牽扯著他的情思,伴他度過艱難時光。要不是發生“文化大革命”,老人以92歲高齡病故于一次“抄家”以后,百歲之期是完全有望的。
比他幸運的,是我母親。她是家中長女,從小在蘇北農村長大,后師從著名教育家陳鶴琴先生,抗戰中在家鄉參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從事幼教工作。她的人生經歷曲折坎坷,因為我的父親44歲病故,中年守寡的母親雙肩挑起生活重擔,將3個子女拉扯成人,自己的工作也非常出色。她是一個精力充沛、勤勞執著的女性,“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磨難時已近古稀之年,但她樂觀、積極地對待一切,并敢于同逆境抗爭;撥亂反正后,她終于有了一個幸福安康的晚年,今年已94歲。80歲那年,她開始執筆寫回憶錄,歷四度寒暑,積20萬字,在她九秩華誕時出版成書,名《燭光》,一時傳為佳話。她是揚州地區離休干部中年事最高的女同志,兩年前她不慎摔斷右腿,因年老缺鈣,牽引接骨未能成功,但她堅持鍛煉。至今已能摸著床沿挪動。她的生命力之強,思維敏捷,談吐活躍,常常令初識者驚嘆不已。
如果說我的兩位長壽前輩,得力于他們受過教育、有比較自覺的養生之法的話,另一位現已活到100歲的老壽星。就是我見到并熟悉的“自學成才”的人中之瑞了。她是個家庭婦女,我小學同窗吳君的母親,我們從小就在她面前玩耍,整整一世紀從這位1896年出生的人的腳下悄悄溜走了。前不久我去外地吳君家看望她,多年未見的老伯母變化并不大,臉色紅潤,皺紋很少,似乎光陰之箭在那里留不下什么刻痕。朋友告訴我,她的長壽之秘,離不開她的平和與仁愛,一生行善,從不動怒。吳君在11個兒女中排行第八,侍奉高堂無微不至,常常“陪睡”在老母側畔,聽她講說陳年舊事或告之以當今新聞,甚至耳鬢廝磨、與老人逗趣,所謂“老萊娛親”,我這位可敬的朋友真正做到了,難怪當地電視臺為他家拍了個專題片<百歲老人和她的孝順兒子)。因此我想,家庭成員的支撐、晚輩的孝心,同樣是長壽的基石,對日趨老齡化的社會來說,這也是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話題。
當然作為生命個體的人,如何把握好生命的節律、駕馭好與自然協調的健康之舵,關鍵還在于自己。在這篇《長壽之方》的文章結尾,我想引用我母親在她的回憶錄《燭光》中寫下的“八十年來的生活體會”也許是切題的,但愿能對樂于探求此道的中、老年朋友們有所裨益。下面就是她的經驗之談:
一、人必須要有正確的人生觀,胸襟開闊,思想開朗。人與人相處,不計較小問題,求大同存小異,俗話說“免淘氣。”
二、要活動,經常出外走走,日常做些力所能及的體力勞動,如家務活計,手勤腳快,從不閑著,幾十年如一日。
三、生活有規律,起居有常,每天早晨六時起身,養成習慣不貪睡,寒冬酷暑一個樣;飲食有節制,定時定量,少食多餐,多素食。
四、對病的看法和辦法:主張不吃藥、少吃藥,預防為主,以活動經絡求健康,依靠“內因”抗疾病。生命在于運動,哪一天不動也就“停擺”了。
【作者簡介】
馮亦同詩人、評論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作家協會理事、南京作協副主席兼秘書長。著有詩集《相思豆莢》《男兒島》,詩評集《人生第五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