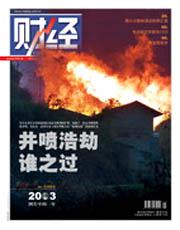“雪擁藍關”之時
舒 立
世事難如人意。華盛頓時間9月28日晚,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提前結束原計劃兩天的新一輪中美WTO談判飛返北京,中國入關的“窗口機會”再次關闔。盡管中美雙方的官方代表仍表示不會放棄在11月西雅圖會議前使中國加入WTO的努力,但多數冷靜的分析家已經得出結論:中國按計劃在年內、其實也就是在本世紀內入關的希望已十分渺茫。
我們當然還在期待奇跡發生,但我們也得正視現實:
——中美雙方在此次談判之后,根本沒有確定下一次談判的時間和地點,而美國國會將在11月間休會。由于中美雙邊協議牽涉到中國的永久性最惠國待遇,必須獲得國會通過,因此如果談判不在10月初達成協議,甚至無法被列入國會議程。
——中國WTO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沒有參加在華府的新一輪談判,但他在華接受CNN采訪時指出,美國于4月間公布的中方加入WTO有關承諾的17頁文件中,至少有10至15處錯誤(mistakes),惟有美國為此進行澄清,才有希望達成協議。沒有任何消息表明美方已經或準備就17頁文件進行“澄清”,可知雙方的立場還有相當距離。
——無論巴爾舍夫斯基在此次談判后在國會聽證會上的表態,還是美國此時的愈加逼近明年總統大選的政治氣氛,都使人感到白宮目前對中國入關雖然態度積極,但迫于政治壓力,在未來談判中進一步妥協的可能性極小。而美國的必要的、具有實質意義的讓步,特別是在紡織品配額、反傾銷等關鍵問題上的讓步,無疑是中美最終簽署雙邊協議的前提。
……
當然,中國能否入關目前主要是國際政治問題,但因為政治本身就具有太多的牽連,討價還價的談判一定需要時間。而爭取年內入關的時間已經過于緊迫,幾乎沒有回旋余地。
從1986年算起,中國為入關已經奮斗了13年,在今年年內更是一波三折,崎嶇多變。回過頭來看,以往十多年內中國至少有三次曾經看到了入關的曙光。第一次是在80年代后期,第二次是在1994年底關貿總協定組織更名為WTO前夕,第三次則是今年4月朱杌總理訪美期間。前兩次機會失之交臂,主要原因當然很不相同,但總與當時國內外復雜的政治經濟形勢相關,具有比較顯著的必然性。但今年4月朱杌總理訪美,提出包括部分重大讓步的一整套談判方案,本來完全有可能借與克林頓總統會晤之機達成雙邊一攬子協議。只是由于克林頓總統缺乏足夠的政治勇氣,才未能在當時達成中美入關協議。雖然克林頓幾天后便悔意昭然,采取了新的補救措施,但此后又有意料之中或之外的大事發生,最終看來很可能使中國入關再度受挫。這次機會喪失,顯出更多的歷史偶然性,使人備感遺憾和惋惜。
我們相信中國爭取加入世界自由貿易體系的努力還會繼續下去。但過去十多年的反反復復足以表明,中國能否入關、如何入關、何時入關,實在不是一廂情愿的事情,許多始料未及的因素都可能變成新的障礙。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需要有很堅強的決心和韌性,無論遇到何等挫折都不應輕易否定已有的努力。1994年間中國“沖關”熱情很高,但年底未能入關之后,國內曾出現一種“酸葡萄”論調,怪罪并主張放棄應有的入關努力。這種非理性的情緒是很有害的。此次WTO沖刺一旦受挫,我們應當謹防輿論再度搖擺,更須警惕“酸葡萄”心理引發盲目排外的錯誤主張。
中國早期改革有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以開放促進改革。此次最高層在年初作出入關沖剌的重大決策,種種考慮之一,也是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借入關時的相應開放舉措來推動難度很大的改革。正因此,這回入關可能難以遂愿,才使許多關心改革命運的有識之士深為抱憾。但我們也應當明白,外因畢竟是外因,中國的事情其實還是要靠自己來做。當前在經濟全球化基礎上的新一波高科技革命浪潮,已經無情地擊碎了靠舊體制維護某些領域的“民族工業”的最后一點幻想。縱使近期內入關壓力不再,人們期待已久的電信業、銀行業擴大開放等利弊已清、決心已下的事情,也應當悉心籌劃、穩步操作起來。以擴大開放迎接競爭推動改革,歸根到底是為了中華民族自己的利益,中國需要把改革開放的時間表握在自己手里。